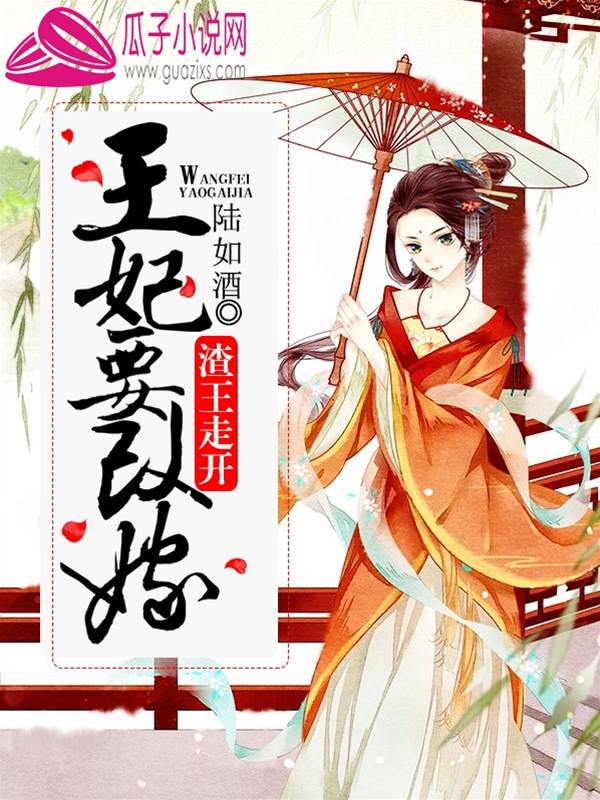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甜寵文里的反派女配》 第73章 番外(二)
分別好幾個月,不僅是凌越想沈嫿,便是也無時無刻不在想他,尤其是兩人心意相通,又皆是坦誠不拘泥的子,親后從未在房事上克制過。
偏生凌越平日冷冷不言語,與獨卻什麼話都不拘著,咬著的耳朵啞聲道:「好似大了些。」
之前猶如初秋懸在枝頭的果子,白皙可人,如今則像是了的桃,恰好能被五指握。
沈嫿這幾日正犯愁,脯鼓鼓的還有些發脹,之前的那些襟都扣不上了,這樣的私又不想被人知道,只能悄悄讓杏仁給重新做小。
不想凌越才瞧了一眼就發覺了,閉著眼雙頰緋紅,輕著長睫悶悶地嗯了聲。
頓了下還補了句:「娘親說懷了寶寶都會這樣。」
「難?」
這等在娘親面前說出來都覺得人的話,在他這卻只猶豫了下,便誠實地又嗯了一聲。
當然難了,不僅脹脹的,有時候裏不夠,了也會覺得刺刺的疼。
凌越沉了片刻,略帶薄繭的手掌覆了上去,作輕地了。
他這雙手是握兵刃的,以往只會重不會輕,可小姑娘的比豆腐還要,輕輕一都會留下痕跡,在娶了之後不得不學會了輕攏慢。
「還疼不疼?」
沈嫿臉上的紅暈蔓延至脖頸,咬著下嚨滾了滾,疼倒是不疼了,可有孕后更加敏,不過被抱著親了親,就化作了春日的雨水。
的聲音又甜又猶如糖水:「不疼了。」
「別,別握啊。」
很快便無力地在了他的前,但他也只低頭輕輕地在臉頰親了親。
沈嫿見他眼尾泛著淡淡的紅痕,卻怕傷著忍著,到底是憐惜他,小心翼翼地伏在他懷中,手指生疏地著。
Advertisement
他則像個耐心的教習先生,在耳邊低喃:「呦呦真聰慧,對了,就是這樣……」
這可並不是什麼值得稱讚的事!
凌越的話落在耳朵里,反而更添幾分旖旎,被誇得面紅耳赤手都酸了,才被準許鬆開。
衫散,他作輕緩地將人打橫抱去了浴池。
沈嫿地靠在池壁,他則作一下輕一下重地為拭上的痕跡,從裏頭出來時,昏昏睡手指都抬不起,渾泛著人的。
天早已暗了,晚膳也都準備好了,兩人總算能好好坐著說說話。
凌越看到桌上一片火紅的菜肴,下意識地擰了擰眉,他是了解口味的,只要好吃的菜肴都喜歡,喜甜喜微辣,可這都不能用微辣來形容了。
且的質偏火氣重,稍微多吃點,隔日就容易角起泡,這麼一桌吃下去,明日還要不要說話了?
而他則無偏好,也不可能是為了遷就他。
他的手指輕輕在桌案上點了點:「怎麼突然想吃這些,是廚子不合心意了?」
他的瓣抿,沒有流出緒,卻有種一點頭,便要將府上的廚子都推出去砍了的架勢。
沈嫿馬上明白過來,他這是誤會被怠慢了,趕忙夾了一筷子的辣子放到他的碗裏,「才沒有呢,是他喜歡。」
邊說邊神溫地低頭了下微微隆起的肚子,「你走之前,我不是就有些胃口不好嘛,那會還不知道是懷了寶寶的緣故,只當是脾胃不舒服。」
「後來診出了孕,便什麼也吃不下去,吃什麼吐什麼,娘親急得沒法子,各種好吃的往屋裏送,爹爹還滿城的尋廚子。」
「以往我可喜歡吃魚蝦了,尤其是鮮的鱸魚,可我一聞著味道就將早膳那點米粥都給吐了。還是同行的一個嬤嬤厲害,在宮便是照顧宮妃的,說有孕的子喜好也會變,各種酸的辣的一嘗,我便吃得下了。」
Advertisement
不僅是喜歡酸,還尤為吃辣的,即便被辣得淚花直冒,還是想吃得,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質有變,如此放肆地吃辣,竟也沒有之前那般連連起泡的狀況。
見凌越不信,連著吃了香辣蝦與辣子,見除了被辣得輕輕嘶著氣外,神都正常,方信了是真的變了口味。
即便他能嘗到味道了,但在飲食上依舊挑剔克制。
他擰著眉嘗試著夾了一筷子,味道雖然重了些,卻比之前那些清淡甜香的菜肴更契合他的口味。
眼見就著一桌紅彤彤的辣子,吃下了一碗半的米飯,還是有些擔憂,讓杏仁準備了下火的小吊梨湯,看著喝下才放心了些。
西北春日的夜晚也還是有些微涼,天徹底暗了,他怕了涼,又見晚上用得有些多,便拉著在屋走消食。
「阿越,你見著大哥哥了嗎?這都小半年了,除了你上回寄來的信里提到了一,本都沒他的消息,若不是我有了孕,爹爹早就急著進京去了。他與阿姊是怎麼回事,家裏可都還好?」
凌越牽著的手,為了遷就的步子,這輩子沒有走得如此慢過,一圈圈從東側間繞到書房來回散著步。
聞言幾不可見地扯了扯角,從沈嫿說起這兄長與程關月的事時,他便發覺他這小舅子對人家姑娘有意思。
可不知是太過遲鈍,還是人家已經有了婚約,讓他更加難以察覺這份喜歡,不僅如此還總把人給惹生氣,人瞧了忍不住發笑。
直到年前程關月真的要出嫁了,沈家又被凌維舟的人所盯,惹下了不的事,三房的沈長儒醉酒不慎打傷了人,對方是鎮國公家的親戚。
孟氏還記恨著趙溫窈的事,鎮國公府與沈家算是勢同水火,再鬧出這麼一遭,便仗著家世他一頭,報了將他關進了京兆府。
Advertisement
不想這事傳到了程關月的耳朵里,就了沈長洲打了人被關,竟不顧家中阻攔,帶著銀錢翻牆跑了出來,要去為沈長洲打點關係,後來才知竟是鬧了個笑話。
沈嫿聽得眼睛都睜圓了,「怎麼還有這種事,我先前還可憐這鎮國公夫人痛失,是個可憐之人,沒想到真是個拎不清的。那之後呢?」
「我到京中時,他已劫了喜轎。」
那會局勢不安,連皇帝都換人了,京中各府人人自危,哪還有心思管誰家的兒被劫了。
他只知道,沈長洲早就在事發之前,就將沈老夫人送去了郊外的莊子裏,而沈長儒被關后,鄒氏四求人都沒用,怕他們真將寶貝兒子給活活折磨死,竟將沈玉芝獻給了寧遠侯做填房,只求他能出面保下沈長儒。
「那寧遠侯都快五十了,比我三叔父都要年長,這,這怎麼能行啊,三叔父也能答應?」
「你三叔父不知,等下聘的人到家了,他才知曉這個消息。」
沈家三爺本就為兒子的事到奔波,再聽到這事活活被氣暈過去了,醒來便要退親,可人都被接走了,他氣得一紙休書與鄒氏和離。
可事已定局,沈玉芝進了寧遠侯府哪還這麼容易出來。
至於那孟氏與鎮國公府,因趙溫窈的關係,不得不和凌維舟綁在一條船上,宮變之時威利京中的大臣們,待到宮門被凌越的鐵騎踏破,他們也了逆黨,昔日鼎盛的鎮國公府被抄家下獄,落了個遭萬人唾棄的下場。
沈嫿唏噓不已,趙溫窈找上孟氏可以說是趙溫窈心機深,而孟氏本可以保持清醒,不想卻一錯再錯還給家族帶來了滅頂之災。
而鄒氏和沈玉芝也是貪婪趨炎附勢的子,並不值得同,唯一擔心的就是三叔父了,如此接連的打擊,也不知能不能熬得住。
Advertisement
「放心,沈家無礙。至於那隴西王,是個識時務之人。」
隴西王的封地與涼州相鄰,他與此人打過不道,只是他的子,若沈長洲還是沈長洲,這奪兒媳之恨他或許不會善罷甘休。
可如今沈長洲是他凌越的妻兄,他便是賣人也會主不予追究,絕不會將事鬧大。
這門親事若想,最重要的還是程關月與程家的態度。
不過是短短幾個月,在涼州養胎彷彿是住進了深山老林,再窺探到外界的消息已然天翻地覆的改變。
兩人在屋走了兩三圈,沈嫿就有些走不了,半邊的子倚在凌越的懷裏,他正要扶著坐下,突得兩人皆是一僵。
沈嫿捧著自己的肚子,雙眼一眨不眨,愣了足有半刻鐘,才低聲音,像是怕驚嚇到什麼似的極輕地道:「阿越,你覺到了嗎?」
後的人也愣了下,他失去了往日的淡定與持重,頓了片刻方繃地道:「嗯。」
「他,他了,是寶寶了。」
之前蘇氏與嬤嬤都說過,大概四個月後就會有胎,但肚子裏的孩子格外安靜,若不是小腹眼可見得一點點鼓起,甚至都要懷疑自己有沒有懷孕了。
沒想到他不是不,是要等爹爹回來啊。
初次當爹娘的小夫妻對視了一眼,都從對方眼裏看到了慌,而沈嫿更多了份興,凌越則是無措。
便是上以一敵百的戰事他都沒這麼慌張無措,他的雙手僵直,凸起的結上下了下,「我去喊大夫。」
說著竟真的要出去喊人,倒把沈嫿給逗笑了。
誰能想到號令天下的肅王,到自家孩兒頭次胎,反應竟會是這樣的。
「阿越,不用喊,這是正常的,這說明我們的寶寶很健康,他定是睡飽了,這會醒來了呢,許是知道你回來了,急著見你。」
凌越抿著,渾繃作僵地將扶到了榻上,在遇見沈嫿之前,他都以為自己厭惡脈親人,家於他而言不過是虛偽與腥的地方。
可自從有了沈嫿,他開始期待回家,甚至很快還會有個與他脈相連的小傢伙出生,這真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
老實說,方才知曉這個消息他都沒什麼真實,直到現在,他才真正的意識到,他將要有孩兒了。
沈嫿覺到他手臂的僵直,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心思,握住他的手掌,小心且堅定地放在了自己隆起的小腹上:「你他呀。」
「阿越,你喜歡男孩還是孩啊?」
「你說寶寶出生以後會像你還是像我啊?」
「要是他也能有一雙像你這般好看的眼睛就好了。」
在耳畔低低地輕語,就像是首聽的歌謠,讓他不自覺地了迷,僵的手掌也漸漸地和緩了下來。
而後他覺到掌心下的拿出,突然又了一下。
他的眼底不自覺地流出了一抹,「都喜歡,像你更好。」
沈嫿的眼眶也有些熱,他雖然無法原諒曾經的家人,卻在努力地接納另一個家,手將他擁,歡喜又輕地道:「阿越,我和寶寶都在等你回家。」
孑然一二十餘載,他終於有家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25 章

攝政王冷妃之鳳御天下
不可能,她要嫁的劉曄是個霸道兇狠的男子,為何會變成一個賣萌的傻子?而她心底的那個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趙國的攝政王?對她相見不相視,是真的不記得她,還是假裝?天殺的,竟然還敢在她眼皮底下娶丞相的妹妹?好,你娶你的美嬌娘,我找我的美男子,從此互不相干。
62.7萬字8 16261 -
完結668 章
毒妃傾城:王爺掌中寵
夏吟墨手欠,摸了下師父的古燈結果穿越了,穿到同名同姓的受氣包相府嫡女身上。 她勵志要為原主復仇,虐渣女,除渣男,一手解毒救人,一手下毒懲治惡人,一路扶搖直上,沒想到竟與衡王戰鬥情誼越結越深,成為了人人艷羨的神仙眷侶。 不可思議,當真是不可思議啊!
120萬字8 17247 -
完結150 章

殷總,寵妻無度
姜綺姝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當她慘遭背叛,生死一線時救她的人會是商界殺伐果斷,獨勇如狼的殷騰。他強勢進入她的人生,告訴她“從此以后,姜綺姝是我的人,只能對我一人嬉笑怒罵、撒嬌溫柔。”在外時,他幫她撕仇人虐渣男,寵她上天;獨處時,他戲謔、招引,只喜歡看姜綺姝在乎他時撒潑甩賴的小模樣。“殷騰,你喜怒無常,到底想怎麼樣?”“小姝,我只想把靈魂都揉進你的骨子里,一輩子,賴上你!”
37.1萬字5 11927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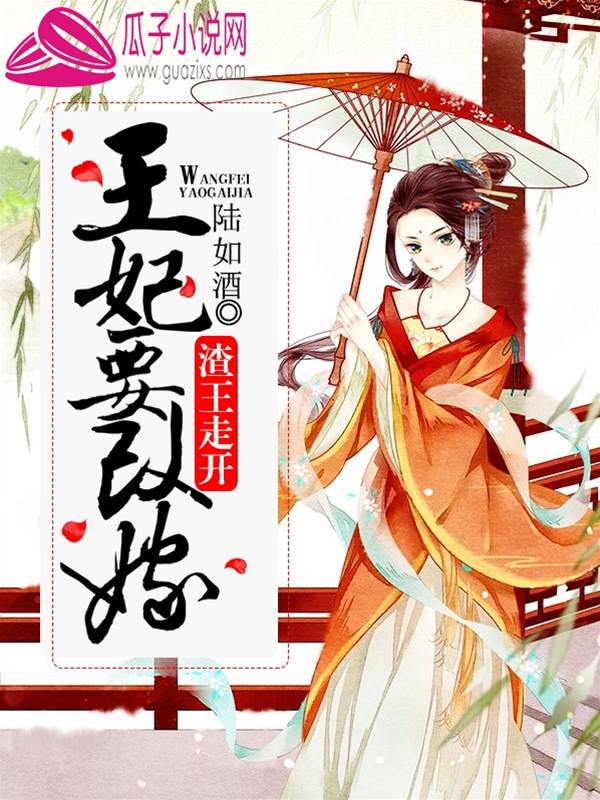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137 章

鶴帳有春
穆千璃爲躲避家中安排的盲婚啞嫁,誓死不從逃離在外。 但家中仍在四處追查她的下落。 東躲西藏不是長久之計。 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生個孩子,去父留子。 即使再被抓回,那婚事也定是要作廢的,她不必再嫁任何人。 穆千璃在一處偏遠小鎮租下一間宅子。 宅子隔壁有位年輕的鄰居,名叫容澈。 容澈模樣生得極好,卻體弱多病,怕是要命不久矣。 他家境清貧,養病一年之久卻從未有家人來此關照過。 如此人選,是爲極佳。 穆千璃打起了這位病弱鄰居的主意。 白日裏,她態度熱絡,噓寒問暖。 見他處境落魄,便扶持貼補,爲他強身健體,就各種投喂照料。 到了夜裏,她便點燃安神香,翻窗潛入容澈屋中,天亮再悄然離去。 直到有一日。 穆千璃粗心未將昨夜燃盡的安神香收拾乾淨,只得連忙潛入隔壁收拾作案證據。 卻在還未進屋時,聽見容澈府上唯一的隨從蹲在牆角疑惑嘀咕着:“這不是城東那個老騙子賣的假貨嗎,難怪主子最近身子漸弱,燃這玩意,哪能睡得好。” 當夜,穆千璃縮在房內糾結。 這些日子容澈究竟是睡着了,還是沒睡着? 正這時,容澈一身輕薄衣衫翻入她房中,目光灼灼地看着她:“今日這是怎麼了,香都燃盡了,怎還不過來。”
20.8萬字8.33 149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