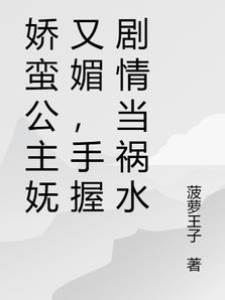《羅家棄女很囂張》 第九十八章:反殺
天將黑未黑,張老三和周來寶就從朱大郎家出來了。
朱大郎點頭哈腰的相送,臉上的笑諂得沒法看:「三爺您放心,錢秀才要真被趙家暗害,我朱大貴就是村裡最有文化的人了,替大伙兒張正義,我不畏艱險、義不容辭。」
「嗯!」張老三渾的高高在上:「做好事再來賣。」
「三爺放心,放一百個心。這樣的機會,我朱老大……我老朱祖上冒了青煙才遇上了。」
朱大郎也曾是讀書人,可惜不是那塊料。他從十四就開始考秀才,考到三十了,還沒考上。
家裡人從懷揣期漸漸絕,家裡貧寒又供不起他的筆墨紙硯。他便再不念了。
這些年,每每見著錢秀才免差徭,租,他就嫉妒得惱。辛虧錢秀才格不好,在縣衙當書辦,不過月余就被遣回了家;教書也不行,區區兩年就惹得夫子們怨言四起,只得回來種田。
要不然,看著錢秀才發跡,他得發瘋。
現在,他不用嫉妒了。三爺的新主子答應給他秀才的功名,錢秀才已經被趙家害了,新明村往後就數他最風、能耐。
況且張三爺還和他說好了,事之後,不新明村,周邊村莊的鹽都讓他負責。他相當於張三爺手下的分銷商。
賣鹽啊!
想想這兩個字,他都能看見金銀珠寶手牽著手,挨挨的往他家滾。
這樣的好事,你說不是祖墳冒青煙,能遇到?遇到了,不豁出去忙抓,那得傻什麼模樣?
張老三沒再看的朱大郎,他才不管朱大郎在做什麼夢,他就沒想過朱大郎能活著回來。
昨兒個新得的信,已經有二十多個村的村民,有不同程度的私鹽中重度癥狀了。要牽扯這麼多人命,又涉及到朝廷命販以權貪礦、倒賣私鹽。
Advertisement
這樣天大的醜聞,哪個敢放出風聲?
不管府尹怎麼判,朱大郎最後都只有個死字。
若不然,他們何苦非得將錢秀才到絕路?
想著這個,張老三暗悔:早知道新明村還有這麼個傻貨,用什麼錢家?家的兒又不值錢,別說謀算計,就讓他白白拿出來,只怕都行。
張老三搖了搖頭,否定了先前的想法:要真那樣,算計趙家的痕跡就太重了。只怕才剛開始,就要被趙家察覺出來。
要說穩妥,錢秀才去告發是最穩妥了。他的,討死鬼!
從朱家出來,張老三和周來寶又在繞著路,在新明村外轉了好幾圈。等天黑了,確定沒人注意他們,才又悄悄進錢秀才家。
不敢趕車過來,張老三便拿頭巾裹住錢秀才的頭臉,命周來寶背著往趙家庫房去。
周來寶臉都青了:他在趙家再不得志,也是管著二十多家糧油鋪的大管事。多人見了他都一臉結,儘是好話?
讓他背死人,還從新明村背到西甲村去?
「磨蹭什麼?你不背,讓朱大郎來背?你弟弟的舉人老爺,也讓給朱大郎當?」
「三爺別生氣,我這不是沒背過,瘮得慌嗎?」
他咯咯乾笑了兩聲,彎下腰艱難的將錢秀才背起來,和張老三一起鬼鬼祟祟的朝西甲村走去。
夏天蚊蟲多,趙家在西甲村的這個庫房又在村外。府尹和屬下分別躲在樹林里,蚊子餵了不,其外卻半點靜都沒等到。
即便如此,趴在草叢中的府尹依舊不敢。那雙眼睛黏在庫房上,幾乎都不敢眨。
開玩笑,這私鹽要是在他眼皮子底下運進來,別說帽,就連他全家老小的腦袋也不用要了。
在府尹眼都快睜不了的時候,有人來了。
Advertisement
到了庫房門口,周來寶將錢秀才摔下來,掏出鑰匙來開庫房大門。張老三斜一眼黑漆漆的草叢,晦氣的唾了一口道:「埋了吧,明晃晃扔進庫房,太不合理,惹人懷疑。埋淺點,兵發現以後都不用別人引導,自己就會往咱們想要的方向猜。」
「是,還是三爺想得周到。在庫房邊發現錢秀才被掩埋的,只能是錢秀才發現了趙家的,被趙家的人殺害。」
周來寶去庫房挑了挑,沒找到能挖坑的工,只得拿了個秤桿出來。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勻,然後便開始刨坑。
「嗯嗯,你是這個庫房的大管事,你最是清楚,你出來作證最好不過。」
張老三看了眼周來寶上的傷,眼中笑意明顯:「為了護住錢秀才,你小命都快待在這裡了。要不是這樣,你也不能站出來舉報趙家販私鹽,是不是?」
「三爺這玩笑開得太大,我這可承不起。」周來寶刨坑的作一頓,起怔愣的看著張老三:「咱們可是說好的,只配合打開庫房讓你們把私鹽運進來,其外要怎樣打司,我一概不管。
今晚上辦事,我便要連夜回漳河老家探親。明兒一早朱大郎擊鼓告狀,領府尹大人過來查。那都不關我的事。」
張老三按住他那秤桿的手,讓他接著挖:「就是個玩笑。」周來寶就這樣站著,直愣愣的看了張老三很久:他心裡七上八下的打著鼓,從沒像現在這樣後悔。
想一想,在趙家做事,到底坦。手裡管著二十多家鋪子,在京城也還算風……
「就是個玩笑,你咋這樣不識耍?」見周來寶還是不,張老三推他一把道:「你信不過我,還能信不過太子?你賭上家命相幫,太子定然恩賞,絕不會將你往這要命的漩渦里拽。」
Advertisement
周來寶又看了張老三兩眼,到底沒能耐反抗,拿著秤桿好生刨坑。
他和張老三替換著來,直累得力,也才挖出半尺深的坑。實在刨不了,張老三便將錢秀才往了坑裡一扔,連土帶草將將蓋住了錢秀才上半。
「就這樣吧,真埋深了,我還怕府發現不了。」
張老三一屁坐在地上,拿袖子著額上的汗,看著估著時辰道:「貨也該來了,怎麼還沒靜?」
「不是出了什麼差錯吧?」
「這可要命!」張老三坐不住了:「你在這裡守著,我接出去看看。」
說著又警惕的檢查了四周,府尹趴在不遠大氣都不敢出。確定沒有異常,他才往外走去:「你自己也注意點,一有不對,趕忙放信號彈知不知道?
「知道!」周來寶有些抖了:按先前的計劃,永興軍早該將私鹽運過來了。
不是真出事了吧?這樣想著,他上抖得厲害,篩糠一般:不行,得想法子活下去。這事要真弄不,太子是皇帝的兒子,我們可狗屁不是。可太子得罪不得啊,要這怎麼辦才好?
他悔得直扇自己耳,扇了有二三十下,終於有了主意:能和太子對抗,又能搭上線的只有秦王了。
對,找晚照苑去。將這驚天的消息告訴古權,也算立了大功了。對,還得想法子接近羅曼,那丫頭小,好糊弄,在趙家又是紅人。只要肯去趙二爺跟前替他說話,只怕升掌柜都不在話下。
說做就做,等再看不到張老三影子,他便撒往晚照苑奔。
什麼舉人老爺、富甲一方。張老三用他跟用朱大郎一樣,本就是想用完就扔。
他必須在這之前找到人庇護。
趙家庫房前又恢復了寧靜,府尹卻再也寧靜不了:這哪裡是查私鹽?這分明就是太子在清繳秦王的勢力。
Advertisement
鹽和太子聯繫起來,又自然的想到了永興軍。要是永興軍還牽扯其中……
陛下讓他查出真相,可這樣的真相……
府尹又出了一冷汗,他上還擔著督查軍防的職。尋常在軍中不上,真出了事責任卻是不輕。
「你們好生盯著,王大,你跟我走一趟。」
府尹叮囑一番,追著張老三的方向去了。
誰知道才追到新明村口,竟和搖著摺扇閑逛的古權迎面撞上,躲都來不及躲。
「這麼巧,府尹大人也來散步?」古權朝府尹作揖行禮,臉上神幽深:「您怕是散不了,我剛才從蘆葦盪那邊過來,看著有大事要發生。」
府尹裡苦,心頭更苦:哪裡是巧,你本就是特意在這裡捉我。
「那一起去看看?」
遠遠地,就看見蘆葦盪那邊衝突起來。一群穿著短打的壯漢堵著河裡的船,七八條吃水很重的船上,壯男子亮著武,個個面帶殺意。
「軍爺息息怒啊,撞停你們的船也是意外嘛。怎麼就到了刀槍的地步?」水鬼瞄著了古權,扯著嗓門喊他:「這不是古先生嗎?你來給我們說和說和吧。」
沒等古權走近,水鬼就說起了事經過:「天氣熱,我們哥兒幾個出來鳧水,沒想撞了他們的船。更不巧的是,我兄弟才得的一柄藏刀找不見了,都懷疑掉到了他們船上。
那刀也不金貴,就是難得,是兄弟的心頭好。於是想著去他們船上看一看,找見了最好,找不到,也好死心。
可他們死活不讓看,先說船上是趙家最金貴的貨。又說是永興軍在執行軍務,運送軍資。古先生說說看,什麼金貴的貨不能看?哪個執行軍務的和我們草莽穿一樣?」
古權笑瞇瞇的看向府尹大人:「既是軍務、軍資便好說了。大人擔著督查的職,最清楚近日有什麼軍資要往外運。」
府尹尷尬的笑:依附著姜家的永興軍,是他一個京兆府尹能督查的?
「別人不能看,府尹大人你肯定能上船看。」古權指著船上泛著寒的刀面,對府尹大人道:「看完刀有沒有掉到船上,大人也順便看看船上的貨。你來了這一趟,貨可就是你查過的了,往後要出了問題,大人……」
看著亮刀的男子,府尹便知道是軍中將士沒錯了。普通武夫,不可能這樣整齊劃一,臉上也沒有那樣濃烈的煞氣。
不用上船,他也猜到了:船上是私鹽,還是太子爺的私鹽!
在荊湖一事上,陛下才打了秦王一系。這次,他想要的,到底是怎樣的真相?
府尹又出了一腦門冷汗,他拿出自己的印,要求上船查驗貨。隨後要怎樣結案是一回事,現在不查卻是寧外一回事。
「怕是不方便。」船上下來個將領模樣的人,他沒看府尹的印,直接攔了路:「這裡景不錯,大人既然來了,便留在這裡好生賞景吧。」
話音落地的同時,利刃出鞘,直削府尹腦袋。古權應變快,手裡摺扇架住了對方的刀。扇子骨架是鐵所造,收攏便是把鋒利短劍。
他將府尹護在後,兩方人馬打了一團。
只深夜押一趟貨,永興軍在船上配的都是普通士兵。古權這邊,卻個個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雖說人,卻和永興軍僵持了下來,沒讓對方佔到便宜。
可到底是寡不敵眾,半個時辰之後,古權這邊便顯出劣勢。府尹雖被古權護著,也不可避免面的多傷,他心裡悲涼一片:得,他代在這裡,也惹不了太子的眼,一家老小的小命好歹是能保住了。
正哭笑不得,突然有金吾衛殺進來。
府尹往來人方向看去,便看到一便裝的秦王,陪著同樣一便裝的皇帝,大步流星的朝這邊走來。
猜你喜歡
-
完結4031 章

世子妃她是朵黑心蓮
前世,南宮玥是被自己坑死的。她出生名門,身份尊貴,得當世神醫傾囊相授,一身醫術冠絕天下。她傾盡一切,助他從一介皇子登上帝位,換來的卻是一旨滿門抄斬!她被囚冷宮,隱忍籌謀,最終親手覆滅了他的天下。一朝大仇得報,她含笑而終,卻未想,再睜眼,卻回到了九歲那一年。嫡女重生,這一世,她絕不容任何人欺她、辱她、輕她、踐她!
436.7萬字8.18 676395 -
完結654 章
震驚!太子會讀心后夜夜翻我牌子
太子蕭錦言是個講究人,對另一半要求很高,擁有讀心術后要求更高。奈何身邊美人無數,卻沒一個是他的菜,直到看見一條小咸魚,嘴甜身子軟,正合他胃口,“今晚你侍寢。”作為混吃混喝的小咸魚瑟瑟發抖:“殿下,我還沒長開呢。”*沈初微一朝穿回古代,成了太子爺不受寵的小妾,琴棋書畫一樣不會的她,以為是混吃混喝的開始,卻沒想到被高冷太子爺給盯上了。徐良媛:“沈初微,你最好有點自知之明,今晚可是我侍
149.2萬字8 67371 -
完結278 章

王妃又帶崽爬墻跑路了
【事業心女主+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男二上位】 一場意外穿越,唐雲瑾身懷六甲,被無情男人丟至冷院囚禁,承受著本不該承受的一切! 多年後再見,他奪她孩子,威逼壓迫,仍舊不肯放過她。 為了打翻身仗,唐雲瑾卧薪嘗膽,假意妥協,卻用芊芊素手行醫,名震京城! 當塵封多年的真相解開,他才知自己這些年錯的有多離譜,將她堵在牆角柔聲哄道:「本王什麼都給你,原諒本王好不好? “ 她卻用淬毒的匕首抵住他的喉嚨,冷冷一笑:”太遲了,王爺不如...... 以命相抵! “ 後來,她冷血冷心,得償所願,穿上鳳冠霞帔,另嫁他人......
100.6萬字8 20983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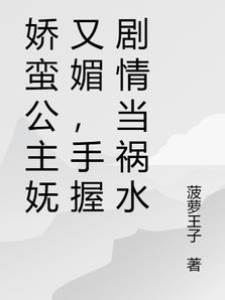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
完結172 章

沖喜王妃腰太細,病嬌王爺狠又毒
【1v1,雙潔雙強+爽文+寵妻無底線,女主人間清醒】寧家滿門覆滅,兩年后,寧二小姐奇跡生還歸京,卻嫁給未婚夫的皇叔,當了沖喜王妃。 皇叔垂死病中驚坐起:王妃唇太甜腰太軟,他怎麼能放任她去蠱惑別的男人? “兵權給我,王府給我。” 病嬌皇叔點頭,抱著她寬衣解帶:“都給你,本王也給你好不好?” “?” 給……給什麼? * 歸來的寧三月只想為寧家翻案,誓為枉死的人討回公道。 后來,寧三月多了一個目標:當好沖喜王妃,讓皇叔好好活著。
29.9萬字8 1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