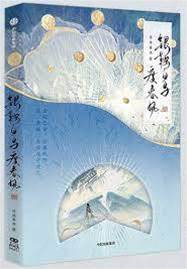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無鹽為後》 第三十章 風聲起
李太后對王容與的喜表現的明明白白,眾秀是又妒又羨。王芷溪來找王容與,「姐姐還在生我氣?」
「如果不是我,姐姐現在也不會得太后親眼。」王芷溪心裏也是懊惱的,畢竟沒想到陛下會要聽王容與拉琴,白白給了表現的機會,但是臉上還是十分委屈,「姐姐就原諒我吧。」
「我沒怪你。」王容與說,「只是妹妹下次說話記得,一筆寫不出來兩個王來,你再把欺君的名號往我頭上安時要切記你也討不了好。」
「姐姐緣何說的這麼重?我一向說話有口無心的。」王芷溪帕子捂臉說。
「妹妹是聰明人,自然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有口無心什麼時候不可以。在宮裏,說錯一句就是死。你或者我死了都無所謂,但要是殃及家人,怕是到了地底下,都無迴。」王容與說。
「姐姐何苦嚇我,我記著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王芷溪說,眼淚汪汪的好不可憐。
「不要再在我面前出這樣的神,已經夠了。」王容與說,「自進宮來我已經忍讓了你許多次,你該知足了不是嗎?按照我們以往的默契,真要惹惱我,最後吃虧的是你。眼看還有最後十餘天就是最後結果的日子,你當真要浪費時間在我這嗎?」
「姐姐。」王芷溪糯糯喊道。
「不要再從我這裏梨花帶雨的離開,不要再去散播我這個姐姐是怎樣的心毒不憐惜你,你花容月貌,人人都敬畏你以後會有個好前程,不要來惹我這腳的人。我要是鐵了心弄你,後果你承當不起。」王容與說。
王芷溪秒變臉,帕子摁了摁眼角,總算不用那膩的人發麻的語調喊王容與,「就像姐姐說的一筆寫不出來兩個王來,既然我們姐妹二人進宮來,日後不得要互相照應。」
Advertisement
「行啊。值不定以後要你照顧我呢。」王容與笑說,「陛下寵你的時候,也記得讓他往不得寵的我這兒走走。」
王芷溪被噎的一哽,起走了,之後倒是往後殿來了。
張來儲秀宮,儲秀宮的姑娘又人人得了一件陛下的賞賜,唯有王容與這,張親自送過來的二胡。「王姑娘,這是陛下賞你的二胡。」
王容與接過來一看,好好的一把二胡,皮了金片,琴頭上鑲了寶石,整個一個珠寶氣,王容與輕輕著琴呢喃,「二胡是流浪的聲音,大地的聲音,穿金戴銀都不像它了,不倫不類。」
張沒聽見王容與說什麼,只是慣會看臉的他知道王容與的臉算不得好,只能賠笑說,「陛下說姑娘二胡拉的好,這二胡庫原是沒有,另請尚功局新做的。」
「謝陛下隆恩。」王容與說。
「姑娘喜歡就好。」張說,靈機一又說,「若是姑娘不喜歡這樣式也可以讓尚功局另作的。」
「多謝公公,但是不必了。」王容與說,「二胡的聲音和它本的裝飾並無關係。若是注重裝飾,就是我著相了。」
「姑娘境界高。」張說,這次他可不會自作主張再讓王容與給他回個禮,二胡送到就要走,王容與示意,喜桃送到殿外給張塞了一個荷包。
「這是幹嘛?」張不收。
「這是姑娘的意思,姑娘心裏清楚這些時日是麻煩你了。你若不收,就是看不起姑娘。」喜桃輕輕的說。
張看,「能有這樣的皮子怎麼窩在儲秀宮一直沒挪窩呢?」
「得,我接著,你替我謝姑娘賞。」張說,「你也是有些運道,好生伺候著姑娘,日後有你的好。」
王容與得了李太后的親眼,自然有其他的宮來湊王容與的熱灶,別人往王容與跟前湊的時候,喜桃反而不上前了。
Advertisement
王容與看一眼來給送熱水的宮,是什麼來著,算了,也不重要。午間在繞廊慢行消食,遠遠看見喜桃招手讓上前來,「昨天怎麼沒見你?」
「奴婢另有事做呢。」喜桃低頭說。
「是不是們欺負你了?」王容與問。
喜桃搖頭。
「那你不想伺候我了?」王容與問。「嫌棄我了?」
「姑娘。」喜桃急道。「奴婢只怕姑娘嫌棄我,怎麼會嫌棄姑娘呢?」
「我不嫌棄你,什麼時候都不嫌棄你。如果我有幸能得獨居一殿,要你跟我一起,你可以願意?」王容與說。
「只要姑娘不嫌我愚笨,奴婢願意。」喜桃激說道。
「那好,以後你就跟著我,別人讓你去伺候,你就說是我說的,只讓你伺候我,別人不願意就讓來找我。」王容與說。現在秀不多,伺候的宮也基本穩定下來,如果特意要別人用了的宮,形同挑釁。
「姑娘。」喜桃的淚眼汪汪。
「我做了幾張書簪,你等會拿去給安得順,讓他拿著玩。」王容與回屋午睡,喜桃給端茶上來,王容與遞給一個檀木小盒輕聲囑咐
喜桃收好後福出去。
安得順頂著太一刻沒停歇的去往乾清宮,他可不敢去前找張,只是窩在張的睡房裏,花上一角銀子讓乾清宮的小太監去幫他找一下張,張回來。「急匆匆的什麼事?我不是讓你晚上再來找我嗎。」
「大好事。」安得順眉開眼笑的說,「姑娘讓我來送這個給陛下。」
「這是什麼?」張接過一看,檀木小盒子裏握著四張書簪,張也不敢拿起,就輕輕的翻,確定裏面沒別的東西。「這個是姑娘自己做的?」
「是呢。」安得順說,「這可是姑娘第一次主向陛下示好呢,許是姑娘開竅了。」
Advertisement
「開竅就好,這天底下誰都要討陛下的歡心,擰著幹什麼呢?現在陛下還在興頭上,由著,等到陛下哪天轉心了,哭都來不及。」張說。他把檀木盒子放好。「得了,你這事咱家記下了。左右等姑娘的冊封下來,就有你的賞了。」
「不知道以後小的有沒有機會繼續伺候姑娘。」安得順殷勤的給張起肩。
「想繼續伺候姑娘?」張說。「那你去姑娘面前獻殷勤去呀,跟我肩敲背的可沒用。」
「姑娘實在是難得的好伺候的人,沒有我表現的機會啊。」安得順苦著臉說。
「你安心著別犯錯,這儲秀宮裏姑娘只和你相,只要到時候姑娘提一句讓你去伺候,這事就妥了。」張說,「你要不知道怎麼討好姑娘你就討好姑娘邊那個宮,常伺候的那個,什麼名來著。」
「喜桃,喜桃。」安得順說。
「對。你去討好喜桃,到時候替你說說好話也。」張說,「行了,你別在我耗時間了,我現在得去伺候陛下了。」
張直到晚間的時候才逮到只有他和陛下的機會,張把檀木盒子呈上給皇帝,朱翊鈞正在練字,看了一眼,「這丑不拉幾的盒子哪來的?」
「陛下,這盒子不重要,盒子裏的東西才重要。」張說。
「你什麼時候也學會給朕賣關子了?」朱翊鈞笑說,接過盒子打開一看,裏頭是書簪,自己裁的樣子,難為邊角都理的很好,上頭是鏤空的亭臺圖樣,下頭的方形里寫著幾個字,「書山有路勤為徑。」
「學海無涯苦作舟。」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書簪無出奇,只勝在字跡清秀雋永。朱翊鈞自然認得王容與的字,「王容與做的?」
Advertisement
「是,王姑娘念陛下送給的二胡,特意親手做了書簪送過來的。」張說。
「還有這樣的心思?」王容與說,「每次見了朕都是為什麼又是你,趕走趕走,我不想和你扯上關係的表,還有這樣的小兒思?」
「王姑娘現如今人在宮中,日後還得仰仗陛下才能活下去呢。」張說。
「朕卻不喜歡這樣的聰明。」朱翊鈞這麼說,但是書簪還是留下來用,畢竟王容與的一手字還是讓人心曠神怡。
郭嬪懶懶的倚在炕上,「今日陛下召幸了誰?」
「今日陛下沒有翻綠頭牌,一個人在乾清宮呢。」郭嬪的大宮綠臘說,「娘娘何須擔心,秀進宮后,陛下甚臨幸後宮,便是有都是召的娘娘去呢。」
「哎,新人已經進宮,我這舊不知道還能得幾分憐惜。」郭嬪說。
「娘娘,陛下是念舊的,何況奴婢冷眼瞧著,這次的秀也沒幾個姿容能超過娘娘的。」綠臘說。
「沒幾個,那就是還有咯。」郭嬪說,「為悅己者容,自然要當這悅己者心中的第一人。」
「娘娘,那個周玉婷不足為患,在儲秀宮的作為,只要一點到太後面前,就沒有迴轉之地。」綠臘說,「倒是那個王芷溪,行事周妥,不溜丟抓不到下手的時機。」
「秀現在去慈寧宮的時間很多了吧?」郭嬪突然問。
「是,每隔一日都要去問安。」綠臘說。
郭嬪角上揚,「那儲秀宮的宮可要好好跟秀說一下太後娘娘的喜好,可一定要幫助秀討太后的歡心。」
猜你喜歡
-
完結121 章

攻心毒女:翻身王妃
可憐的李大小姐覺得自己上輩子一定做錯了什麼,這輩子才會遇到這麼多衰事。好在美人總是有英雄相救,她還遇到了一個面如冠玉的男子相救,這麼看來也不是衰到了極點哦? 不過偽善繼母是什麼情況?白蓮花一樣處心積慮想害死她的妹妹又是什麼情況?想害她?李大小姐露出一絲人獸無害的笑容,誰害誰還不一定呢!
46.5萬字8.18 19134 -
完結337 章

成為人生贏家的對照組[快穿]
她不是人生贏家,卻比人生贏家過的還好,你敢信?人生贏家歷經磨難,一生奮斗不息,終于成了別人羨慕的樣子。可她,吃吃喝喝,瀟灑又愜意,卻讓人生贏家羨慕嫉妒恨。在紅樓世界,她從備受忽視的庶女,成為眾人艷羨的貴夫人,作為人生贏家的嫡姐,也嫉妒她的人…
212.4萬字8 11147 -
完結686 章

神機毒妃只想寵反派
穿成狗血文女主,黎清玥開局就把三觀炸裂的狗男主丟進了池塘。為了遠離狗男主,轉頭她就跟大反派湊CP去了。原書中說大反派白髮血瞳,面貌醜陋,還不能人道,用來當擋箭牌就很完美。然而大反派畫風似乎不太對…… 她逼他吃噬心蠱,某人卻撒起嬌: “玥兒餵……” 她缺錢,某人指著一倉庫的財寶: “都是你的。” 她怕拿人手短,大反派笑得妖孽: “保護好本王,不僅這些,連本王的身子都歸你,如何?” 【1V1雙強,將互寵進行到底】
130.7萬字8.18 178083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662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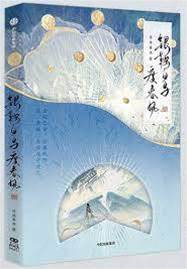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