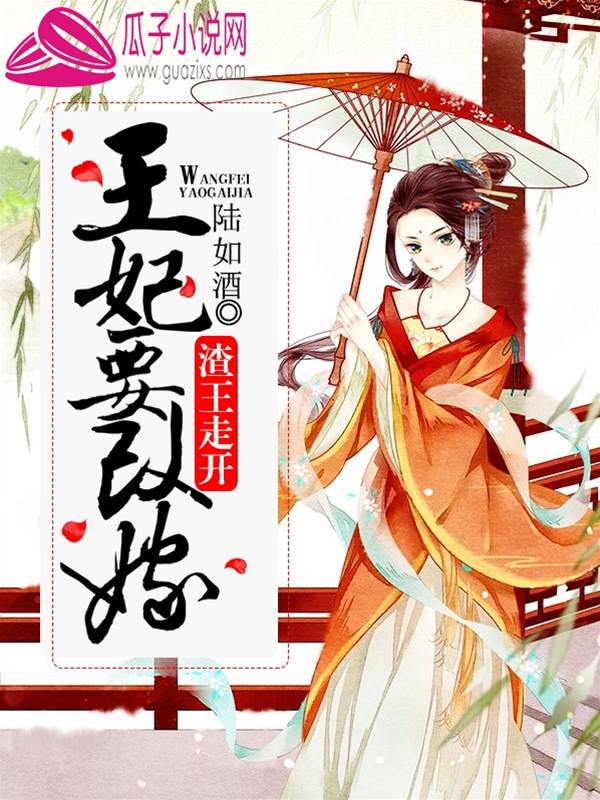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代嫁太子妃》 第九十三章 來得突兀
他像搗藥一般,拿起石杵對著那些花瓣輕輕地砸起來;鮮紅的很快浸潤了白的杵罐,那紅的讓人驚豔又驚心。
“主子,您要的。”
田青小心的把一小塊白的幾近明的東西放到了石桌之上,又悄無聲息的退下了。
酈昭煜拿起一點,放進杵罐;那個東西很快碎,溶解,裏麵的也被它吸收了一部分。
由一開始的疑,到後來的好奇;慢慢的,不知不覺中,竟然不由自主的用手托住腮,撐在桌案上,認真的觀察著他手底一點一點的作。
“好了!”
“嗯?”
還沒有從當中回過神來。
的樣子讓他輕笑,一本正經的向出手。
“拿來。”
在的微愣下,他主拉了的手過來;隨即清涼的覺在指尖散開他正用竹簽挑起杵罐之中的花瓣的泥漿為細致的敷到指甲之上。
Advertisement
那認真的樣子,仿佛在對著一件珍貴的珠寶。
這分明是古代最簡易的丹寇!
類似於現代的塗抹指甲油,這是孩子的事,他做起來也是得心應手,不知他準備了多久,又費了多的心。
的手隨著心微微抖了一下,要往回。
“別。”
囑咐著,手底作不停,十個指甲一個個的細心為敷好;最後,滿意的欣賞著自己的“傑作”,輕聲問。
“喜歡嗎?”
呃。
那皺皺、涼涼、深諳的東西,也虧他費這麽大的心,實在看不出有什麽“好看”“不好看”來。
“這個”微微皺了一下眉頭。
“嗬嗬。”他自嘲的笑了一下,“我太心急了。”
他的垂下頭,對著的指尖輕輕吹著氣,加速它的風幹。
暖暖的,的覺在心底漾開;能清晰地到自己心的悸。
Advertisement
片刻之後,指甲上的涼意漸散,那一個個花瓣的泥漿幹幹的凝固在的指甲之上,厚厚的,很不舒服;他便招呼田青捧來一盆清水,細心地為洗盡。
那紅潤潤的略帶一些的便留在了的指甲之上;他拿著白的錦帕又了兩下,居然沒有!
“太好了!”他長舒一口氣,“田青?”
“奴才在。”
“告訴譚掌櫃,就用明礬。”
疑著他們之間的默契,他卻溫的了過來。盯住額頭上得傷疤,薄抿了又抿,愧疚的說。
“這是我心底的疤,——是我沒有保護好你,對不起!”
今天,這是他的第幾次認真?
這讓分外的不自在起來,別過眼。
“都過去了,不要再提了。”
“不!這是我的錯!我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醫治好你!”他說的無比沉重,握起的手,小心的解釋,“現在,就先讓我做一些彌補;知道剛才加的是什麽嗎?”
猜你喜歡
-
完結325 章

攝政王冷妃之鳳御天下
不可能,她要嫁的劉曄是個霸道兇狠的男子,為何會變成一個賣萌的傻子?而她心底的那個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趙國的攝政王?對她相見不相視,是真的不記得她,還是假裝?天殺的,竟然還敢在她眼皮底下娶丞相的妹妹?好,你娶你的美嬌娘,我找我的美男子,從此互不相干。
62.7萬字8 16261 -
完結668 章
毒妃傾城:王爺掌中寵
夏吟墨手欠,摸了下師父的古燈結果穿越了,穿到同名同姓的受氣包相府嫡女身上。 她勵志要為原主復仇,虐渣女,除渣男,一手解毒救人,一手下毒懲治惡人,一路扶搖直上,沒想到竟與衡王戰鬥情誼越結越深,成為了人人艷羨的神仙眷侶。 不可思議,當真是不可思議啊!
120萬字8 17247 -
完結150 章

殷總,寵妻無度
姜綺姝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當她慘遭背叛,生死一線時救她的人會是商界殺伐果斷,獨勇如狼的殷騰。他強勢進入她的人生,告訴她“從此以后,姜綺姝是我的人,只能對我一人嬉笑怒罵、撒嬌溫柔。”在外時,他幫她撕仇人虐渣男,寵她上天;獨處時,他戲謔、招引,只喜歡看姜綺姝在乎他時撒潑甩賴的小模樣。“殷騰,你喜怒無常,到底想怎麼樣?”“小姝,我只想把靈魂都揉進你的骨子里,一輩子,賴上你!”
37.1萬字5 11927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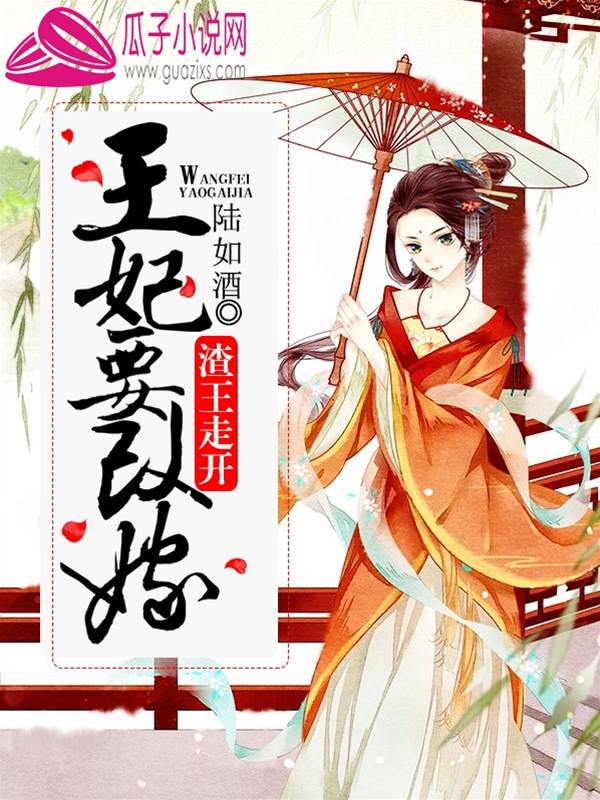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137 章

鶴帳有春
穆千璃爲躲避家中安排的盲婚啞嫁,誓死不從逃離在外。 但家中仍在四處追查她的下落。 東躲西藏不是長久之計。 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生個孩子,去父留子。 即使再被抓回,那婚事也定是要作廢的,她不必再嫁任何人。 穆千璃在一處偏遠小鎮租下一間宅子。 宅子隔壁有位年輕的鄰居,名叫容澈。 容澈模樣生得極好,卻體弱多病,怕是要命不久矣。 他家境清貧,養病一年之久卻從未有家人來此關照過。 如此人選,是爲極佳。 穆千璃打起了這位病弱鄰居的主意。 白日裏,她態度熱絡,噓寒問暖。 見他處境落魄,便扶持貼補,爲他強身健體,就各種投喂照料。 到了夜裏,她便點燃安神香,翻窗潛入容澈屋中,天亮再悄然離去。 直到有一日。 穆千璃粗心未將昨夜燃盡的安神香收拾乾淨,只得連忙潛入隔壁收拾作案證據。 卻在還未進屋時,聽見容澈府上唯一的隨從蹲在牆角疑惑嘀咕着:“這不是城東那個老騙子賣的假貨嗎,難怪主子最近身子漸弱,燃這玩意,哪能睡得好。” 當夜,穆千璃縮在房內糾結。 這些日子容澈究竟是睡着了,還是沒睡着? 正這時,容澈一身輕薄衣衫翻入她房中,目光灼灼地看着她:“今日這是怎麼了,香都燃盡了,怎還不過來。”
20.8萬字8.33 149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