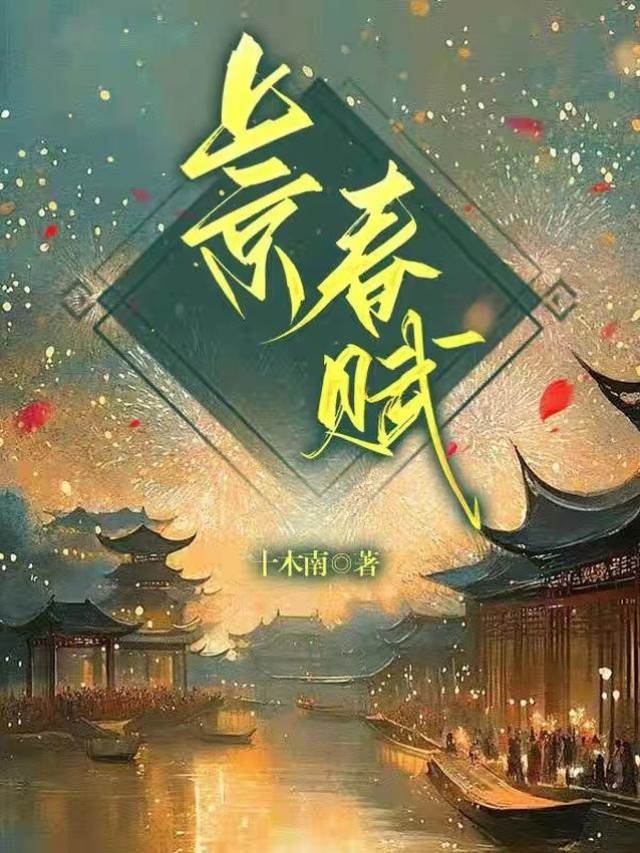《臣領旨》 45、第045章 昱王
許驕朝指尖哈了哈氣,在夜明珠上一點點寫上宋卿源幾個字,就像晨間醒來時的宋卿源,溫和,清澈,不染一雜質……
***
翌日晨間,敏薇來喚。
許驕迷迷糊糊中參雜了幾分惱火,“今日不早朝,我要睡到自然醒,天榻了也別我~”
但敏薇的腳步聲了屋中,“相爺~”
許驕扯了被子罩頭,“不在。”
敏薇笑道,“相爺,傅小姐來了~”
許驕無語,“哪個傅小姐?”
忽得,許驕整個人都醒了,頓時坐起來,“傅喬?“
敏薇笑嘻嘻點頭。
傅喬回京了?!許驕好像許久都沒有這麼高興的事了。
連忙下床穿鞋,又一面問道,“小蠶豆來了嗎?”
雖然不知道小蠶豆是誰,但是敏薇知曉傅小姐的兒跟著一道來的,敏薇頷首,“傅小姐帶了兒來。”
“wuli小蠶豆~”許驕換好服,見車岑士,傅喬和小蠶豆都在苑中。
聽到的聲音,岑士搖頭,傅喬驚喜,小蠶豆朝拋過來,“干娘~”
很快,又趕改口,“干爹~”
苑中都是許府的人,還好。
許驕抱起小蠶豆,“重了,高了,越來越好看了!”
小蠶豆摟著脖子笑。
許驕抱了小蠶豆上前,同傅喬笑道,“喬喬~”
“阿驕~”岑士略帶責備。
傅喬跟著笑起來,“正經一點,你是許相。”
許驕連忙清了清嗓子。
岑士頭疼,“難得傅喬來,我去做一只糖醋魚,你們說著話。“
“我想吃糖醋魚你都不做!“許驕抗議。
岑士道,“你要是像傅喬一樣聽話,我日日都給你做。“
許驕噤聲。
傅喬忍不住笑,小蠶豆也跟著笑起來。
Advertisement
“什麼時候回來的?”許驕這才問起。
傅喬道,“昨日晚些時候回來的,你這里太遠,今日才帶小蠶豆來。”
許驕又抱著小蠶豆舉高高,“要不要劃船,干娘這里有好大一片湖?”
小蠶豆“咯咯“笑開。
傅喬帶小蠶豆在許驕這里玩了一整日,許驕這里什麼都有,船,湖泊,還有湖泊后的小后山,還有家里的園,每一樣都讓小蠶豆覺得新奇又喜歡,和早前家中全然不一樣……還有岑夫人的糖醋魚實在太好吃……
岑夫人問起傅喬近況,傅喬說,先回家中侍奉父母。
許驕沒有吱聲。
等鄰近黃昏,傅喬和小蠶豆要回去了,許驕道,“岑士,我送傅喬和小蠶豆回去吧,正好明日要去寧州,我今晚住鹿鳴巷,明日也不用一早折騰了。”
岑士嘆了嘆,只得應好。
敏薇趕收拾東西,這一趟去寧州要大半月,來回怕是要到三月底了,六子和葫蘆會同去。
“岑士,我會想你的。”許驕還是從后摟著脖子,岑士拍了拍的手,“一路平安,娘就放心了。“
“放心吧~”許驕親了親,而后上前牽了小蠶豆的手,一起上了馬車。
岑士眼眶微微有些紅。
傅喬帶著小蠶豆,讓想起了許驕的爹剛過世的時候,帶著許驕的時候。
一晃,都這麼大了。
“岑士,我會盡早回來的~”許驕揮手。
岑士笑了笑。
***
今日玩了一整日,小蠶豆有些累了,上了馬車不久就在傅喬懷中睡了。
等傅喬睡了,許驕才道,“喬喬,鹿鳴巷有我的宅子,你要是有難的時候,就去那里避一避。”
許驕說完,傅喬愣住。
許驕沒有破。
Advertisement
昨日晚些才回京,怎麼會今日晨間就來這麼遠的地方看,應當是同家中起了爭執……
傅喬子溫和,又不太愿意表,在小蠶豆面前,又要掩藏更多,原本,應當也是想在這里呆一日再回家中的。
明日就要起程去寧州,有些不放心傅喬,所以才會同岑士說要送們一程……
“我哥哥嫂嫂的事……不提了,等你回來再說。”傅喬輕聲。
“鹿鳴巷,記得自己去,如果實在有事,讓人給我送信,我從寧州回來。”許驕沉聲。
傅喬笑了笑,“不會,就是口角沖突罷了,只是不想爹娘夾在其中氣,其實,長在旁人上,又怕別人說什麼,只是那時候我親,兄長和嫂子覺得朱家高攀,眼下有些落井下石,不想讓孩子聽見。”
傅喬一向溫婉,能說方才那句話,不知道這口角沖突當有多難聽……
許驕心里有些不舒服。
……
馬車繼續駛到了傅府外的街道上,許驕起簾櫳,傅喬和小蠶豆下了馬車。
許驕不舍,“記住了,有事讓人送消息給我。我在寧州的時候,你要是不開心,就去鹿鳴巷避一避。”
傅喬應好。
傅喬又同小蠶豆道,“同干娘再見。”
小蠶豆做了口型,“干娘~”
而后才是朗聲再見。
許驕的心好了些,目送他們母二人回了傅府,許驕才讓六子駕車回了鹿鳴巷。
只是到許府外時,見有暗衛朝拱手,六子去停馬車。
許驕時,見屋中的燈是亮的,清燈在窗戶上映出一道悉的影,悉到看一眼就知曉是他。
手中拿著折子,一手握著筆,認真專注許久未。
許驕,宋卿源也明顯愣怔。
Advertisement
許驕一面拖下外袍,一面道,“你怎麼在?”
宋卿源淡聲,“你不在,我就不能來嗎?”
淡聲里又著慣有的溫和。
許驕臉微紅,沒有應聲,捧著那枚錦盒去了床頭一側,將夜明珠拿出來,放在床頭,而后才折回。
“我去沐浴洗漱。”知會一聲。
“嗯。”他仍低頭看著冊子,輕聲應了聲,沒有抬頭。
許驕回頭看了看他,依舊在認真專注,屋中都是他上的白玉蘭香氣混著龍涎香的味道,是宋卿源的味道……
耳房里,許驕寬了浴桶。
仰首靠在浴桶邊緣上,目空著天花板出神,想起昨日岑士的一番話,想起傅喬和小蠶豆,又稀里糊涂想起方才看到宋卿源時,他那句,你不在,我就不能來嗎?
許驕忽然想,他是將這里當了家……
這個念頭在許驕腦海中一閃而過,也讓許驕再度失神。
良久,許驕都還在對著銅鏡頭,一直在出神想著什麼,宋卿源時,見出神模樣,“阿驕?“
許驕回過神來,“在想事。”
他是見許久沒出來,進來看。
“我馬上出來。”許驕話音未落,他上前,拿了手中的巾給頭,鼻尖都是他上的白玉蘭香氣,不由手抱了抱他的腰。
“怎麼了?”宋卿源覺得有些不對,但又說不好。
“抱抱龍不讓抱嗎?”開口卻又是胡謅,宋卿源寬心。
“別著涼了。”他給頭。
埋首在他腰間不肯出來,“許驕!”
他知曉多半又要開始鬧騰,果不其然,耳房里水汽裊裊,的手不老實,他沉聲,“折子沒看完,別鬧……”
換個地方了。
“許驕……”
Advertisement
再換個地方。
“……阿驕”
再等手不老實,他俯將了下去,銅鏡里映出綺麗繁華的幕幕,許驕附耳,“宋卿源……我真的很喜歡你……”
他回應的是熾熱的親吻,擁上九霄云端,也拽落繁花谷底。
……
時候尚早,他繼續看他的折子,在他后話癆,“說,你是不是很喜歡我?”
“……”
“我不在,你還來,是不是睹思人?”
“……”
“宋卿源,你是不是喜歡死我了?”
宋卿源終于看不進去折子了,“有病……”
許驕笑開。
宋卿源知曉是在捉弄他,惱意道,“你膽子是越來越大了!”
許驕忽然不鬧了,換在一側托腮,“宋卿源,我要是死了,你是不是很傷心?”
宋卿源看,“掀了棺材板,挫骨揚灰。”
許驕莫名抖了抖,抱著引枕回去睡了。
宋卿源低眉笑了笑。
……
許驕很久才睡著,再晚些時候,后人上了床榻,擁住睡著。
翌日醒來,宋卿源已經不在了。
早朝何時見天子遲過?
要同羅友晨出發去寧州了,今日不用去早朝,這一覺睡到了自然醒,許驕已經很是滿足。
起更的時候,見案幾上留了紙條。
許驕上前。
——早歸。
許驕目怔了怔,他總能中心中……
***
許驕出門的時候已經有軍在門外等候了,“許相!“
許驕頷首。
一深紫的府,顯得神奕奕,踩著腳蹬上了馬車。
馬車緩緩往北城門去。
今日會在本城門外十余里集合,而后出發前往寧州,寧州所轄好幾座城池,今晚會在驛館落腳,明日就會抵達寧州一行的第一站,節城。
馬車中放了打發時間的書,許驕隨意翻了翻。
從鹿鳴巷去北城門有些時候,許驕聽到馬車外的喧嘩聲,似是有人打馬而過,但很快,的馬車停了下來?
有軍在,誰這麼大膽子?
簾櫳掀起,是魏帆。
“你怎麼又來了?”許驕看了他一眼。
魏帆上前,“你不是去寧州嗎?給。”
他遞上袋子,袋子里是一枚糖葫蘆。
許驕愣住,“你跑來給我送糖葫蘆?”
魏帆輕聲,“你不喜歡嗎?路上吃。“
許驕眉頭微微攏了攏,“魏帆,你太殷勤了……”
魏帆笑,“男的對的殷勤能有什麼事?”
許驕想起他著急在岑士面前討喜的模樣,眉頭攏得更深,“魏帆!”
魏帆起笑了笑,“我心向明月,明月照渠。“
許驕“啪“的一聲將袋子放回他懷里,“我不是明月,我是太,不高興的時候曬死你那種!”
魏帆愣住。
……
魏帆都不知自己是怎麼被轟下來的,看著手中的糖葫蘆,喪氣得啃了一口,“好心當驢肝肺!”
馬車上,許驕被魏帆胡攪一通,沒有心思再看書了,想起這一趟說半個月,恐怕,至一個月是有了,宋卿源不會猜不到,只是兩人都沒點破。
如果半個月,才不需要在政事堂和翰林院將事待得這麼清楚。等回來不是三月初,而是三月中,興許三月末了……
***
明和殿,宋卿源沒心思看奏折。
許驕走的第一日,史臺在早朝時奏本,是天子尚無子嗣,后宮空置,搖國之本,讓江山社稷不穩,奏請天子盡快充盈后宮。
史臺奏本,朝中老臣紛紛響應。
尤其是之前梁城之,讓朝中再次將目集中在后宮空置之事上。
大監看他。
大殿上,他沉聲道,“朕心中有數,等梁城之事與恩科結束再議。”
……
大監知曉今日陛下心不好,好些員求見,都被大監擋了回去,大監也不敢貿然。但相爺的東西送來,大監還是送去,“陛下。”
宋卿源看他,不知他今日怎麼這麼不知眼。
大監趕道,“相爺讓人送來的。”
宋卿源微微怔了怔,大監遞上,信封里是一頁紙。
正面是他早前寫的“早歸”兩個字,背面寫著“臣領旨”三個字。
大監見他目滯住,眉頭仍是沒開,默默退了出去。
宋卿源看著“臣領旨”三個字,他知曉是在同他打趣。
——說,你是不是很喜歡我?
——我不在,你還來,是不是睹思人?
——宋卿源,你是不是喜歡死我了?
——宋卿源,我要是死了,你是不是很傷心?
宋卿源眸間黯沉。
***
抵達節城,是第二日黃昏。
寧州知府和節城城守親自帶了黑的一群人來接。
簾櫳起,眾人躬,“見過相爺。“
許驕笑了笑,“我還以為你們怕看到我。“
寧州知府臉僵了僵,“怎麼會?相爺親臨,寧州有幸。“
許驕言簡意賅,“去衙門吧。“
節城城守驚訝,“給相爺準備了接風宴。“
許驕恍然大悟般,“不介意的話,接風宴上談春調的事也行,只是沒想到,這個節骨眼兒上了,還有功夫準備接風宴,應當是春調的事完了?”
節城城守間輕咽。
寧州知府也一臉尷尬。
許驕淡聲,“革職查辦了。”
節城城守僵住,趕跪下,“相爺!”
許驕沒有再聽后人的哀嚎聲,周遭都在想,相爺這是殺儆猴,這次春調是要真格了,只有羅友晨清楚,節城城守原本就在春調的革職名單里,相爺這是順水推舟。
從二月中,到二月末,再從二月末到三月初,許驕一連走了寧州的大半城池,吏的調任皆在城中完,一氣呵。
三月初的時候,許驕抵達寧州婺城了。
婺城的吏二話不,在城外就將春調的名冊和計劃全部列好,羅友晨看過,心中唏噓,這近來幾日所到的城池都是如此。
婺城是最后一站,婺城邸看過所有這一路的資料,許驕忽然覺得可以給放個假,在婺城吃條魚,然后收拾收拾,明日回京。
等到驛館的時候,見有值守的侍衛在,不像是婺城的侍衛,驛館掌吏道,“相爺,昱王在。”
昱王?
許驕詫異,宋云瀾?
驛館掌吏道,“昱王來婺城見大夫,相爺前腳去了邸,昱王后腳來了驛館,突然,來不及知會相爺一聲。。”
昱王弱多病,幾乎都在養病,不怎麼面,這些年宋卿源給他找了不大夫都不見起,聽聞他也在四求醫,南順的,蒼月的,長風的名義都求過,但始終沒見好,眼下到了婺城,說不定又是什麼所謂的神醫偏方……
許驕道,“既然昱王病著,不沖撞了,我去邸落腳,先替我通傳。”
昱王在,怎麼都要拜見之后再走。
驛館掌吏帶路。
婺城這樣的地方很小,平日里很清靜,不會有太多人來,驛館的苑子也很靜,又尤其是三月暖春,清靜里都著春意。
驛館掌吏領了許驕至一苑落前,許驕駐足,伺候的人見了,趕上前,“許相。”
許驕溫聲道,“聽聞昱王在,下來見。”
侍去通傳。
稍后,侍相迎,“相爺請。”
許驕跟著侍,屋中有濃郁的藥味和檀木香參雜在一的味道,應當是覺得藥味難聞,所以點了檀木香沖淡。
“王爺,相爺來了。”侍出聲。
許驕拱手,“許驕見過昱王。”
屏風前的人淡淡抬眸看,聲音溫和,“許相免禮。”
許驕小時候見過昱王幾次,因為那時昱王還在京中,所以必要的宮宴都會出席,在宮宴上見過昱王幾次。
后來宋卿源登基,登基大典上,見過昱王一次,而后昱王就去了封地,再沒回京過,在許驕印象里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都是遠遠看了一眼,沒有細看過。
眼下宋云瀾出聲,許驕起看他,稍稍有些愣住。
宋云瀾……和宋卿源很有些像……
早前還覺得宋昭和宋卿源掛像,眼下才覺宋云瀾比宋昭像多了。可明顯,宋云瀾一幅病秧子模樣,人的格也溫和許多,不過一兩句話的功夫,咳了好幾次……
許驕說不好。
雖然宋云瀾的模樣溫和,但眼神仿佛藏了東西,總給不怎麼好的覺。
像是,又不像是。
許驕閱人無數,直覺總是有的,但不好輕易蓋棺定論。
“本王聽說了,許相來了寧州督辦春調,今日剛至婺城。”宋云瀾又掩袖咳了兩聲,“陛下得許相,得一良才。”
許驕拱手,“為君分憂,乃微臣本份。”
宋云瀾看,“許相一人撐了半邊朝政,換了旁人,怕是陛下都不信任。”
許驕看他,“朝中良才諸多,人才濟濟,蒙陛下垂青,清和僥幸。”
宋云瀾笑,“許相不必自謙,本王不在朝中,對許相也多有耳聞。難得在婺城,本王也想念陛下了,還請許相帶幾句話給陛下,不知明日可能出半日時間?”
婺城春調之事已經看過,明日確實沒事,稍加打聽就知曉。昱王開口,又打著讓捎話給宋卿源的名義,不好婉拒。
……
從苑落出來,許驕沒有再去邸。
左右明日還要同昱王一半日,方才照面過了,昱王讓就在驛館落腳,反正明日半日過后就要折返京中,也不折騰了。
夜里歇下,許驕想,終于快回京了。
作者有話要說:發得急,可能有錯別字,稍后修改
今天也是勤的一天
猜你喜歡
-
連載47 章
情絲
我是無情道中多情人
53.8萬字8 9569 -
完結268 章

死後第一天,乖戾質子被我親懵了
【雙潔 甜寵 雙重生 宮鬥宅鬥】 【絕美嬌軟五公主×陰鷙病嬌攝政王】 前世,她國破家亡,又被那個陰鷙病嬌的攝政王困在身邊整整兩年。 一朝重生十年前,她依舊是那個金枝玉葉的五公主,而他不過是卑微質子,被她踩在腳下。 西楚國尚未國破,她的親人母後尚在,一切都沒來得及發生…… 看著曾被自己欺負的慘兮兮的小質子,楚芊芊悔不當初,開始拚命補救。 好吃的都給他。 好玩的送給他。 誰敢欺負他,她就砍對方的腦袋! 誰料病嬌小質子早已懷恨在心,表麵對她乖巧順從的像個小奶狗,結果暗戳戳的想要她的命。 少年阿焰:“公主殿下,你喂我一顆毒藥,我喂你一隻蠱蟲,很公平吧!” 然而此時的少年並不知道,上一世的他早已對小公主情根深種,那位已然稱霸天下的攝政王,豁出命也想要給她幸福。 攝政王對不爭氣的少年自己氣的咬牙切齒:“你要是不行換我來!”
48.9萬字8.33 15703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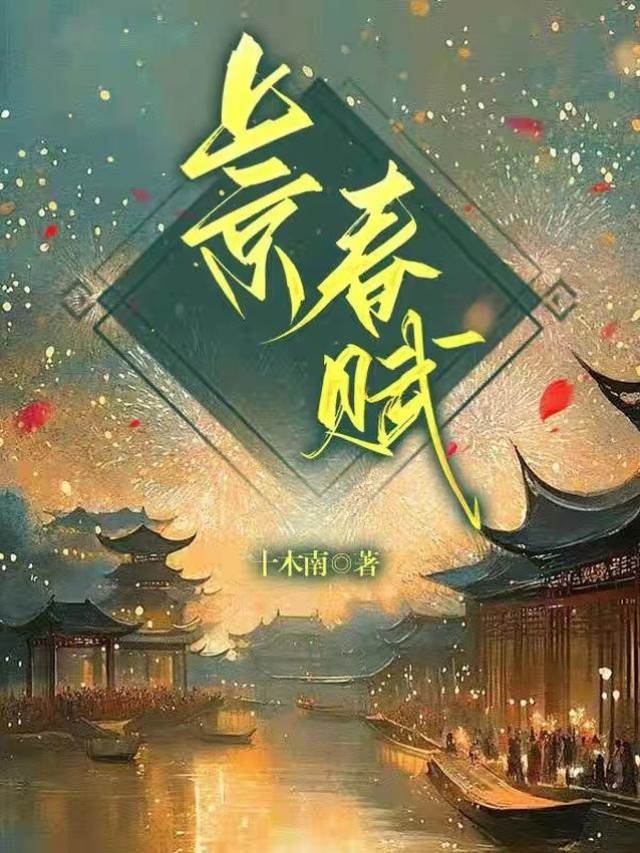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