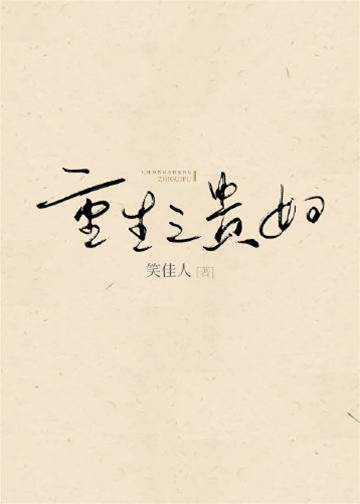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一品村姑》 隔生死周伯升父子重逢
周伯升不是什麼正經的蒙學先生,雖說從三字經教起,可沒幾日小丫頭就把三字經上的字認了,雖說用筆寫出的大字歪七扭八的不是樣兒,筆畫卻一點兒沒錯,著實是塊讀書的好材料,便索棄了三字經,挑揀了那淺顯一些的詩詞歌賦口傳心授。
一開始怕功課太深,這丫頭吃力,誰想到,跟三字經一樣,他不過誦讀兩遍解一遍,小丫頭就差不多能背下來通曉意思了,沒幾日竟是教了小半本詩經進去,越發來了興緻,倒把教學生當了正經事兒干。
這裏周伯升客串先生,客串的正得意,哪想到家裏頭因為他音信全無,早已慌了手腳,這周伯升是個地道的讀書人,家道原也只算平常,食不愁而已,指他鑽營銀錢家業也無甚指,周家從上到下,歸總起來也都是些只會花不會賺的主子,眼瞅著坐吃山空不是長久之計,周伯升的爹娘遂生了個主意出來。
周伯升十八上,父母做主娶了妻子王氏,乃是他的兩姨表妹,這王氏雖沒念過多書,家裏卻殷實富庶,祖上傳下來城底下的幾傾地,俱都是沃良田,每年的糧食米粟吃都吃不清,王家老爺又會鑽營,在城裏跟人,做起了買賣,幾年過來倒混上些面。
因跟周伯升的爹是連襟,便就近做了親,圖的是個名聲,周家家私雖不多,卻是世代書香,也算一門如意親事。
這王家人丁單薄,雖妻妾不卻只得了一個閨,銀錢田產陪嫁過去不知多,借了王家的東風,周家便富了起來,更加上這王氏從小跟在父親邊,雖是個丫頭,那世俗買賣上的營生,卻也學了七八。
到了周家,持外,填了幾買賣,等二小子周子明落生后,便舉家遷前後三進的新宅院裏,填了諸多婆子丫頭小廝家丁,呼奴喚婢,已是富甲一方。
Advertisement
王氏雖能幹,可也知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道理,因此一直督促丈夫苦讀,兩個兒子一到開蒙的年紀,就早早請了先生進府,也不知是運氣不到,還是怎的,舉人倒是中的早,可京城三年一次的科考,趕了四趟都名落孫山,眼瞅著兒子一天天大了,王氏便把那功名利祿之心轉嫁到了兒子上。
周伯升卻不服氣,念了半輩子書,舉人也中了,可就卡在科考上,如今眼瞅著已界不之年,連個一半職都沒混上,覺得面無,這一年不顧妻子苦攔狠勸,剛冬,便只帶了兩個書上路了,弄的王氏生了好幾日閑氣。
其實王氏也不是非要攔著丈夫,只不過這冬底下,天寒地凍,路也不好走,中間還隔著一個年呢,橫豎春闈要等到來年,過了年再走也不遲,再說,王氏前兒些日子去廟裏燒香,求了個簽文,解簽的和尚說,今歲不宜出行,恐有命之憂,王氏便記在心裏,偏周伯昇平日雖不理府里是事兒,這個時候卻執拗起來,非走不可,最終還是去了。
他這一走,王氏就見天的提心弔膽起來,連個安穩覺都睡不踏實,跟邊的丫頭婆子每日裏就念叨,也不知走到哪兒了,也不知那邊可落了雪,一會兒擔心帶去的棉太薄,一會兒又擔心兩個書伺候的不得力,盼著丈夫報平安的書信早到家門,一日便讓丫頭去前面問上十來遍。
要說從這裏走到京城,別說還坐著車馬,就是走路兩個月也該到了,論理說臘月里肯定能到,可就是連點音信都沒有,想起那個簽文,王氏越發后怕,忙遣了兩個得力的家丁,讓沿路去尋。
這邊家丁剛出去沒幾日,周伯升的家書便到了,王氏大喜,忙把兩個兒子到婆婆屋裏,讓大兒子周子聰念來聽,聽得遇上強盜,搶了馬車財,婆媳兩個唬的臉都白了,后聽得遇上恩人才鬆了口氣。
Advertisement
既知道在蘇家安,婆媳兩個便商量著,誰去走這一趟妥當,畢竟周伯升在信里囑咐要多帶去些銀錢,以答謝蘇家救命之恩,這銀錢戴在上,只遣了家丁恐不妥當,可旁人……
公公去的早,王氏跟婆婆畢竟是婦人,大兒子周子聰倒合適,卻前兒著了寒,有些咳嗽,這一趟奔波勞碌過去,恐這小病釀大災,最後還是周老太太說:「不若讓子明跑一趟吧,過了年也十四了,這個年紀娶媳婦兒的也有,男孩子出去走走見見世面也是好的,多帶上幾個能料理事兒的小廝就是了。」
於是周子明帶著幾個小廝第二日便匆匆走了,一路倒也順遂,到了定興縣城外的蘇家莊正是正月二十九。
蘇家雖是莊戶人家,過起年來倒頗有些民俗風味,蘇採薇參與其中過的也是有滋有味,過了臘八,蘇家就開始忙活起來,人人都忙,父親蘇善長把院裏地窖里儲的一些能吃的菜,倒蹬上來,趕在除夕前又跟弟弟,把被雪塌了的棚頂子用檁條搭上,鋪上稻草先住,等來年開了春再重新翻蓋。
蘇婆子跟母親劉氏,搭上姐姐明薇,從進了臘月就開始給全家人製過年穿的裳,鞋,忙著飛針走線,連抬頭的功夫都沒有,一家裏最閑的就是採薇。
因年紀小,病又剛好,加上借了念書的由頭,倒是明正大的懶起來,跪在椅子上在炕對面的桌子上一筆一劃的寫大字,這是周伯升給留的功課,每日十張大字,指孰能生巧,把字寫的像樣些。
說句實話,蘇採薇的字真不差,現代的時候練過一陣兒,只不過是筆,筆這樣趴趴的,用起來總不大順手,練了幾天找到了點兒訣竅,便好些了,寫出的字雖仍不算多好,至不想一開始那樣深一道淺一道的了,只是這手真冷,寫會兒就覺得發僵。
Advertisement
採薇放下筆剛要手,便有一個嶄新的暖手捂子,套在手上,棉花絮的很厚,想是在火上烤了,裏面又又暖,竟跟能暖到心裏頭一樣。
明薇道:「倒是正合適,既不喜歡靠著火盆便戴這個吧,寫字的時候,手冷了便暖暖。」蘇婆子道:「二丫頭這病好了卻越發古怪起來,竟把這些讀書寫字當個正經差事,若是個小子這樣寒窗苦讀的,說不準將來能把咱蘇家的門庭都改了,可惜是個丫頭。」說著,微微嘆口氣,劉氏臉一黯。
蘇善學從外面走了進來,蹲在在地上的火盆子上烤了烤手,蘇婆子忙問:「外面都拾掇好了?」「拾掇好了。」蘇善學答的利落:「大哥正在南屋裏看那周老爺給咱家寫對子呢,周老爺說了,對子要在門上是咱家的門面,就他寫,屋裏水缸柜子上的小福字就讓採薇寫就好了。」
蘇婆子一愣倒是笑了:「這話可是,二丫頭快多寫幾個福字,來年咱蘇家福氣多多。」又小聲對劉氏道:「我這麼算著,周家老爺的家書早該到了,怎的家裏還沒人過來?」
劉氏道:「來不來的有什麼打,咱家也沒指著報恩,媳婦兒琢磨著,縱是年前不到,過了年也該到了……」
正說著,就聽外面一陣馬嘶聲傳來,蘇婆子一拍大:「聽這靜可不是咱村裏那些撅的畜生,想是來了外客,八就是周家的人,趕的,咱們出去瞅瞅去,今兒可都臘月二十九了呢。」
婆媳兩人帶著明薇採薇出了屋,剛行到院裏隔著籬笆就看見外面停了兩輛馬車,車把式跟家丁一共來了六七個,都穿著半舊的棉襖棉,從前頭的馬車裏跳下一個十三四的年來。
Advertisement
外面一件石青緞的棉披風,裏面深赭綢緞棉袍,中間花青絛,打了福壽如意結,還沒看清五如何,已經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喊了聲爹,爺倆個抱頭痛哭起來。
險些生死相隔,周伯升如今見了兒子就如那隔世重逢一般,最後還是蘇婆子說了一句:「外面怪冷的,既已見了面,不如去屋裏敘話。」
這才一併請到了周伯升落腳的南屋裏,周子明見到父親住的屋子破舊不堪,地上雖點了個火盆,卻有些嗆人的煙氣,想在這樣的屋裏,爹竟然住了一個月,心裏不一酸。
周伯升卻道:「若不是你蘇家叔叔救的爹爹迴轉,說不得現在你連爹爹的墳頭都尋不到,還不跪下,給救命恩人磕頭。」
兒子畢竟年紀小,周伯升是怕言語不妨頭,說出什麼不中聽的話來,大過年的倒給人家添堵,周子明自來聰明,哪有不知道爹的心思,便下嫌惡之心,恭敬的跪下給蘇善長磕下頭去……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太子殿下你被逮捕了
世人皆讚,寧安侯府的四小姐溫婉寧人,聰慧雅正,知書達理,堪稱京城第一貴女,唯有太子殿下知曉她的真麵目,隻想說,那丫頭愛吃醋,愛吃醋,愛吃醋,然後,寵溺他。
134.7萬字8 8508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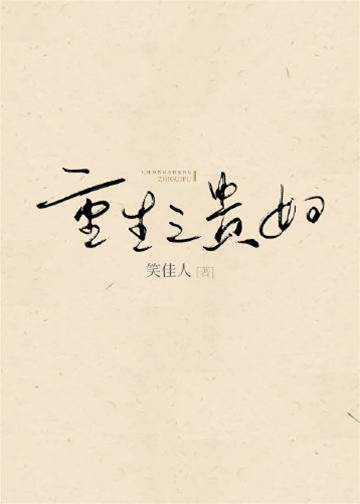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5840 -
完結322 章

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
蘇沉央一遭穿越成了別人的新娘,不知道對方長啥樣就算了,據說那死鬼將軍還是個克妻的!這種時候不跑還留著干嘛?被克死嗎?“啟稟將軍,夫人跑了!”“抓回來。”過了數月。“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抓回來。算了,還是我去吧!”…
86.3萬字8 86025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54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