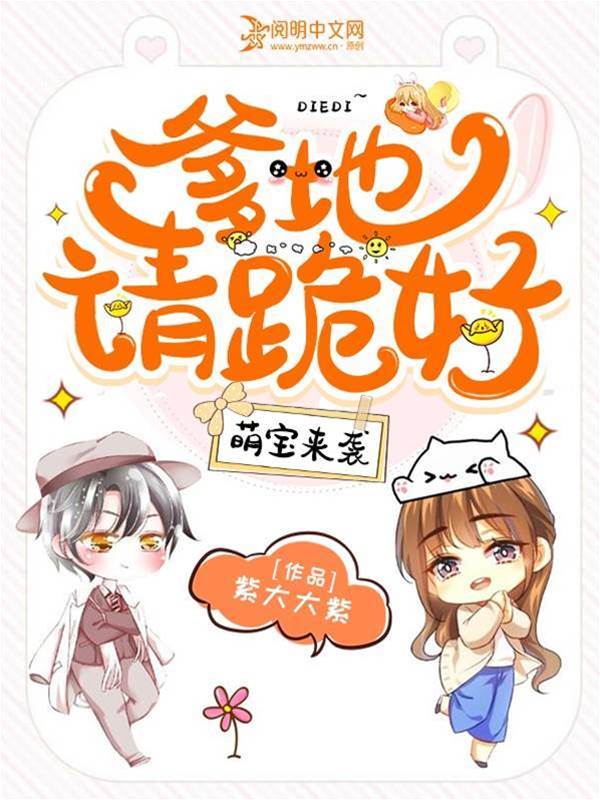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一筆玫瑰》 第76章 由不得你決定
蔣知歸的眼神同樣滿是戾氣,抓了一下額前的碎發,他半瞇著眼說道:“早就該還你這一拳了,晚了五年。”
臉頰上結結實實挨了早有預謀的一拳。
陸見淮角出了,他也沒顧,舌尖輕輕頂了一下,抬眼的一瞬間,眼眸里閃過一芒,而后再次握起了拳頭,想向另一個男人砸去。
大概僅有0.1毫米的距離。
“陸見淮!”
書杬脆生生的嗓音將他神智拉回。
眉心涌過一陣下墜,陸見淮斂起神,下頜線條繃了起來,抿直一條直線,毫無任何弧度。
的聲音仍然在耳邊盤旋,帶著埋怨與責怪,一邊扶起靠在墻上的另外一個男人,一邊問著:“你是瘋了嗎?”
心臟仿佛被狠狠了一下。
陸見淮痛苦地閉了閉眼。
瞬間被一無所適從的荒唐裹脅。
“嘭!”忽而有碗筷掉在地上的聲音。
書杬抬起眼睛看去,發現是那位老太太發出的靜聲,似乎沒見過這場面,明顯有些慌張了。
扶起地上那張摔倒的椅子,書杬付完餐費,包括還沒上的那些菜,轉頭對著兩個都了手的男人說道:“你們還不走麼?”
他們都沒賞過對方一個眼神。
然而走出小餐館,兩人又異常默契,一個往右走,一個往左拐,留給站在中間的書杬都只剩瀟灑背影。
書杬懵圈了幾秒鐘。
黑的公共垃圾桶里還砸著一束不知道誰扔的紅玫瑰花,紅與黑,層次分明到有些刺眼。
左邊也看了,右邊也看了,猶豫一小會兒,朝著蔣知歸的方向小跑追去,拉住他起來的一條手臂說道:“你還好吧?”
蔣知歸轉過頭,眼底染上幾分喜悅。
Advertisement
以及,勝利者的驕傲。
他搖搖頭,輕聲回答道:“沒事。”
接著,書杬臉上浮現過有的歉意,細聲說著:“我替他和你道歉,真的很對不起,我一定會好好問他是怎麼回事的。”
傍晚與黑夜替,幾顆暗淡的星辰陡然出現。路邊的樹葉被風吹得“簌簌”地響,著濃厚的霧水,有幾分春天獨有的蕭條景致。
蔣知歸從心底蔓延起一陣無力,收斂起眼睫,啞著嗓子問道:“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你替我向他道歉。”
在書杬的沉默不語里,他才多出幾分唐突后的歉意,很快將這個不太好的話題一筆帶過,瞥了眼自己停在不遠的車子,問道:“送你回家?”
書杬回答:“不用。”
蔣知歸并沒有過多強求,抿著,溫地說道:“那好,下次我請你吃晚餐吧。”
另一邊相反的方向。
陸見淮只知道跟著月亮走。
半晌之后,他第三次刻意放慢腳步,也聽不到后有什麼跟過來的靜聲時,氣得踹了一腳汽車胎。
然后不服氣地回頭看著。
直到視線里真的有書杬的背影出現,他還不可置信地了眼睛,邊也漾起不可抹滅的彎度。
在人立定時,又變了一副寡淡的模樣。
仿佛什麼都不放在心上。
“你剛才是怎麼了,為什麼要一上來就揍人?”書杬瞪著眼睛認真問道,長而卷翹的睫還掩蓋住了眼眸里的幾分怒火。
陸見淮不以為意,角還作痛著,他回答道:“我也挨打了。”
然而這五個字聽在書杬耳朵里,就覺得只是無理取鬧,氣的子都有些抖了:“那還不是因為你先無緣無故手打人家的嗎?”
Advertisement
而且店主還是一位老太太,萬一心臟不好了什麼刺激的,他要怎麼背起這個責任,表面看著吊兒郎當,其實小的時候一起喂的流浪貓走了,都能難過的人。
要是真的害死了一個人,不得自責愧疚到死麼。
后半句想的話,書杬沒有機會開口說。
眼前的男人嗤笑了一聲,將所有緒打斷。
他耷拉著眼皮子,眸清冷:“他活該。”
這三個字從真正意義上惹惱到了書杬。
如果單純以作為蔣知歸朋友的立場來看,其實更生氣,但因為對方是陸見淮,所以才想著先問問緣由。
安靜了一會兒之后,書杬抬起腦袋,說道:“陸見淮,你能不能點了啊?”
又不是十幾歲了,還總打架。
然后自己也了傷。
都出了,肯定很疼。
“我不。”陸見淮滿眼促狹,角微微下著,也是氣話,他徑直說道:“那你去找你那個初啊,他。”
反正從上高中開始起,被渣的那個人又不是他。
不長記,直到現在幾年過去了,仍然往上湊的人也不是他,俗話還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呢。
當年為那男的哭那副鬼樣子。
是真的都忘了麼?
該死的初。
書杬也不是一個善于把壞脾氣藏著掖著的人,尤其對方還是陸見淮,不爽的緒更是直沖云霄。
聽完他說的話,回答道:“陸見淮,你現在就是在沒事找事,莫名其妙出現,莫名其妙打人,還莫名其妙和我說這種話!”
話音剛落,陸見淮轉就走了。
背影被月照出一道斜影,細細長長。
這好像還是第一次,吵完架,他扭頭就走,然后一點都沒有要再回來的意思。
Advertisement
書杬真的氣到不行,對著不遠那道背影大聲吼道:“找他就找他,以后我們別再見面了!”
“再也不要見!”
眼眶都在不知不覺中潤了。
心臟像是被撕裂了兩半一樣的疼,難到窒息。
書杬低垂著腦袋,想要強行把奪眶而出的眼淚給憋回去。
泄了一地的月灑在的腳尖上,不遠的馬路上,鳴笛聲嗚嗚咽咽,世界在某一刻突然靜止,卻耳鳴了。
“轟隆隆”響著。
突然能聞到悉的古龍水的味道。
下一秒,書杬的下被攥抬起,接著,上上來了一個冰冰涼涼的東西。
陸見淮很用力,另一只手摁住了的后腦勺,瓣從啃噬到廝磨,所有燥熱的氣息直進嚨口里,熾熱纏綿。
書杬被吻到全發麻,里的所有都像是在逆流一般。
的腦袋暈乎乎的,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出來。
在被松開息的那幾秒鐘里。
陸見淮在耳邊,輕輕著氣,嗓音沙啞而低沉,帶有一狠戾的威脅:“要不要跟我見面,由不得你決定。”
猜你喜歡
-
完結759 章

慕川向晚
千年難得一遇的寫作廢柴向晚,因為書撲成了狗,被逼相親。 “媽,不是身高一米九腹肌十六塊住八十八層別墅從八百米大床上醒來的國家級高富帥,一律不要。” “……你是準備嫁蜈蚣?” 后來向晚終于如愿以償。 他被國家級高富帥找上門來了,撲街的書也突然爆火—— 有人按她書中情節,一比一復制了一樁命案。 而她與國家級高富帥第一次碰撞,就把人家給夾傷了…… …… 愛情、親情、倫理、懸疑、你要的這里都有,色香味俱全。 【本文狂撒狗血,太過較真的勿來。】
178.1萬字8.09 16781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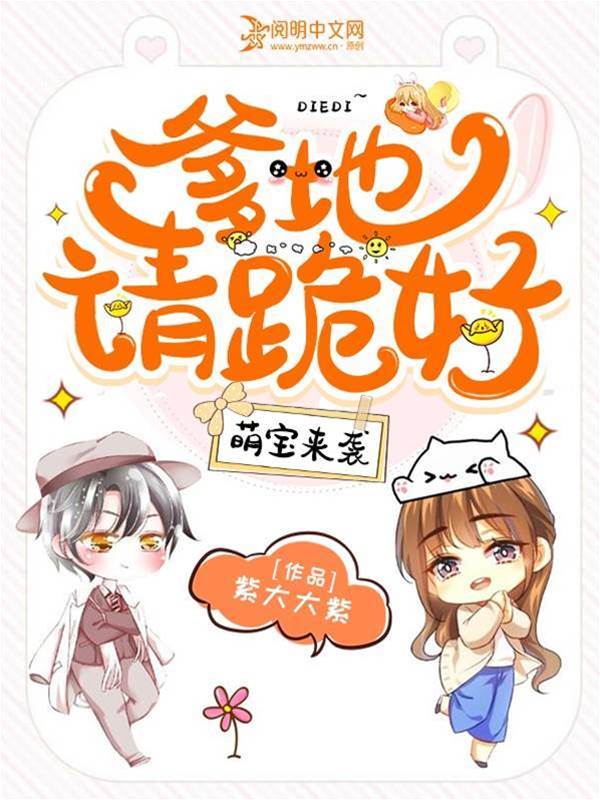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連載339 章

小啞妻死後,千億總裁在墓前哭成狗
一紙離婚協議,喬明月挺著八個月的肚子被趕出薄家。卻不幸遇到車禍,她瀕臨死亡之際,才想到自己的真實身份,不是啞巴,更不醜,而是名動雲城的喬家大小姐!她憤恨、不甘,最終選擇帶著孩子獨自生活,順便虐渣打臉。誰知五年後,孩子的親生父親卻回到雲城,甚至還想讓她嫁給別人!喬明月冷哼一聲,磨刀霍霍預備宰向豬羊!多年後,薄時琛懊悔不已,本該是他的妻,卻兜兜轉轉那麼多年,才重回他的懷抱。
61萬字8 6030 -
完結142 章

他等我分手很久了
莊斐和男友,以及男友的好兄弟陳瑜清共同創立了家公司。陳瑜清以技術入股,對經營的事一概不問。 莊斐和男友經營理念出了分歧,經常意見相左。每每這時,他們就要徵求陳瑜清的意見,試圖以少數服從多數來讓對方妥協。 可陳瑜清總是沒意見,來回就那麼幾句——“隨便。”“你們定。”“我怎麼樣都行。” 他甚至還能幫他們關上會議室的門,懶洋洋地站在門口喊:“你們先吵,吵完了叫我。” - 莊斐離職,幾個要好的同事爲她舉辦了一場狂熱的歡送會。一慶仲裁庭裁決拖欠多年的勞動報酬到手,獲賠高額賠償金;二慶擺脫渣男,恢復自由之身。 森林酒吧裏,渣男的好兄弟陳瑜清不請自來。 莊斐喝醉了,姿態嬌媚地勾着陳瑜清的脖子:“反正你怎麼樣都行,不如你叛了他來幫我?” 不料,厭世主陳瑜清反手扣住她的下巴,毫不客氣地親了下去,無視一羣看呆了的朋友。 他側在她耳邊低語:“既然你那麼恨他,不如我叛他叛個徹底?”
21.4萬字8.18 7874 -
連載455 章

終極火力
這個世界不只是普通人熟知的模樣,還有個常人不會接觸的地下世界。政府特工在暗中處理麻煩,財閥雇養的殺手在私下解決問題。有殺手,傭兵,軍火商,還有特工,有把這個世界
99.5萬字8.18 30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