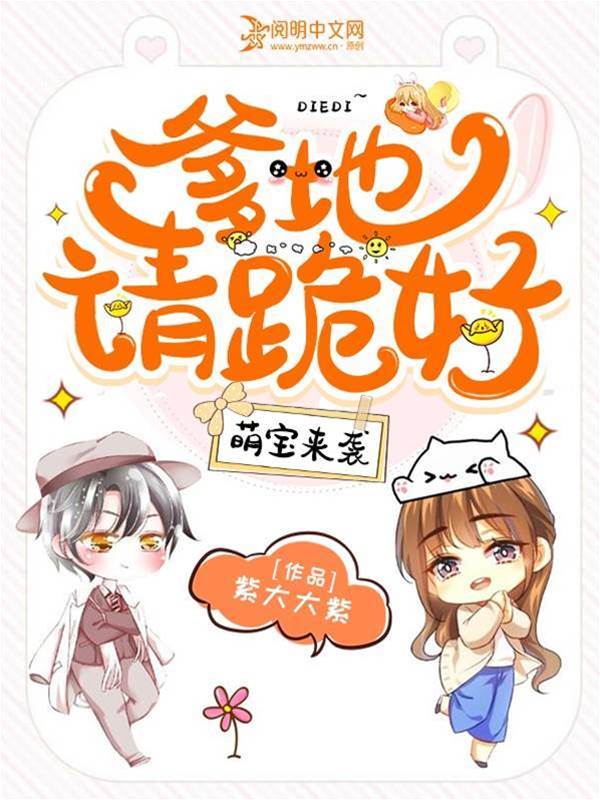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于她深吻九萬次》 第173章 你再親我
湊什麼熱鬧,電梯開了,一同進去不就是趁著方便嗎。
傅琮凜:“喲,了解得可真清楚。”
時綰閉。
怕自己想呼他一個大子。
……
唱歌的地方趙閑早就安排好了,外面還有車停著。
傅琮凜沒跟車走,帶著時綰自己開車。
時綰剛坐進去,屁都還沒坐穩,手就被人著,影投下來,在還沒反應過來之際,后腦勺便被扣住,鋪天蓋地的滿是侵略氣息的吻就落了下來。
疾風驟雨的帶著濃濃的懲罰意味,男人的舌勾纏著,霸道蠻橫又強勢的,幾乎讓不過氣。
時綰試著推搡他,被傅琮凜制住,等臉都憋得通紅,呼吸都重了些,傅琮凜才緩緩松開,又依依不舍的在角咬了一口。
時綰吃疼,悶哼了一聲,睜開眼,眸泛水。
傅琮凜的手到的后頸了,啞聲道:“也就這時候你才乖點兒。”
Advertisement
平素里就不老實的跟他嗆聲,和他對著干。
時綰氣息不均,聲:“你過來。”
“嗯?”
“你再親我試試?”
傅琮凜不上當,在后頸的手轉了個方向,的耳垂,“想咬我?”
傅琮凜有過被咬破皮的經驗,又不是狂,自然不會送上去挨傷挨痛。
看著他,帶了點纏綿,嗓音發,“你過來就知道了。”
傅琮凜悶聲笑了下,丟了手,自己坐好駕駛座,慵懶啟,“現在時機不對,晚點兒讓你咬。”
他微偏頭,的結滾,眸深深地盯著慢條斯理,“想咬哪兒都行。”
時綰:“……開你的車。”
傅琮凜卻沒,想到什麼,從儲格里拆封了酒和消毒水,看向時綰,“手出來。”
時綰沒,“不。”
“,了不干凈的東西。”
Advertisement
時綰不解,“我什麼了?”
“野男人的手。”
“你麼?”
時綰自己不清楚,傅琮凜卻還記著,先前走廊里,時綰可著李岳的手了。
當時他看著就礙眼,礙于在外,著沒靜。
他自然不可能把這點小事說出來,不然時綰得說他小肚腸。
只一言不發的把時綰倔犟的手拽了過來,細細的消毒干凈。
而后又了自己。
時綰盯著自己的手,舉起來看了看,問了一個很早以前就想問的問題,“傅琮凜,你說你這麼潔癖,到底是怎麼活到這麼大歲數的?”
傅琮凜:“……”
“請注意你的用詞。”
時綰就笑了,還笑出了聲兒。
男人冷著臉,瞥了一下。
傅琮凜雖然有潔癖,但也沒到那種無時無刻都忍不了的狀態,他只是對于不的人,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喜他人親近。
比起生理,更偏向于心理上的潔癖,比如他能接時綰的親近,能接朋友的勾肩搭背,但換了人,就不行。
是以趙閑曾說過,想跟傅琮凜做朋友,還真不是簡單的事兒。
首先,得他的眼,再是順眼,而后看著不反,才接,其次才有進一步流的機會。
說他驕矜清冷不是沒有道理的。
猜你喜歡
-
完結759 章

慕川向晚
千年難得一遇的寫作廢柴向晚,因為書撲成了狗,被逼相親。 “媽,不是身高一米九腹肌十六塊住八十八層別墅從八百米大床上醒來的國家級高富帥,一律不要。” “……你是準備嫁蜈蚣?” 后來向晚終于如愿以償。 他被國家級高富帥找上門來了,撲街的書也突然爆火—— 有人按她書中情節,一比一復制了一樁命案。 而她與國家級高富帥第一次碰撞,就把人家給夾傷了…… …… 愛情、親情、倫理、懸疑、你要的這里都有,色香味俱全。 【本文狂撒狗血,太過較真的勿來。】
178.1萬字8.09 16781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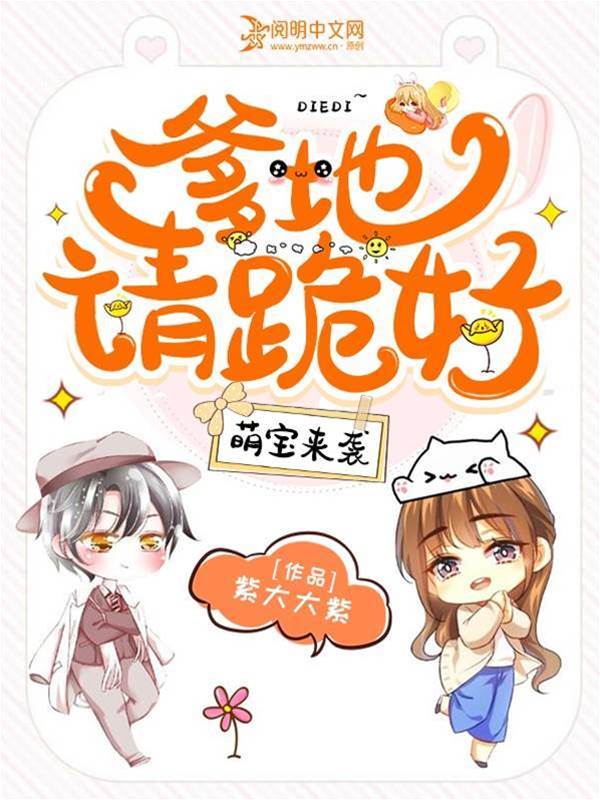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連載339 章

小啞妻死後,千億總裁在墓前哭成狗
一紙離婚協議,喬明月挺著八個月的肚子被趕出薄家。卻不幸遇到車禍,她瀕臨死亡之際,才想到自己的真實身份,不是啞巴,更不醜,而是名動雲城的喬家大小姐!她憤恨、不甘,最終選擇帶著孩子獨自生活,順便虐渣打臉。誰知五年後,孩子的親生父親卻回到雲城,甚至還想讓她嫁給別人!喬明月冷哼一聲,磨刀霍霍預備宰向豬羊!多年後,薄時琛懊悔不已,本該是他的妻,卻兜兜轉轉那麼多年,才重回他的懷抱。
61萬字8 6030 -
完結142 章

他等我分手很久了
莊斐和男友,以及男友的好兄弟陳瑜清共同創立了家公司。陳瑜清以技術入股,對經營的事一概不問。 莊斐和男友經營理念出了分歧,經常意見相左。每每這時,他們就要徵求陳瑜清的意見,試圖以少數服從多數來讓對方妥協。 可陳瑜清總是沒意見,來回就那麼幾句——“隨便。”“你們定。”“我怎麼樣都行。” 他甚至還能幫他們關上會議室的門,懶洋洋地站在門口喊:“你們先吵,吵完了叫我。” - 莊斐離職,幾個要好的同事爲她舉辦了一場狂熱的歡送會。一慶仲裁庭裁決拖欠多年的勞動報酬到手,獲賠高額賠償金;二慶擺脫渣男,恢復自由之身。 森林酒吧裏,渣男的好兄弟陳瑜清不請自來。 莊斐喝醉了,姿態嬌媚地勾着陳瑜清的脖子:“反正你怎麼樣都行,不如你叛了他來幫我?” 不料,厭世主陳瑜清反手扣住她的下巴,毫不客氣地親了下去,無視一羣看呆了的朋友。 他側在她耳邊低語:“既然你那麼恨他,不如我叛他叛個徹底?”
21.4萬字8.18 7874 -
連載455 章

終極火力
這個世界不只是普通人熟知的模樣,還有個常人不會接觸的地下世界。政府特工在暗中處理麻煩,財閥雇養的殺手在私下解決問題。有殺手,傭兵,軍火商,還有特工,有把這個世界
99.5萬字8.18 30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