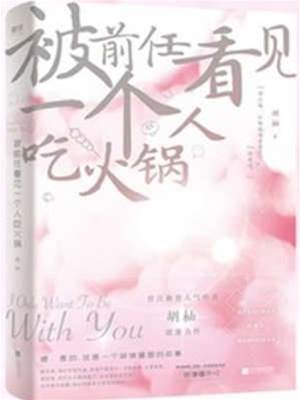《于她深吻九萬次》 第233章 鳥為食亡
夜。
江潔按響了門鈴。
來開門的是個人。
穿著松松垮垮的睡袍,大片的暴在空氣中,上面留有或深或淺的曖昧印記。
人倚靠在門邊,淡淡的掃了一眼,眸底輕蔑之意明顯,一句話也沒說就轉進去了。
里面的男人隨意一問:“是誰?”
經過了一場愜意的魚水之歡,謝安穎渾都散發著慵懶的氣息,聞言掀眸,似笑非笑的哼聲,“來找你的。”
蔥白的指出去漫不經心的過男人赤著的膛,“這麼晚都還來找你,倒是會挑時候。”
聞厲鶴垂眸,深深看一眼,將的手抓著拿開,自己攏了下睡袍。
謝安穎低嗤:“這會兒倒是守如玉起來了。”
男人輕笑:“為你?”
謝安穎掙開他的手,拂開他頭也不回徑直往里走。
窈窕的姿有幾分輕狂。
聞厲鶴到了外廳才看見沙發上坐著的人。
聽見靜,江潔猛地抬頭看向他,臉有些許蒼白。
“找我有什麼事?”
男人剛洗過還半著的中長發卷卷的隨意搭在耳畔,隨著他低頭拿煙的作,掉下來幾縷,襯得側臉廓深邃。
江潔了,“他在查我了。”
聞厲鶴挑眉,偏頭點燃煙,大剌剌的坐在沙發上,疊起修長的雙,行為舉止很是放浪肆意。
“那又如何?”
江潔有些激,“你不是說的會保全我嗎!”
明亮的燈下,的面容有些猙獰。
“找上來了嗎?”男人不不慢的一句反問。
江潔霎時一僵,訥訥道:“沒有。”
“那你著什麼急?”
江潔心里憋了一口郁結的氣,臉格外難看,“他都已經找到我家去了,還去看了我媽!”
Advertisement
“誰讓你蠢。”
“你——!”
“我什麼?”
男人還是那副姿態從容的神,江潔心思稍沉,“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這是你的私事,跟我有什麼關系。”
江潔驀地站起來,臉繃得的,攥著手,指甲陷進手心的皮里,“你想過河拆橋?”
“從沒搭過,何來拆字一說。”
江潔咬,“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事都抖出去嗎,你現在這麼對我,別到時候你死我活,就算我遭殃也會拉個墊背的!”
聞厲鶴:“你大可以試一試。”
江潔深深地倒吸一口氣,知道自己肯定玩不過,只能忍下來。
“沒意思。”
一道音突然打破這晦的劍拔弩張。
在里間聽了個墻角的謝安穎,興致缺缺的走了出來。
走到聞厲鶴邊,抬旋即側坐在聞厲鶴上,單手摟著他的脖頸,帶了一魅的人香來。
江潔臉一沉,警惕的盯著謝安穎,“謝小姐,這是我和聞先生之間的事,你這麼做會不會太過了。”
指的,自然就是聽墻角這事。
謝安穎不以為然,手抬起來了聞厲鶴的臉,有些狎昵的意味,“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說完就從他里搶走了煙,遞到自己口中了兩口,又給塞回去,笑盈盈道:“你說呢?”
有屬于人的甜香在齒邊,聞厲鶴微微瞇起眼,看著這個在他上囂張又肆意妄為的人,嗓音沉沉:“你說的對。”
謝安穎哼笑,“算你識相。”
江潔就那麼站在那里,背脊僵直,眼底劃過一抹深深地嫉妒。
他們旁若無人的親昵舉,襯得愈發難堪。
跟謝安穎向來不合,謝安穎對的敵意很深,起初也以為是聞厲鶴對有意思,誰知道,不過就是他的墊腳石,利用完隨時都可以踹。
Advertisement
眼下謝安穎這般,無疑是狠狠地打的臉,讓無地自容。
江潔咬著牙,臉上閃過不甘心,“我也不想其他的,只想得到我想要的。”
“你想要的?”謝安穎翹起自己的手,看著指頭上的致甲,挲了兩下,“你是說人還是錢?”
江潔:“謝小姐——”
“我可沒想參與你的事,別把我當假想敵。”
那你就別!
江潔很想把這句話狠狠砸在謝安穎那張純天然妖嬈嫵的臉上,看了看聞厲鶴,迫不得已使勁把這話給吞了回去。
“我真的不懂,你為什麼非要盯著別人的肚子呢?你要是想,自己也可以生。”
江潔冷笑了聲,“謝小姐不知其中緣由,最好是別說話。”
謝安穎挑了挑眉,“我知道了,你想生,可傅琮凜不愿意啊。”
江潔額角跳了跳。
“打蛇七寸你知道嗎?一個人一旦懷了孕,那的肋就是孩子,那麼問題來了,在肚子里時,和生出來后,哪一個的威脅更大?”
謝安穎說這話的時候,模樣輕佻,口吻散漫,似漫不經意,卻仿若一道警鐘,猛地敲響了江潔。
“打擾了。”眼神有些復雜,低下頭拿起自己的手提包,步伐匆匆的朝外走。
室安靜下來,一支煙緩緩地完。
“滿意了?”男人慵懶的嗓音響起。
謝安穎起眼皮,神淡淡:“我有什麼好滿意的。”
聞厲鶴圈著的腰肢:“看不出來,你還有當劊子手的能耐。”
謝安穎呵了聲,“這可跟我沒關系,我只是隨口一說。”
“你猜會怎麼做?”
“不猜。”
謝安穎并不興趣,實際看不上江潔,無論從哪點來說,無法理解一個人的執念為何那麼深,明知道自己不能擁有,卻偏偏要強霸占。
Advertisement
這種人,說好聽點,是為癡狂,打著的名義做出些帶來傷害的事。
說難聽點,就是傻,人當自己,如果連自己的初衷都不能守著,就算是了,也都是帶著枷鎖。
不過終歸不在江潔的角度,沒經歷過的事,謝安穎也不好置詞,換個稍微平和的說法,那就是可憐。
可憐人必有可恨之。
……
時綰回時家沒打算跟張燕說。
之前兩人鬧了不愉快,張燕氣得好幾天沒睡好覺。
只是這次回去有些東西必須帶走,還是回了一趟時家。
張燕見著臉一點兒都不好。
“你回來干什麼?”
時綰面如常,“拿點東西。”
張燕一瞪眼:“拿什麼東西!這里還有什麼是你的,白眼狼,威脅你媽,刻薄我,你就是這麼為人子的嗎!”
時綰懶得跟吵。
知道是越吵越來勁。
直截了當道:“別攔著我,傅琮凜還在下面等著,我拿了東西就走。”
話音一落,就見張燕變了臉。
時綰有點想笑,冷笑。
搬出傅琮凜,張燕果然沒再為難,只上上下下,眼神犀利的打量著,跟在后,走哪兒跟到哪兒。
時綰全當不在。
張燕看著的肚子,看不出個什麼來,但就是篤定,“幾個月了?”
時綰瞥了一眼,沒理。
張燕也不氣餒,繼續問:“你以為你不說,我就看不出來嗎?你都是我生出來的,還想瞞著我!”
“您說什麼就是什麼。”
張燕氣得牙,覺得真是越來越叛逆了。
“傅爺那邊知道你懷孕了嗎?”
時綰沒吭聲。
張燕瞧著,心里一琢磨,就道:“好歹他們傅家家大業大,你懷的又是他們家金孫子,竟然還不讓你進門!”
Advertisement
那語氣頗為恨鐵不鋼。
“進什麼門,您在想什麼。”
張燕才不聽的話,直言道:“我是說一直問你,你要麼不說話要麼就否認,原來是傅家不承認你!”
氣急:“我早說了你要后悔!當初就不應該離什麼婚,現在好了,你要是不跟傅爺復婚,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個私生子!”
時綰的作重了些,表很淡:“私生子又怎麼了?”
“你還說怎麼了?”張燕指著,發狠道:“你這是在丟我們時家的臉!你又是個明星,要是有私生子這件事曝出去,看你怎麼辦!”
時綰這次回來就是來帶走小時候時父給做的手工小玩,都存放在一個木盒子里。
有些是被拿出來擺放在書桌上。
時綰仔仔細細的收拾著,也不搭腔了。
張燕對時綰有怨氣,但更多的是對傅家。
卻也不敢念叨出來,在了心里。
最后沖著時綰來了一句:“他們傅家,欺人太甚!”
時綰:“……”
.
時綰胎像較為穩定的度過了前三個月,害喜倒是沒那麼嚴重了,只是口味刁鉆,喜歡吃臭的還有酸的。
有天晚上傅琮凜回來,推門而就聞到了一尖銳刺鼻的意味,臉都黑了。
往里走一看,時綰正坐在沙發上,一邊看電影,一邊好整以暇的吃著榴蓮。
傅琮凜直接避開躲到了臥室里。
有點避如蛇蝎的意味。
這還不算是過分的。
傅琮凜時常能見吃什麼腸、螺螄,就連之前傅琮凜不允許吃的臭豆腐,都在外面的躲起來吃。
自從上次樓梯間的事后,傅琮凜就給時綰邊安了人,只要出門,就的跟著。
一般時綰做了什麼,都會事無巨細的匯報給傅琮凜。
時綰那點小把戲,在傅琮凜跟前完全沒藏的余地。
他也未過多干涉,只要別太過分就行。
因著奇怪的癖好,傅琮凜有幾天晚上沒跟時綰一起睡。
起初時綰還答應得好好的,說不跟他說就不睡,也不稀罕,竟然還敢嫌棄臭。
結果到了夜半就跑過來敲傅琮凜的門,每每把傅琮凜吵醒。
男人沉著臉,帶著一臉倦意的打開門,就看見時綰抱著枕頭,可憐的站在門口,仰著臉看他,撅著說:“我睡不著……”
傅琮凜是被折騰得一點脾氣都沒了。
讓了位置把人迎進來,也不忘奚落兩句:“不是說不稀罕嗎?過來做什麼。”
時綰:“我冷還不行嗎?”
傅琮凜駁了拙劣的借口:“冷有空調,要不然再加一床被子。”
時綰哼哼唧唧的,把枕頭放在他旁邊,了鞋子就滾上去,占據他睡得暖和的地方,還大方的給傅琮凜留了床位,拍了拍,“快上來,我要睡了。”
一副大發慈悲又臨幸的口吻。
傅琮凜當真是被氣笑。
掀了被子躺上去,把人摟懷里,“可勁兒作,你也就在我跟前亮爪子。”
時綰在他懷里翻了個,手搭著他的腰,“誰說的?”
傅琮凜被這麼折騰一通,睡意倒是散了些。
“現在是不是可以了?”
時綰閉著眼沒反應過來,隨口一答:“什麼可以了。”
傅琮凜的手探過去了的,又了兩下。
暗示的意味明顯。
時綰一下就愣了,回過神來,沒好氣的擰了下他的手臂,“我還懷著孕呢!”
傅琮凜抱著,手一下又一下的著的背脊,閉上眼淡聲:“我知道。”
“那你還問。”
“醫生說的過了三個月差不多行了。”
時綰臉熱嗆聲:“胡說八道,哪個醫生說的?”
“之前。”
他這麼一說,時綰就明白過來了,之前做孕檢的時候,傅琮凜陪著去的,離開的時候他又折消失了片刻,時綰當時不知道他干什麼去了,問起,男人只平聲說問了些相關事宜。
誰知道竟然是問這個的。
時綰當即就要從他懷里爬起來。
傅琮凜按著,沒讓,“還鬧,不想睡了?”
“我回臥室睡。”
傅琮凜:“不是沒我不習慣,睡不著嗎,跑來跑去,你不嫌累。”
時綰哼了聲,“總好過在大尾狼邊睡。”
傅琮凜揚淺笑,睜開眼看著,男人的眼底漫著明顯的笑意,他拍了拍的屁,“給我老實點兒。”
時綰跟他較著勁兒,手指無意的劃過他的膛,猛地一。
傅琮凜的睡紐扣沒系得完全,上面三顆都是松開的,一來二去的,蹭得他的睡有些,領口更是大敞,時綰咬了咬,目落在眼前健康小麥的結實膛上,起伏的理很是,時綰連忙移開目,整個人像是被電了似的。
見作停下,傅琮凜垂眸,要笑不笑的看著,“怎麼停下了?”
時綰面紅耳赤,沒說話。
傅琮凜往上稍微一,“繼續蹭啊,不是能鬧騰。”
時綰推開他的膛,指尖及他的皮,滾燙又實,倏地閉上眼,自我催眠道:“我睡著了,你別打擾我。”
傅琮凜抓著的手了,嗓音喑啞:“一天不收拾,就皮的。”
他低頭攫住的舌,輕的一個吻,漸漸加深,的纏綿。
傅琮凜稔的挑起的緒,手指搭在的腰椎部分,慢慢的游移,時綰呼吸有些重,被迫仰起頭跟隨他的吻,四下寂靜,僅僅只余兩人親的融,曖昧的氛圍愈加濃烈。
猜你喜歡
-
完結1795 章
婚內燃情:三叔,別這樣!
“我會負責。”新婚夜老公的叔叔在她耳畔邪惡道。人前他是讓人不寒而栗的鐵血商業惡魔,人後卻是寵妻狂。他對她予所予求,為她鋪路碎渣,讓她任意妄為,一言不合就要將她寵上天。隻因多看了那件衣服一眼,他就直接壟斷了整個商場在她的名下。他說:“隻要你要,傾我所有!”
166.3萬字8.08 304871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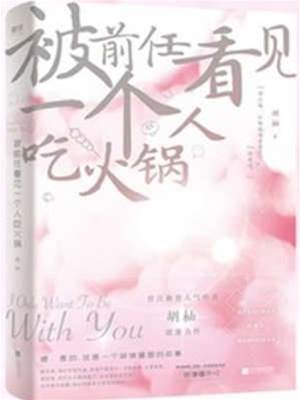
被前任看見一個人吃火鍋
【葉陽版】 葉陽想象過與前任偶遇的戲碼。 在咖啡館,在電影院,在書店。 在一切文藝的像電影情節的地方。 她優雅大方地恭維他又帥了, 然后在擦肩時慶幸, 這人怎麼如此油膩,幸好當年分了。 可生活總是不盡如人意。 他們真正遇到,是在嘈雜的火鍋店。 她油頭素面,獨自一人在吃火鍋。 而EX衣冠楚楚,紳士又得體,還帶著纖細裊娜的現任。 她想,慶幸的應該是前任。 【張虔版】 張虔當年屬于被分手,他記得前一天是他生日。 他開車送女友回學校,給她解安全帶時,女友過來親他,還在他耳邊說:“寶貝兒,生日快樂。” 那是她第一次那麼叫他。 在此之前,她只肯叫他張虔。 可第二天,她就跟他分手了。 莫名其妙到讓人生氣。 他是討厭誤會和狗血的。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讓她說清楚。 可她只說好沒意思。 他尊嚴掃地,甩門而去。 #那時候,他們年輕氣盛。把尊嚴看得比一切重要,比愛重要。那時候,他們以為散就散了,總有新的愛到來。# #閱讀指南:①生活流,慢熱,劇情淡。②微博:@胡柚HuYou ③更新時間:早八點
19.1萬字8 7230 -
連載601 章

這主播真狗,掙夠200就下播
189.5萬字8.18 8244 -
完結146 章

那月光和你
大學畢業,顧揚進了一家購物中心當實習生。 三年后,他作為公司管理層,和總裁陸江寒一起出席新店發布會。 一切看起來都是順風順水,風波卻悄然而至。 高層公寓里,陸江寒一點點裁開被膠帶纏住的硬皮筆記本,輕輕放回顧揚手里。 那是被封存的夢想,也是綺麗華美的未來。 再后來。 “陸總,您能客觀評價一下顧先生嗎?” “對不起,他是我愛人,我客觀不了。”
41.4萬字8 6805 -
完結122 章

月光渡我
時衾二十歲那年跟了傅晏辭。 離開那天。 傅晏辭懶散靠門,涼涼輕笑:“我的衿衿急着要長大。” 時衾斂下眸子:“她不可能永遠是你的小女孩。” 夜深。 時衾咬着牙不肯。 傅晏辭發了狠,磨得人難捱,終於得償所願換到一句破碎的細語—— “衿衿永遠是你的小女孩。”
18萬字8 122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