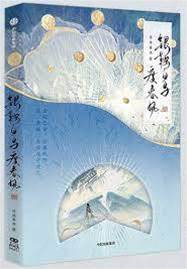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洛九針》 二十二 話不聽
應該是個匠工。
知客翻看著冊子。
托西堂的作,曾經斷絕的消息渠道又活了過來。
西堂向京城打探消息,京城這邊自然也打探各方消息。
“這位七星,接了幾個訴求,做的都是匠工制造和指點。”他說,“掌管西堂的長老是段秀,匠工出,他設下的堂口是匠工坊。”
“看來這位新人技藝很出眾啊。”高小六轉著手里的骰子,說,“技高人膽大,讓西堂這般不顧一切跳出來。”
他再次看著盅底。
“七星。”
這就是西堂新匠工的名號吧,大概是段秀的弟子。
“名字好聽的。”知客在旁說,也念了一遍,“七星,天上星嗎?”
高小六哼了聲:“一個木匠,這個名字做什麼,應該尺子墨斗呢。”
話剛說完,門被急促敲響。
“六爺。”一個仆從進來,神焦慮,“那個伶人跑了。”
跑了?
知客神驚訝。
這伶人還真有些本事啊,竟然能從他們手下逃走。
“行啊,一個個真有本事,真是膽子大的可以啊。”高小六說,一腳踹倒面前的桌椅,“可以將我們所有人都葬送了事!”
……
…….
張元呼啦啦沖進京兆府,不多時又招呼人,不過沒有像以前那樣,一呼百應。
【認識十年的老書友給我推薦的追書app,野果閱讀!真特麼好用,開車、睡前都靠這個朗讀聽書打發時間,這里可以下載 】
稀稀拉拉只站過來四五個人,其他的腳步遲疑。
“張頭兒,我吃壞了肚子。”一個差役抱著肚子愁眉苦臉說。
另一個差役垂頭說:“我娘不好,我今日要告假。”
張元掃過他們,冷笑一聲:“你們是吃壞了肚子還是不想跟我出去,我難道看不出來?”
Advertisement
既然他說明了,有個差役干脆抬起頭,說:“頭兒,我們不想被人說是都察司的走狗。”
張元的臉鐵青:“我說過了,這是我們京兆府的桉子。”
“劉秀才桉已經結束了。”另一個差役小聲說,“主犯是那個佃戶妻,已經死了。”
“胡說八道。”張元喝道,“佃戶妻只不過是買兇,兇還在逃,別人不知道,你們當差的也不知道嗎?”
差役們不說話,低著頭看向另一邊。
“都察司提供的消息怎麼了?那也是我張元的桉子。”張元喝道,“你們不想去就不用去了,以后也別在我張元手下做事。”
說罷大步向前走去。
有五個差役遲疑下跟上去,余下的七八人你看我我看你最終沒有邁步。
屋檐下幾個吏也看到了這一幕。
“喊住張元嗎?”一個吏皺眉說,“他跑了一趟都察司后,到抓穿草鞋的,鬧得犬不寧,如今人人都在說我們京兆府了都察司走狗。”
另一個員搖搖頭:“不用管他,府尹已經把他的調令送上去了,他很快就能滾蛋了。”
“這張元就是貪慕霍蓮權勢。”又一人哼了聲說,“以前沒機會,現在逮到機會了,當然鞍前馬后。”
霍蓮的權勢令人厭惡也令人艷羨,這些年多人希借他之勢,送他家中的財珍寶不計其數。
張元這個窮鬼只能送自己了。
“那算什麼權勢。”先一人說,“不過是把刀。”
先帝在位時,朝堂積弊雜多,而新帝本不是皇儲,可以說倉促上位,要想坐穩朝堂就需要一把刀。
刀,非人哉,用完了就扔掉。
自來酷吏都沒好下場。
那倒也是,幾個吏點點頭,所以還是安安穩穩的好,有自己的小權,又能長長久久。
Advertisement
……
……
“張參軍。”
要踏一家酒樓的張元聽到街上傳來一聲喊,他的腳步一頓。
四周原本看熱鬧的民眾已經紛紛向后退去,原本詢問議論的嘈雜也瞬時消失。
一隊黑人走過來。
為首的年輕人滿臉笑。
“張參軍查桉呢?”朱川熱地說,“需要幫忙嗎?”
張元眼角的余看到自己帶的幾個差役紛紛垂下頭,也向一旁避開幾步。
他看著朱川搖搖頭:“不需要。”
“不要客氣啊。”朱川笑瞇瞇說,停下里一副不肯走的姿態,“你們人這麼。”
他看向酒樓。
“這麼多人怎麼也都得帶走查一查吧。”
這話一出口,酒樓里的人發出驚呼喧囂,更有人一跪在地上哭起來。
“不需要。”張元忍著眉頭跳,看出這朱川是故意的。
朱川笑嘻嘻:“真的不用嗎?”
一副你不說用我就不走的樣子。
張元知道別看他笑嘻嘻,隨時能翻臉,比如那次在都察司,但張元現在寧愿他翻臉,張口要再次拒絕,但話沒開口,有幾個都察司兵衛跑過來。
“朱爺,都督跟人打起來了。”他們喊。
笑嘻嘻的朱川哈了聲:“誰他娘的不想活了!”
來人低聲跟朱川說了句什麼。
朱川的笑臉頓消,眼神兇惡,罵了一聲臟話:“帶路——”
一眾兵衛呼啦啦向前方跑去,眨眼就消失在大街上。
街上議論紛紛,雖然懼怕都察司,但聽到霍蓮跟人打起來了,實在是難得一見,不閑人忍不住跟過去。
張元看了朱川離開的方向一刻,收回視線看向酒樓,雖然朱川走了,但見張元看過來,酒樓里的人們依舊驚恐的向后退一步。
張元沒有解釋自己跟都察司不一樣來安眾人。
Advertisement
解釋有什麼用,沒用。
等他做好了自己該做的事,一切自有評斷。
張元沉聲對差役們吩咐:“讓他們認認畫像。”
差役們應聲是,取出畫像走進去。
張元沒有進去,而是向朱川離開的方向跟去,并沒有多遠,穿過一條街就看到了擁的人群。
人群雖然擁,但格外的安靜。
越過人群,張元一眼看到幾面藍底云紋旗幟,他不由愣了下,神有些復雜。
北海軍。
跟霍蓮打起來的,竟然是北海軍啊。
北海軍啊。
大家都不陌生,霍蓮更不陌生。
襁褓中的他漂流在北海軍轄的河流上,年的他跌跌撞撞奔跑在北海軍的營地里,年的他穿上北海軍的兵袍負箭持刀巡查邊境。
除了在邊境,北海軍大將軍梁寺來京城覲見皇帝,他舉著北海軍的旗幟,親自接過了皇帝的賞賜。
這不是他作為一個小兵衛這輩子唯一一次接皇帝賞賜,后來,他穿北海軍的兵袍,將義父梁寺的頭顱獻給皇帝,又一次接到了賞賜。
只是,那時候的他是梁八子。
現在,他是霍蓮。
“本都督說的話,你聽不懂,還是不聽?”霍蓮說,隨著說話,勐地抬腳。
馬背上的男人猝不及防,竟然被他踹下馬。
還好男人及時穩住了形,有些狼狽地抬起頭。
他的年紀比霍蓮大幾歲,臉上染著邊軍的風霜,讓他顯得些許糙。
“梁八子——”他的聲音也很糙,張口大罵,“你這個王八子——”
四周的民眾還來不及為這聲罵驚呼,那邊霍蓮形一扭,手里多了一把長長的闊刀,裹挾厲風,噼了下來。
那糙的男人瞬時被刀砸中肩頭,一聲悶哼,跪在地上。
瞬時從厚重的鎧甲下滲出來,蔓延在肩頭。
街上頓時哄然。
猜你喜歡
-
完結121 章

攻心毒女:翻身王妃
可憐的李大小姐覺得自己上輩子一定做錯了什麼,這輩子才會遇到這麼多衰事。好在美人總是有英雄相救,她還遇到了一個面如冠玉的男子相救,這麼看來也不是衰到了極點哦? 不過偽善繼母是什麼情況?白蓮花一樣處心積慮想害死她的妹妹又是什麼情況?想害她?李大小姐露出一絲人獸無害的笑容,誰害誰還不一定呢!
46.5萬字8.18 19134 -
完結337 章

成為人生贏家的對照組[快穿]
她不是人生贏家,卻比人生贏家過的還好,你敢信?人生贏家歷經磨難,一生奮斗不息,終于成了別人羨慕的樣子。可她,吃吃喝喝,瀟灑又愜意,卻讓人生贏家羨慕嫉妒恨。在紅樓世界,她從備受忽視的庶女,成為眾人艷羨的貴夫人,作為人生贏家的嫡姐,也嫉妒她的人…
212.4萬字8 11147 -
完結686 章

神機毒妃只想寵反派
穿成狗血文女主,黎清玥開局就把三觀炸裂的狗男主丟進了池塘。為了遠離狗男主,轉頭她就跟大反派湊CP去了。原書中說大反派白髮血瞳,面貌醜陋,還不能人道,用來當擋箭牌就很完美。然而大反派畫風似乎不太對…… 她逼他吃噬心蠱,某人卻撒起嬌: “玥兒餵……” 她缺錢,某人指著一倉庫的財寶: “都是你的。” 她怕拿人手短,大反派笑得妖孽: “保護好本王,不僅這些,連本王的身子都歸你,如何?” 【1V1雙強,將互寵進行到底】
130.7萬字8.18 178083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662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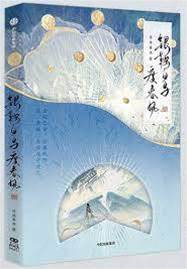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