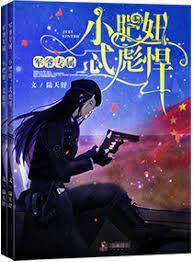《東宮美人(荔簫)》 第 12 章 第 12 章
太子審視著楚怡,審視得骨悚然。
腦子里打結打得跟古代結繩記事的繩似的,卡殼卡到連該說“討厭”還是“不討厭”都想不明白。
然后也不知是怎麼想的,楚怡呆滯地開了口:“奴婢說討不討厭……有用嗎?”
“?”沈晰鎖著眉頭沉思了一下,坦誠道,“沒用。你已經是孤的妾侍了,這不是你說了算的。”
楚怡:“……”
那你問個屁!
為此悲從中來,沈晰倒似乎因此豁然開朗了,變得心大好。
他舒著氣站起,又手把也攙了起來。
楚怡心跳得跟有二百個小姐姐在腔里踩著鼓跳《相和歌》似的,沈晰一臉好笑地了一下的額頭:“孤不是強人所難的人,你現在不愿,孤容你慢慢準備。”
……那奴婢要是一輩子都不愿呢?
楚怡慫的沒敢把這句話問出來,抬眸瞅瞅他,局促不安得只想開溜。
沈晰也沒打算讓這麼心神不寧地繼續當值,便讓回去歇著。至于外頭的那個周明,他也沒再追究,讓人回北邊去了。m.166xs.cc
楚怡回到房里,心跳也并沒有順利地緩和下來。把自己悶進被子里,腦子里糟糟的。
猝不及防地被太子“表了白”,突然麼?突然。
但奇怪麼?說實在的,不奇怪。
單憑現在這張臉,被男人喜歡就不值得奇怪。
何況這還是古代,他是太子?
對他來說,這有什麼不可說的?他跟本沒有遮遮掩掩的理由。
——不管是歷史上還是宮斗劇里,皇帝皇子們看上個宮,二話不說就給睡了的例子還嗎?這是階級制度給他們的特權和三觀,是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去看的。
Advertisement
站在這一套三觀基礎上,他都沒直接睡了,而是愿意給時間,已經堪稱道德楷模了。
畢竟,他若是今晚就打算直接睡也沒轍。這個時代的人管那“臨幸”,是一種恩賜,到這種恩賜的人應該激涕零。
眼下他顧及的心思可以說是很難得的,或許也是真對用了些心。
這些道理楚怡想得明白。但想得明白管屁用,明白道理和自己心甘愿撲上去睡太子是倆概念。
其實,倒不介意給太子當妾,也不介意他會有越來越多的三宮六院——這個人的適應能力很強,既然清楚拿現代三觀要求古代人不現實也不科學,那就懶得矯那麼多,所謂忽略背景談三觀都是耍流氓。
但問題是,真的認為自己搞不定宅斗宮斗那套東西。
——萬一一不小心就特別得寵了怎麼辦?到時候能容得下他去睡別人,別人不一定容得下啊!
這一不小心可是要送命的!又沒有宮斗片主那種上個煙熏妝就要黑化放大招的本事,對這條小命,可寶貝了!
這就很難辦,從了吧,擔心的這些事兒十有八|九避不過;不從吧……怎麼才能不從啊?
楚怡煩躁地在床上翻來滾去了一下午,到了傍晚時聽聞太子照例去宜春殿用膳了,的心才平復了一些。
好好好,祝他們夫妻舉案齊眉,百年好合。不然太子去看看別的誰也都好,可別再提喜歡的事兒了。
宜春殿里,夫妻兩個各自低頭用著膳,沒什麼話可說。
云氏和廖氏冊封后搬出了宜春殿,太子妃到底識了趣,沒再給太子塞人。太子也是怕了了,不再在宜春殿留宿,只每晚過來用個膳,用完就走,自己回書房睡覺。
Advertisement
這樣的相好像很平靜,但也正因為這樣,夫妻兩個之間的好像愈發淡薄了。太子每天來看太子妃都像是在完任務一樣,只是為了讓安心,除此之外別無他想。
太子妃趙氏呢,又素來不是個會主與人親近的子,太子不說話,便也不說。
可事實上,趙瑾月的心里是很慌的。
太子把云氏和廖氏冊封了送出宜春殿,就再也沒臨幸過,徐側妃那邊他也沒去,是讓放了些心,甚至于有些。
但同時又在想,這樣不是個事呀!
——有著孕,堂堂太子就誰也不見了,這若傳出去,讓旁人怎麼說?
還有四個月才生,不能讓太子一直這樣。是太子妃,賢惠是最要的,專寵那是妖妃才會做的勾當。
趙瑾月就這樣惴惴不安地琢磨了一頓飯,太子放下筷子的時候,其實才吃了沒幾口。但按著宮里的規矩,桌上地位最尊的擱了筷子,旁人便也不能吃了,趙瑾月就也把筷子擱在了一邊。
沈晰由宮人服侍著漱了口,抬眼便見碗里的飯沒兩口,夾菜的碟子也幾乎是完全干凈的,不蹙了蹙眉:“吃得這麼,子不適?”
太子妃搖搖頭:“沒有,臣妾適才想事走了神,沒顧上吃。”
時常這樣,沈晰也習慣了心思重,便又說:“那孤先回去了,你再吃些,讓小廚房給你做些合口的也好,別拘禮了。”
他說罷起便走,原該起恭送他的太子妃卻住了他:“殿下。”
沈晰轉回頭,趙瑾月笑了笑,走到他面前抬手給他理起了領。
這種親昵的舉在夫妻間十分正常,但大概是因為太子妃從不這樣做,沈晰一時竟覺得不太自在。
Advertisement
于是,他攥住了太子妃的手:“有事?”
趙瑾月低垂著眼簾,溫聲道:“殿下有日子沒去看徐妹妹了。”
又來?
沈晰郁結于心,口吻不自覺的生:“這是我的事,你不要這個閑心。”
趙瑾月卻置若罔聞,溫溫和和地又道:“殿下上承著家國重擔,多子多福是要的。徐妹妹是側妃,份貴重,該為殿下開枝散葉。”
“……”沈晰越聽眉頭皺得越,費解得不得了。
他真的不知道是怎麼想的。
有孕之初,為了不讓他去見側妃,拼命地拿妾侍拴他的是,現在主勸著他去側妃那里的也是。
塞妾侍的時候,說多幾個人服侍他是應該的,如今又說徐側妃份貴重,該為他開枝散葉。
好聽的全讓說了。可他聽著,就是覺得哪句也不是真心話。這些話的背后,一定還有別的思量。
楚怡就不這樣。里沒幾句好聽的(……),但句句都實實在在。
沈晰不自覺地嗤笑了聲,眼見太子妃被笑得一懵才回過神,又忙正了:“改日再說吧。明天是逢五的日子,得去向母妃問安,你早點休息。”
說完他就離了宜春殿,自是沒去徐側妃那邊。趙瑾月兀自在寢殿里靜了會兒神,卻是越靜心里越不安生,總覺得他那笑里有什麼別的意味。
第二天一早,沈晰將放楚走的事詳細地寫了個折子,差人送去了乾清宮。然后便給沈映派了差事,讓他領了個東宮侍衛的銜。
前侍衛和東宮侍衛聽著不高,但其實都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有許多都是宗親子弟在混資歷。沈映這種旁支到讓太子想不起來的宗親,按道理還不著這麼好的差,但沈晰一時也想不出別的差事給他,便跟他說:“這差事你先干著,若干得不好,孤隨時打發你走,錢你還得照還。”
Advertisement
沈映滿臉喜,抱拳干脆地應下,便告了退。
他昨日暫住在了東宮,眼下要收拾收拾東西回家去,等到當值的日子再進來。
經過離書房不遠的一方院子的時候,沈映聽到里頭呼哧呼哧的,便下意識地停了腳,結果一眼就看見楚怡正跑圈。
這一個多月來,楚怡為了提高素質一直堅持每天早上跑圈,跑完全還會回屋做兩組俯臥撐。
這種運強度不大,也不耽誤事,但堅持下來效果還好——現在上有勁兒了,腹部有點了,在太子邊一站一下午也不太覺得累了。
但昨天夜里被太子的話攪得一夜都沒睡好,今天早上狀態特別差,沒跑兩圈就了起來,簡直在真實呈現什麼疲憊如狗。
門外乍然傳進來一聲“楚姑娘”,楚怡停住腳好生恍惚了一下,才向院門的方向去。
不遠的重影很快合了一個清晰的人,楚怡微怔,而后抹著汗笑迎上前:“沈公子!”
沈映不解地打量著:“姑娘這是……”
“沒事,活活筋骨。”楚怡說著,作勢掰了下手腕,又反問他,“公子去見殿下?”
“剛見過,我回家一趟。”他說著笑了笑,略作思忖,把聲音低了幾分,“姑娘有沒有什麼話要帶給楚公子?”
……哎?
楚怡忽而覺得哪里不對頭,脧了他兩眼,小心探問:“公子跟我兄長很麼?”
昨天沈映“賣”救了楚,楚卻高冷地連見都懶得見他,還以為他們的關系也不過爾爾,只是沈映想要報恩而已。
現在,沈映卻表示能幫帶話?那昨天的拒不見面就覺很奇怪了啊!楚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沈映倒是也沒想瞞,直截了當地告訴說:“楚公子目下沒地方住,暫時借住在我家。”
楚怡:“?”
他們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
猜你喜歡
-
完結1576 章
快穿團寵:她又美又颯
曲嫣是快穿執行者裡出了名的又美又撩,嬌縱恣意。但凡她出任務,就冇失敗過。再高傲不羈的男人,後來都會變成——冷酷的霸總:“乖乖寶貝,我錯了。”風流的公子哥:“嫣嫣,我保證再也不看彆的女人一眼。”狠戾的反派大佬:“誰敢欺負你,老子弄死他!”坐擁後宮的皇帝:“江山為聘,朕願為你廢除六宮。”嗜血魔尊:“做我的妻,六界任你馳騁。”【蘇爽,甜寵。女主又美又颯,虐渣不手軟】【男主靈魂是同一個人,1V1】
155.1萬字8 48071 -
完結486 章

三年後,她帶戰神夫君炸翻全京城
空間➕爽文➕雙潔➕多馬甲 “什麼?天盛國又又又出了新武器,投石機?機械馬?快投降!這誰打的過?” “什麼?天醫穀又又又出了新藥?趕緊搶,可不能錯過!!!” “什麼?玄靈宗現世了?趕緊讓各皇子們去學習!” “什麼?蓮福鳳女降世了?得此女既得天下?等等……怎麼被人捷足先登了???” 這不是雲家的那個醜丫頭麼? 某穆爺:“這顆珍珠,我先得了。” 眾人咬牙切齒,悔恨交加。 然而,正當天下要因此大亂時,雲妙站出來一句:“誰敢亂?” 各方勢力齊呼大佬,統一跪拜! 頓時,天下震驚,續太平盛世,四國再不敢動。 命天士歎服:此女能揭天下風雲,亦能平天下戰火,奇女子也!
90.2萬字8 31588 -
完結3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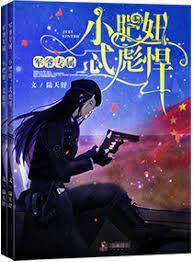
軍爺專屬:小肥妞,忒彪悍!
身為雇傭兵之王的蘇野重生了,變成一坨苦逼的大胖子!重生的第一天,被逼和某軍官大叔親熱……呃,親近!重生的第二天,被逼當眾出丑扒大叔軍褲衩,示‘愛’!重生的第三天,被逼用肥肉嘴堵軍大叔的嘴……嗶——摔!蘇野不干了!肥肉瘋長!做慣了自由自在的傭兵王,突然有一天讓她做個端端正正的軍人,蘇野想再死一死!因為一場死亡交易,蘇野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色誘……不,親近神秘部隊的軍官大叔。他是豪門世家的頂尖人物,權勢貴重,性情陰戾……一般人不敢和他靠近。那個叫蘇野的小肥妞不僅靠近了,還摸了,親了,脫了,壓了……呃...
96.9萬字8 14612 -
完結1258 章

皇家金牌縣令
【種田+輕松娛樂+穿越】 方正一穿越至大景朝成為一名小縣令。 花費七年時間打造了屬于自己的世外桃源,本想做個土皇帝逍遙一生。 景和十三年,大景皇帝微服私訪,偶然間誤入桃源縣.... 皇帝初入縣內滿心震驚! 各種新奇之物,讓人目不暇接。 “抽水馬桶為何物?竟然如此方便!嘶...你們竟然用紙....??” “這鏡子也如天上之物?” “還有這.......” ........ 不久之后,皇帝攜太子再臨桃源縣。 且看小縣令如何玩轉朝堂,迎娶公主,登頂權利之巔! 架空史觀,借鑒了各朝代,希望大家看的開心
232.8萬字8.18 290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