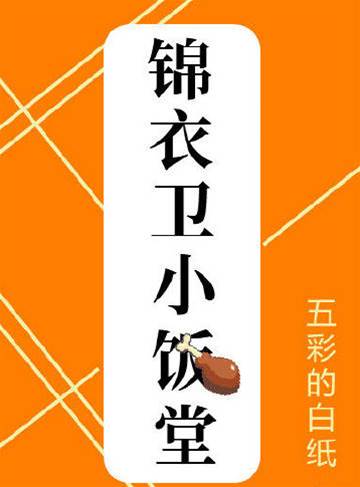《娘娘快跑您的昏君也重生了》 999:(番外)贏紂不滿
沈立刻覺到自己佔了下風,趕說:「可是這鐲子分明就是在你們房中出現的,不是你的,也是你娘,或者你邊的婢的!」
「那更不可能了、」時沉抬頭看著贏紂:「王爺瞧瞧民的一打扮,再瞧瞧民的娘。」
贏紂眉心微不可查的皺了皺,確然,這倆人一破舊裳,面黃瘦,很顯然在此了不委屈。
他眼中慢慢匯聚了一團黑霧,有些不悅。
「像是民這種打扮,連最低賤的奴才都比不上,怎可能進到前廳去會客。」
「了夜明珠,也就罷了,我們窮,可以拿去賣錢,可是我們非但沒有賣錢,反而打了一個金鐲子?」
時沉越說越覺得想笑,這對母二人的表演可真是百出:
「王爺若是不嫌棄,可以派人去我家屋子裏看,最值錢的,就是一把桃木梳,連吃的,也只有半個餅,拿來的錢去打金鐲子?」
Advertisement
贏紂越聽臉越黑:「瑯白。」
瑯白拱手,抬腳就去搜了。
須臾,一臉無語的出來:「啟稟王爺,裏面,確實是清貧……」
這都是含蓄說了,何止是清貧,那是非常清貧!連只耗子都沒有。
贏紂挑起眉梢,意味深長的朝著白尚書看去:「白尚書。」
白真渾一,戰戰兢兢的看著他。
瑾王聲音愈發沉冷:
「如此待家室,可真是大家風範啊。」
「王爺言重啊!」白真趕跪下:「下,下一直以來都忙於公事兒,這家中的大大小小的瑣事,全部給賤來管,對於這母二人過得好不好,是一點都不知啊!」
「自己的兒過得好不好都不知。」
贏紂微微勾起角,溫潤的臉上帶著鋒利的殺意:
「你還當個什麼?」
白真臉上盡褪,眼珠兒慌的轉:
「下只是一時糊塗,急火攻心,這才做錯了事兒!」
Advertisement
「急火攻心?做錯了事兒?」
贏紂呢喃著這句話,笑容愈發深:
「本王卻瞧著,這丫頭似乎是被你們當做死人了。可你的兒死而復生,你竟並不激,反而打法嫻,想來不是一時做錯了事兒,而是一錯再做,釀大錯!」
白家人齊齊一哆嗦,竟是一時無言以對。
白善善與沈暗中對視,心中百轉千回,研究對策。
白善善當即定下結論,跪著上前兩步:「王爺,不是這樣的!們在撒謊!」
時沉看過去,倒有些訝然。
都弄到這個份兒上了,竟然還能想出方法辯駁。
白善善死死的咬著下,掙扎一番,而後開口:
「們是故意裝可憐,引王爺同,們實際上本不是住在這個院子裏,們……另有廂房居住的!」
另有廂房?
這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本事,時沉真的很想問一問師傳何。
沈也忙不迭的點了點頭:
Advertisement
「是啊是啊王爺!民婦真不知道,們為什麼要說謊!這間屋子,最是清凈,最近白府剛辦了喜事兒,若是出了喪事也不好,所以就給安排在這間房子裏了。」
說著指著時沉的娘:
「這劉芳,還有這個丫頭,不過是怕自己的新衫弄髒,才尋了兩個下人的服穿罷了!沒想到今日竟然反咬我們一口!王爺,民婦冤枉啊!」。
猜你喜歡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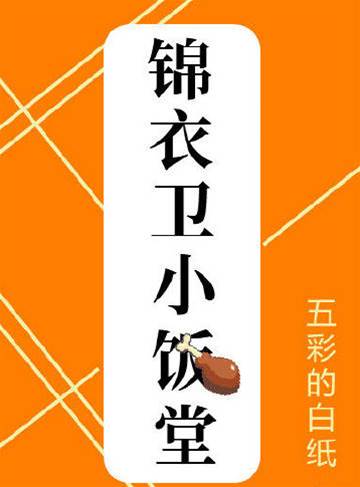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25 39928 -
完結529 章
冷王追愛:萌妃輕點寵
一朝穿越,慕容輕舞成了慕容大將軍府不受寵的癡傻丑顏二小姐,更是天子御筆親點的太子妃!略施小計退掉婚約,接著就被冷酷王爺給盯上了,還說什麼要她以身相許來報恩。咱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躲躲藏藏之間,竟將一顆心賠了進去,直到生命消亡之際,方才真切感悟。靈魂不滅,她重回及笄之年,驚艷歸來。陰謀、詭計一樣都不能少,素手芊芊撥亂風云,定要讓那些歹人親嘗惡果!世人說她惡毒,說她妖嬈,說她禍國?既然禍國,那不如禍它個地覆天翻!
89.6萬字8 47499 -
完結265 章

首輔嬌妻被風吹倒了
京中人人皆知喬御史家的嫡女身體羸弱、風一吹就倒,卻被皇上指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大人牧時景為妻,牧時景可是令京中無數閨閣少女夢破碎的‘鬼見愁’,更何況牧時景已經接連交了兩年罰銀,成了京中的剩男。 喬御史一家見皇上賜婚,對象還是當朝首輔,恨不得當天晚上就打包將女兒送進首輔府,再不進門,他女兒還得再交一年的罰銀‘一百一十一兩’..... 京中都在等著看二人的笑話,就連牧時景都等著喬家女咽氣,好恢復自由身,誰承想一扭頭就看見她身手利索地爬上了樹,一眼看不到就把他的對頭打了,這是弱柳扶風?
50.6萬字8.18 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