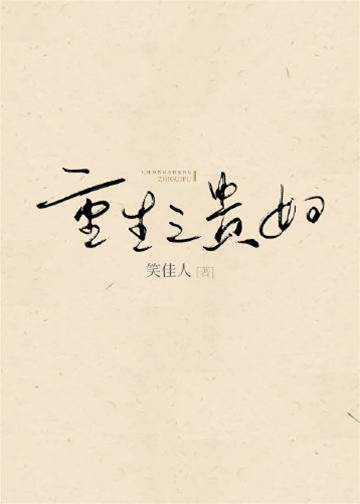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娘娘快跑您的昏君也重生了》 1127:番外:一命抵一命
白善善立刻附和:「是啊王爺,裝作一副手無縛之力的樣子,其實都是假的,都是偽裝的!」
高的男人倏然抬眸:
「閉。」
房間默了一默,施斐抿著委屈的吸了吸鼻子:「王爺……」
「東一句西一句,吵得本王頭疼。」贏紂神肅穆的著們,氣場愈發冷:「都下去,白暮瑤留下。」
施斐臉微變:「王——」
「下去!」贏紂低喝。
施斐委屈的抿了抿,心不甘不願的站起來,餘著一冷朝時沉看去,慢慢退下了。
廂房之中,獨剩時沉與贏紂二人。
保持著被捆綁的姿勢,躺在地上,下輕輕點著地。
二人彷彿陷了一片死寂當中,良久,贏紂站起,墨的角拂過椅面,慢慢來到了的面前,俯下,一把緻的匕首痛快的劃過了捆著的麻繩。
Advertisement
纖細的手腕上有兩道紅印,除了這些,還有大大小小的傷口。
他眸微黯,凝著傷口,不自的出手輕輕了。
沉並未有所察覺,坐了起來,贏紂趕收回了手,不自在的抿了下,隨後又面容無波的朝看去。
時沉還是那句老話:「小桃子在哪?」
「被我安置起來了,在冰窖里,防止腐爛。」贏紂站起:「你如何?」
時沉揚眉,這才有了覺。
方才不顧一切要掐死陳嬤嬤,被人打了好幾下,傷口都在悶悶作痛。
「我可真是一個廢。」自嘲的扯了扯角:「真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廢。」
「當年,我當太的時候風生水起,後來安樂國毀在了我的手裏,我邊的人,我都沒有保護好。」
慢慢的站起:「如今,連小桃子我都保護不了,那帝之位,說不定帝母傳給時沉姌,就是又一個結局。」
Advertisement
「安樂國早晚都會隕落,不管你的帝母將皇位傳給誰,都是一個結果。」
贏紂目沉沉:
「天註定的,你怎麼樣也改不了,但……」
頓了頓,他看向:「你死過一次,自己反省反省當初到底是錯在了哪,這一次就會有所不同。」
時沉聞言回首,扭頭朝他看去,眸中似是覆了一層冰霜,與他相許久,慢慢的轉移了目。
「如若我能夠在一開始就將小桃子護在邊,再往前追溯,如若是我能夠與時沉姌表面上的功夫做得好,即便是再討厭贏灝也要溫相待,說不定就不一樣了,一直以來自命清高,走到如今這一幕,都是我活該。」
「樹直易折。」長嘆了一口氣:「這些事兒,我早該看明白的。」
從前的時沉太孤傲,誰也看不上,從來就不像是時沉姌對誰都是笑盈盈的。
現在想想,擺在時沉姌手中,也是有可原。
緩緩的攥了拳,眼中閃過一篤定的。
-
「您說什麼?」
暮下,施斐不敢置信的看著瑯白:「王爺說要放過白暮瑤?」
瑯白頷首,燭搭在他半明半暗的臉上:
「王爺說了,一命抵一命,您節哀順便。」。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太子殿下你被逮捕了
世人皆讚,寧安侯府的四小姐溫婉寧人,聰慧雅正,知書達理,堪稱京城第一貴女,唯有太子殿下知曉她的真麵目,隻想說,那丫頭愛吃醋,愛吃醋,愛吃醋,然後,寵溺他。
134.7萬字8 8508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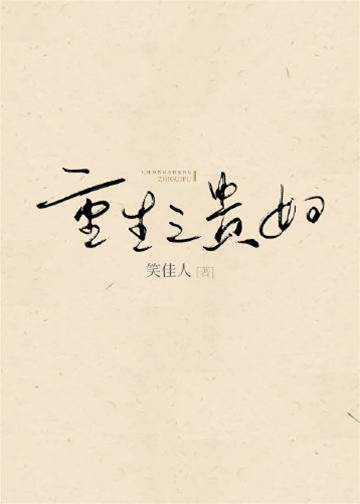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5840 -
完結322 章

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
蘇沉央一遭穿越成了別人的新娘,不知道對方長啥樣就算了,據說那死鬼將軍還是個克妻的!這種時候不跑還留著干嘛?被克死嗎?“啟稟將軍,夫人跑了!”“抓回來。”過了數月。“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抓回來。算了,還是我去吧!”…
86.3萬字8 86025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54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