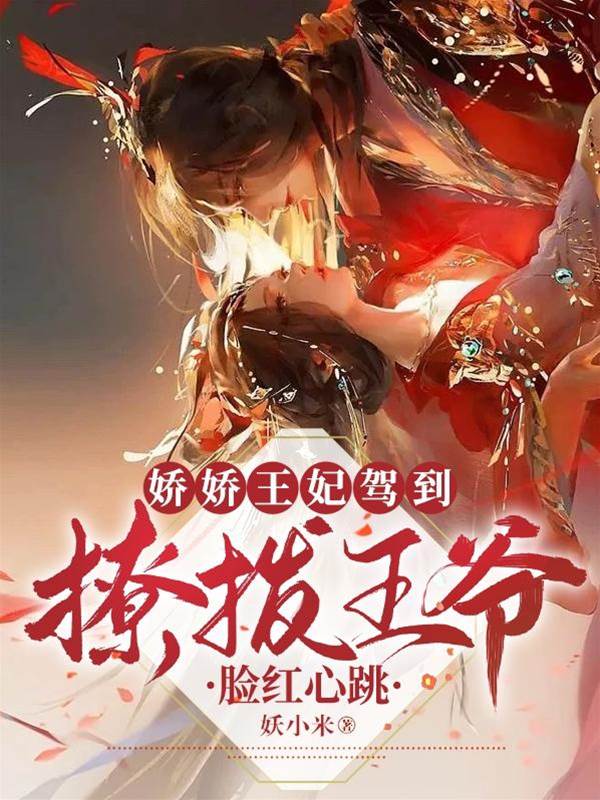《第一卿色》 第110章 酒與夢
兩人對酌許久,漸漸都醉了,歪歪斜斜靠在一起,醉醺醺說著胡話。
秦弗雙眼迷離:“許澄寧,你想要什麼?孤給你!”
許澄寧嚨里辣乎乎的,指著頭頂的月亮。
“我要那個,看著解。”
“孤給你弄下來。”
秦弗彎腰從窗外撿了枝子,在虛空中捅啊捅,里重復地問:“掉下來沒?吃到了沒?”
許澄寧躺在榻上,半瞇著眼,說“沒呢,沒呢”。
秦弗捅半天,又開的看了看,把枝子一甩,扔了,在邊躺下來,嘟囔道:“太難了,孤不弄了,換一個。你還要什麼?”
許澄寧在榻上扭來扭去,突然轉過來,臉上紅彤彤的:“我想要,跟金陵韓氏一樣的山水別院,有山,有水,有花,有草,食無憂……”
“孤給你!”秦弗揮了揮手,也轉過頭看,“還有呢?”
“我想……”許澄寧忽而一癟,帶了哭腔,“我想我爹活著!”
趴在榻上哭起來。
秦弗心里有點酸疼,大手輕輕的腦袋。
許澄寧哭了一會兒,半張臉埋在胳膊里,悶悶道:
“殿下,你知道嗎?我喜歡被人抱,我喜歡別人把我抱在懷里,舉得高高的。
“我上學堂的第一天,邢夫子把我從墩子上抱了下來,從那之后,我就一直跟著他,功課不懂了、沒水喝了、找不到恭房了,我都找他。
“我喜歡讀書是因為,那時候上學堂,每天,爹爹抱我去上學,下學后,邢夫子抱著我到路口等我爹,我爹又把我抱回家。
“一天里,我能被兩個人抱,那是我長這麼大,最開心的時。
“可現在,他們都抱不了我了。”
又埋頭哭起來。
秦弗踢掉酒杯,手把撈進懷里,一下一下地輕拍著。
Advertisement
“不哭,孤抱你。”
“孤抱了就不會松開了。”
許澄寧摟著他的腰,臉往他懷里鉆,像貓一樣拱了拱。
“你得像跟著你夫子一樣,以后一直跟著孤。”
許澄寧在他前的服上抹淚,低低嗯了一聲。
兩人在窗前相擁,夜風微涼,秦弗懷里卻很暖,兩種覺合在一起,很舒服。
許澄寧醉意上頭,變了困意,不多時昏昏睡了過去。
秦弗懷里抱著,單手拎著酒壇,仰頭灌酒,怕酒澆到上,就用手掌蓋住,自己擰過頭去喝。
兩壇下肚,他也倒了。
渾暖洋洋的,好像置一片溫的花海。
睜開眼睛時,看到一片刺目的白,恍惚春融融,白日當空,一只高大的白玉酒卮立在眼前,玉質通細膩,起來的,手極好。
他酒沒喝夠,懶洋洋的,想要再喝幾口。
剛上前,酒卮居然了,像個人一樣跑起來離他越來越遠。
他在后面追,不知跑了多久,他終于抓住了酒卮,一把抱住。
酒卮不了,他上下索,找不到流口在哪兒,轉來轉去地看,終于找到一個小小的紅的口。
他含住,吮吸幾下,又停下來,咂了咂。
梨花白,怎麼有甜味?
不確定,再嘗嘗。
許澄寧夢見了書院那只黃梨的黃貓兒,一見就要討吃的,討不到吃的,就兇地拱。
被拱得往后仰倒,黃梨放肆地跳到上來,好重。
大貓,怎麼還咬呢?
秦弗嘗著嘗著,也喝習慣了,這酒不烈,可以多喝。
他把頭埋進酒卮里,從小小的流口拱進去,深深地啜飲。
可玉卮子又了,秦弗把它箍得更。
月西斜,幾案已經從榻上打翻了下去,杯盤狼藉。
Advertisement
一長一短兩條影疊在一,頭對著頭,臉對著臉,輾轉黏纏。
旭日東升,暖白的日照進窗欞,鳥兒聲聲清啼。
秦弗皺了皺眉,抬手擋住了眼睛,緩了一會兒,才坐了起來。
環顧四周,發現自己已不在床榻上,頭頂的玉冠不知滾落到了哪里,此刻頭發披散,衽微開,出一片潔白的。
而臨窗的榻上,酒壇子七倒八歪。
許澄寧橫在上面,四肢散開,圓圓的頭頂朝向榻外,一片長發垂到地上,領口微微松散,約可見一痕致細巧的鎖骨。
飲酒誤事。
秦弗在額前一拍,覺腦子里的記憶被剪掉了一截,只記得許澄寧跟他說了很多話,哭了,后面他就開始哄孩子……再后來,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醒了。”
他輕拍了拍許澄寧的臉蛋,把起來。
許澄寧著惺忪的眼睛,看到眼前的一切,驚了一跳,連忙扯好自己的領,又覺眼睛干,還有些痛。
“殿下,昨晚我沒有對您無禮吧?”也忘記了。
秦弗抬頭想了想,道:“你拉著孤背書,吵得孤腦仁疼。”
他忽然看過來,皺眉問:“你怎麼了?”
許澄寧一愣,對鏡看了看,發現有紅腫,像吃了發似的,怪不得覺得痛呢。
“大約酒太烈了,不適合我喝。”
正是夏日,府上正好有冰,秦弗讓人包了塊冰來給許澄寧敷眼睛和。
“你昨日來尋孤,所為何事?”
因被親生父親毀掉多日籌謀的郁郁不平,經一晚上的休整,已經徹底消散,白天,他仍是殺伐決斷、智珠在握的上位者。
許澄寧拿出請柬,把陸欽鋒告訴的話說了。
“我人微言輕,不好摻和進去,不如殿下您做決斷。”
Advertisement
秦弗看了看大紅印金的請柬,文國公府四個大字威嚴大氣,世家的高不可攀在一橫一豎中姿態盡顯。
“你若想去,便帶你去可好?”
秦弗沒喝醉,說話居然也能這般溫。
許澄寧驚訝得一時沒有回答,等反應過來才搖搖頭:“我不想去。”
注意到秦弗憐惜的表時,許澄寧忽然明白了他在想什麼,解釋道:“殿下,卑怯是我小時候的事了,不去不是因為看輕自己,而是我明白什麼位置該做什麼樣的事,不是我的東西我不會宵想,何況我并無攀附之意。”
秦弗看坦然,心這才放下一半。
誰能想到這樣清靈俊秀、風采卓絕的年,曾經也有過輕生厭世的念頭呢?以后連話都不能對說太了。
“放著吧,孤會做安排。”
許澄寧自回了家,放浪形骸一個晚上,現在上都是酒臭味,所以立馬燒水,干干凈凈地洗了個澡。
穿著中出來,正要去找件干凈的服,卻看到妝奩的梳子下著一封信。
李茹剛好走進來,哎呀一聲。
“我忘說了,這信送了大半個月了,是給南哥哥的!”
“我的信?”
“朱老爺!”
猜你喜歡
-
完結497 章

首輔為后:陛下,臣有罪!
一朝穿越,命不由己。顧文君卻是個假男人,女兒身。今日顧家欺她無權無勢人微言輕,他朝金榜題名權傾朝野時,何人敢不敬她怕她!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為首輔。某暴君道“只要你恢復女兒身嫁為皇后,朕也可以在愛卿之下。”顧文君怕了。“陛下,臣有罪!”
134.4萬字8 26232 -
完結820 章

貪財王妃太囂張
一朝穿越就惹來殺頭大禍?王爺夫君不僅嫌棄還要和離?嗬,笑話!生死怎麼可能掌握在他人手中!看她右手揮銀針,活死人肉白骨,讓那惡毒繼母慘叫連連。瞧她左手抱肥貓,開啟無敵係統,讓那白蓮情敵跪地求饒。蘇卿瑜冷傲的看著某王爺:“你不是要和離?請簽字!”某王不要臉死不認帳:“和離?笑話,本王愛你還來不及呢!”係統肥貓表示:……嗬,小爺我隻吃草藥,不吃狗糧。
131萬字8 42335 -
連載1872 章

團寵農家小糖寶
老蘇家終于生閨女了。 于是,窮的叮當響的日子,火了! “爹,我在山上挖了一籃子大白蘿卜。” 奶聲奶氣的小姑娘,把手里的小籃子遞到了蘇老頭面前。 蘇老頭:“……” 腦袋“嗡”的一聲。 這麼多野山參,得賣多少銀子? “爹,我還采了一籃子蘑菇。” 蘇老頭:“……” 身子晃了晃。 這麼多靈芝,能置多少大宅子? “爹,我……” “閨女呀,你讓爹緩緩……”
332.7萬字8.18 173217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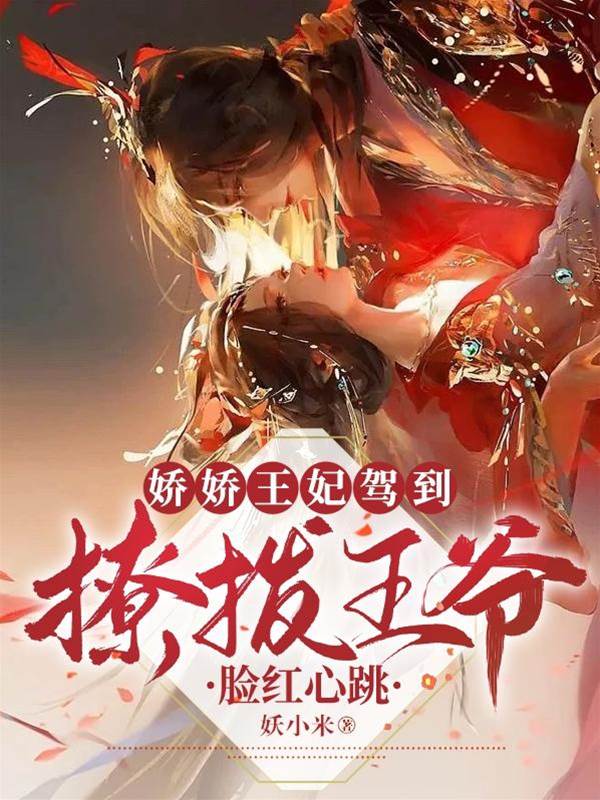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266 章

重生后嫁給廢太子
重生後,餘清窈選擇嫁給被圈禁的廢太子。 無人看好這樁婚事,就連她那曾經的心上人也來奚落她,篤定她一定會受不了禁苑的清苦,也不會被廢太子所喜愛。 她毫不在意,更不會改變主意。 上一世她爲心上人費盡心思拉攏家族、料理後院,到頭來卻換來背叛,降妻爲妾的恥辱還沒過去多久,她又因爲一場刺殺而慘死野地。 這輩子她不願意再勞心勞力,爲人做嫁衣。 廢太子雖復起無望,但是對她有求必應。餘清窈也十分知足。 起初,李策本想餘清窈過不了幾日就會嚷着要離開。大婚那日,他答應過她有求必應,就是包含了此事。 誰知她只要一碟白玉酥。 看着她明眸如水,巧笑嫣然的樣子,李策默默壓下了心底那些話,只輕輕道:“好。” 後來他成功復起,回到了東宮。 友人好奇:你從前消極度日,誰勸你也不肯爭取,如今又是爲何突然就轉了性子? 李策凝視園子裏身穿鬱金裙的少女,脣邊是無奈又寵溺的淺笑:“在禁苑,有些東西不容易弄到。” 知道李策寵妻,友人正會心一笑,卻又聽他語氣一變,森寒低語: “更何況……還有個人,孤不想看見他再出現了。” 友人心中一驚,他還是頭一回看見一向溫和的李策眼裏流露出冷意。 可見那人多次去禁苑‘打擾’太子妃一事,終歸觸到了太子的逆鱗!
41.8萬字8.18 436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