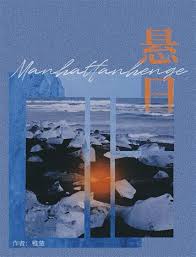《臣好柔弱啊》 第186頁
蘭達勒哪能不知道他的小九九。
但又覺得有理,“這天譴不會落在本王子頭上吧?”
“哪能!咱們現在不是得利了嗎?”
兩人在那頭嘀嘀咕咕。
寧如深沒忍住,“大王子,我可以走了吧。”
蘭達勒立馬收聲,“你那裳……”
寧如深心底了下,“怎麼了?”
他裳撕了一塊下來,沒來得及理,要是被人發現就解釋不清楚了。
蘭達勒說,“士兵找布料綁木生火,不知道那是你的裳,就拿去燒了。”
“……”
找布能找到舞姬帳角落裡去。
寧如深掃了眼旁邊心虛的副將,哪還不明白是誰在搞鬼。
他瞇了瞇眼:這狗日的。
但幸好,差錯地幫他毀滅跡了。
“再給我重新找一吧。”
蘭達勒說,“你這量…暫時找不到合的,本王子讓舞姬給你改一,你先將就將就。”
寧如深倒不是很介意穿什麼,只是不知道這兩人在打什麼鬼主意。他沒說話,朝蘭達勒看了幾秒。
蘭達勒被看得有些不安,彌補道:
“這樣吧,你還有什麼別的需要?熏,還是酒……”
寧如深心頭一,搖頭,“不用。”
他故作隨意,“我想去舞姬帳住,裡面有大承人。我一個人待著悶得慌,想找人聊天解悶。”
Advertisement
蘭達勒想了想,“好。”
雙方各自達到了目的。
寧如深很快收拾毯子,心滿意足地搬去了舞姬帳裡。
…
另一頭,大承軍營。
剛打完一場漂亮的勝仗,不費一兵一卒就折損了賀庫王上千兵馬,三軍皆神振,氣勢空前——
然而中軍帳裡,被他們奉若戰神的帝王卻不見喜。
李無廷撐額坐在案前,指節收。
燭火靜燃,在他眉間的壑和低垂的眼睫下落了幾分影。向來沉靜的面間,罕見地泄出真實的焦灼。
眼前不斷地晃過那道影。
他指尖微,全靠驚人的定力支撐著紛的心緒。
靜默的夜中,一道鷹唳驟然劃破上空!
李無廷心底一震,抬眼看去。
帳簾很快被掀開,霍勉一手挽鷹大步走進來,手中了張還沒來得及展開的布絹:
“陛下!有急報。”
李無廷一抿,接過來。
他視線在布絹上落了瞬,隨即深吸一口氣,強行定下神將布絹展開。
雪白的料晃得人眼睛一花。
接著,就看悉的字跡嘩嘩寫道:
『人在狄營,已神,勿擔心。』
“………”
李無廷,“?”
他指節了,又往下看去。
Advertisement
下方是一張輿圖,幾筆勾勒,標出了蘭達勒駐營的地點,還有營帳分布。
帳中安靜了半晌。
帝王連日繃的神驀然一松,著眉心,忽而低笑了一聲:
“寧卿……”
霍勉看得莫名,“怎麼了,陛下?”
李無廷一布絹,斂了神鎮定抬頭,“召集眾將,拔營!”
·
蘭達勒營中,舞姬帳。
寧如深搬來後,安安穩穩地窩了兩天。
這兩天,蘭達勒顧不上找他,他以“運發於南”的理由將人兵馬支去了邊關——
只要再多暴幾次行蹤,哪怕自己給的輿圖不那麼準,大軍也一定能找到大營的位置。
這會兒他正窩在帳中一角。
旁邊是替他“改裳”的大承姑娘,名菀桑。看著十五六歲,大概是剛被擄來沒多久,還沒有那麼頹喪。
“我是個牧羊,是和羊一起被搶來的。你呢?”
寧如深說,“我是個點糧,是和糧車一起被來的。”
“……”菀桑茫然:?
他看人似乎沒能理解,心歎:
不理解就對了,他自己都不太理解。
寧如深換了個話題,“對了,這營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特別的事?”菀桑思索,“說起來,北狄軍中不酒。每次劫掠回來,那些北狄將兵都會喝酒殺羊……這算不算?”
Advertisement
寧如深心頭跳了下:不酒?
劫掠回來,那不就是這兩晚。
…
當晚,北狄兵搶了牛羊回來,果然大擺宴席。
外面火通明,嘩聲喧天。
舞姬帳位於大營一角,帳中線偏暗,倒是相對安靜。
寧如深看向帳外晃喧鬧的人影:
白隼飛離幾天了?
算著時間,若從長綏整頓調兵過來,也差不多該到了。
如果能趕上今晚……
他正想著,帳外突然傳來陣靜。
一道嚷嚷聲傳來,接著簾子一掀,一名北狄將領喝得滿臉通紅地走進來,隨手抓了名舞姬,“出來!”
舞姬驚了聲,掙得一退。
那將領罵罵咧咧了兩句,繼續抓人。
Top
猜你喜歡
-
完結247 章

[ABO]離婚后他拒絕當渣攻
強大狠厲Alpha攻&斯文謙和Omega受(強強聯合)破鏡重圓小甜品,吃糖了! ****** 一:秦聞跟遲寒的三年婚約到期,他看著對方毫不猶豫遞出離婚協議。 整整三年,竟是一點兒眷戀都沒有。 遲寒冷漠地看著秦聞:“緣分到此,日後珍重。” 秦聞說不出話,他想折盡尊嚴地問一句:“可不可以不離婚?” 但是遲寒轉身太快。 每當秦聞想起這段灰暗絕望的時光,就忍不住給身邊的人一腳,然後得得瑟瑟地問:“你當年不是很狂嗎?” 遲寒將人抱住,溫聲:“輕點兒。” 二:離婚後沒多久秦聞就發現自己懷孕了,就那一次失控。 秦聞輕嘆:“寶寶,以後就咱們父子兩個相依為命了。” 可遲寒卻不答應了。有人刁難秦聞,遲寒想盡辦法也要扯下對方一層皮;有人愛慕秦聞,遲寒差點兒將人扔進醫院。 同性戀合法,雷生子勿入,雙潔!
57.7萬字8.18 2316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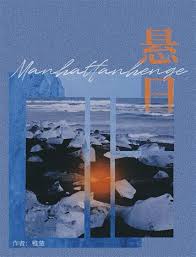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