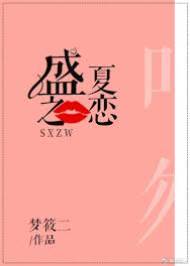《君心》 第 11 節 碎京華
是沈袖。
今日穿著一火紅的勁裝,提著長劍,這打扮看上去,倒是與謝重樓頗為相配。
只是謝重樓一見到,神便冷淡下來:「你怎麼能進我的演武場?關副將,帶出去!」
「謝小將軍有所不知,臣來這里,是皇上的旨意。」
「哦。」
謝重樓面無表道,「既然如此,京郊那麼多演武場,你隨意挑一個就是。我這里不歡迎你。」
他拒絕得直白又不留,沈袖一僵,臉上的笑幾乎要掛不住:
「謝小將軍莫非是覺得我一介流,不配待在你的演武場?連皇上都——」
謝重樓不耐煩地撇下,徑直走到我邊:
「任憑你說破天去,小爺的演武場就是不要人,你若不滿,大可以去皇上面前告我一狀!」
沈袖朝我這邊斜睨了一眼,忽然道:
「謝小將軍,你既說你的演武場不能進人,為何陸姑娘能進來?你這是雙重標準!」
謝重樓沉了臉:
「廢話。你既然這麼想進來,就別想著那幾招花拳繡能打我。來吧,若你能在我手下十招不敗,我就答應你。」
我雖未學過幾天武藝,卻也能看出沈袖無力,招式虛浮,宮宴上的劍舞,也不過幾招花架子。
前世亦是如此,可前世謝重樓卻視如珠似寶,甚至時不時用的武藝譏諷我:
「陸大小姐這種養在閨閣的金雀,又哪里知道巾幗子的颯爽迷人?」
他似乎全然忘記了,我的劍法和馬,還是從前他教給我的。
而如今,謝重樓毫不留的招式下,沈袖毫無回擊之力,兩招便被他反剪雙臂,死死按在了地上。
沈袖惱怒,回頭道:「謝小將軍如此欺負我一介流,就沒有半點憐香惜玉之心嗎?」
Advertisement
謝重樓嗤笑一聲:
「你親口在皇上面前說,你不比那些花玉般的閨閣子,自己說過的話都不記得了?」
「你要上戰場,莫非指北羌人也對你憐香惜玉一番?」
沈袖咬著,楚楚可憐地仰起頭,低聲說了些什麼。
那一瞬間,我心中忽然涌上奇怪的不安,下意識往過走了幾步。
接著便聽到了謝重樓不掩驕傲的聲音:
「我謝重樓追回心上人,從來正大明,還需要你所謂的刺激?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沈小姐。」
9
從演武場回去,是謝重樓送我的。
離開前我掀開車簾看了一眼,沈袖正提劍站在門口,目奇異地向我過來。
我形容不出的眼神,只覺得輕蔑之中,又帶有一高高在上的憐憫。
正心下不安之時,謝重樓卻手過來握住我,挑眉:「昭昭,不必理會無關要的人。」
這一世不知為何,他好像對沈袖一點興趣都沒有,與前世在我面前極盡所能維護的行徑截然相反。
大概是前世的五年折磨太過刻骨,縱然現實并非那般,縱然謝重樓也說那只是夢,我卻仍覺不安。
也不知該如何面對謝重樓,只好默默從他邊挪開。
他眸一暗,有些然道:「陸昭懿,你真要為那樣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就徹底冷落我嗎?」
回府后,母親瞧出了我緒不佳,提出三日后去城外若華山上的金陵寺祈福進香。
結果不知誰走了風聲,到那日,我又在金陵寺門口遇上了謝重樓。
扭頭去,母親著我:
「昭昭,我先同太師夫人去廂房用些素齋,你們若是說完了話,只管過來找我。」
我與謝重樓之間的奇怪氛圍,想必都看在眼里,才想了這樣一個辦法。
Advertisement
謝重樓迎上來,規矩行禮:「請伯母放心,我定然會將昭昭照顧妥帖。」
等母親離開,他從懷中取出一支煙紫的翡翠發簪,遞到我手里:
「深秋已至,春海棠難尋,我便雕刻了一支送你。」
我低頭看了看:「這是你親手雕的?」
「對啊。」謝重樓說著,低咳一聲,「我知道你也學過一些金玉雕刻之,大可評價一番,實話實說就是。」
既然他這麼說了,我也只好再細細打量一番,然后誠實道:
「雕工淺,行刀過度,上好的春翡料子卻……」
「陸昭懿!」
話沒說完,謝重樓已經不滿地盯著我,著重強調了一遍,
「這是我跑遍京城尋來的料子,一整夜才雕刻完。」
「……但心意難得,細看便覺
春海棠栩栩如生,實乃世間凡品。」我只好轉了話鋒。
謝重樓顯然滿意了,手接過簪子就往我發髻上:「既然你這般喜歡,我現在便為你戴上。」
他溫熱的指尖拂過我鬢邊,又輕輕掠過耳尖。
那像是落在心上的羽,一陣麻,我忽然臉紅發燙。
說話間,我們已經并肩穿過金陵寺中庭那片梨花樹林,來到后殿。
眼前線驀然和,繚繞在鼻息間淡淡的檀香味,讓我不安的心忽然沉靜下來。
坐在玄塵大師對面,我恭敬施禮后,便聽到他的聲音:
「施主心有疑慮,卻又不知何解,故而終日憂心。」
他雙手合十,沖我微一低頭,「紅塵紛擾,人心卻可貴。施主大可遵從本心,此局便也可破。」
「可我從前遵從本心,卻將自己陷囹圄,上了絕路。」
「那施主可知,你既已到了絕路,又為何還能到這里來?」
Advertisement
玄塵大師緩緩睜眼,目慈和卻平靜,
「人心易變,人心卻也最不易變。此局不比從前,置之死地而后生,方得云開月明。」
我謝過玄塵大師出去,謝重樓在門外等我。
「那老和尚同你說了什麼?」
「他讓我遵從本心。」我見他神并不好看,不由多問了一句,「他又跟你說了什麼,你不開心嗎?」
謝重樓瞇了瞇眼睛,桀驁道:「他讓我不必執念太深,有些事有緣無分。」
「……然后呢?」
「然后我將他臭罵了一頓,告訴他這種事由我心,既不由緣分,更不由命。」
果然是謝重樓這樣的格會做出來的事。
他從不信神佛。
我輕輕嘆了口氣:「或許他說得對,你是執念太深,退一步也沒什麼不好——唔!」
一聲驚呼,是謝重樓扣著我的手腕,將我按在了后涼亭的柱子上,目結一抹旖:
「退一步——陸昭懿,我從十二歲起就日日盼著娶你過門,現在你讓我退一步,讓我莫名其妙放棄?」
「我說了,那只是你的夢!我什麼都沒做過,你卻因為一個夢就給我判了死刑,可曾想過是否對我公平?」
說到最后,他眼尾微微發紅,嗓音里也裹挾了一輕微的抖。
心尖延綿不絕的痛泛上來,我張了張,發現自己幾乎發不出聲音。
我又何嘗不知,這樣的冷落對于什麼都不知道的謝重樓來說,并不公平。
可那并不是夢,那是我親經歷過的五年。
一千多個日夜,如同鈍刀一點點裁下我心頭十六載的熱切。
那種模糊的痛,至今想起來,依舊心有余悸。
我深吸一口氣,抬眼著謝重樓,緩緩道:「如果,那不是夢呢?」
10
他神驀然一凜。
我卻短短一瞬就卸了力,無奈地著額頭:「罷了,你只當我在胡說八道。」
氣氛安靜片刻,一時間,掠過我們耳畔的只有風聲。
「你夢中除了我們與沈袖,旁人呢?」
謝重樓忽然又問我,
「倘若我真要與你退婚,我爹娘第一個不同意。你夢里的他們呢?」
他們……
謝伯父謝伯母,在我嫁過去不到一年時,便雙雙病逝。
臨行前,謝伯母還握著我的手,低聲說:
「昭昭,你不要太難過了。不知為何,我一直覺得,自那日提出退婚后,重樓便也不再是我的孩子了。」
「如今我要去了,你便只當他跟我一同去了吧!」
我把前世的這些都告訴了謝重樓,他聽完,沉默片刻,篤定地告訴我:「我娘說得對。」
「昭昭,縱使傷了自己,我也不舍得傷你分毫,更不會做出那樣的事。」
「除非你夢里那個人,本就不是謝重樓。」
說完這句話,他低頭凝視我的眼睛,然后著我的下,吻了上來。
這個吻溫但熱烈,是前世婚五年,我也未從謝重樓那里得到的。
我揪住他襟,嗓音發:「……謝重樓,這是佛門凈地。」
「我不信神佛,更不信天命。」
他退開了一點,仍然在很近的地方盯著我,
「但我相信心意不可變,相信人定勝天,相信——只要你不放開我,那個夢,無論如何我都不會令它真。」
后來山間零零落落下起小雨,他將我一路送到廂房,與母親相會,又拒絕了母親的邀請,不撐傘便往山下走。
走了兩步,謝重樓忽然停住,轉頭向我:
「西南邊陲,圣上已下旨命我帶兵平——昭昭,我去給你掙誥命了,等我回來,我就去請旨重新賜婚,好不好?」
這道嗓音,奇異地與四年前年跪在雪地里的承諾相合。
我難以抑制心頭悸,倚著走廊用力點頭,也莊重應聲:「好!」
可隔著雨簾,一團模糊里,我卻始終無法看清謝重樓的眼睛。
他走后不足半月,西南便有捷報頻頻傳出。
父親上朝回來時總會帶些消息。
例如他不慎中了埋伏,千鈞一發之際被一小兵所救,已將對方提為副將。
寥寥幾語,聽上去已經足夠驚心魄。
我握著篆刻刀,細細雕刻著手里的長簪,想等謝重樓凱旋之日送給他。
日子流水般過去,我想或許前世種種不過大夢一場。
而我與謝重樓的婚事,也會如我從前無數次幻想的那樣,順順利利地進行下去。
就在這時,父親告訴我,他要班師回朝了。
那一日是初冬,京中飄著細碎的雪花。
我系著滾白的艷紅斗篷,發間著謝重樓送的春海棠發簪,站在城門外等他。
小織勸我在馬車等,我搖搖頭:「也不算太冷,就在外面等著吧。」
臨近午時,遠遠的有兵馬越走越近,我不知怎麼的,忽然想起——
前世,似乎就是這一日,謝重樓來太傅府提了退親。
下一瞬,兵馬最前方,一匹四蹄踏雪的烏黑駿馬馱著兩個人直奔過來。
馬蹄踏雪,濺起細碎的白。
我一瞬間如墜冰窟。
坐在前面一襲藍、腰佩長劍的,是神采飛揚的沈袖。
而后,用斗篷將攬在懷中,目冰冷又漠然地向我掃過來的年,正是謝重樓。
11
馬在我面前驀然停住,高高揚起前蹄。
我躲也不躲,只是定定瞧著謝重樓。
未從我臉上看到驚慌與悲,他似乎有些意外,沖我挑了挑眉:「陸大小姐,你在等誰?」
「自然是等你。」
不等謝重樓答話,他前的沈袖已經輕笑一聲,向后靠了靠,姿態親昵:
「陸姑娘既然與謝將軍退婚,你們之間便再無瓜葛。你自去尋你的良人,怎麼又來糾纏舊?」
眼里是藏都藏不住的自得。
我攏了攏披風,安靜道:「這是我和謝重樓的事,與你何干?」
「當然與我有關,我在西南戰場救他一命,謝將軍打算以相許,來回報這份救命之恩呢。」
前世的記憶里,這分明是該一年后發生的事,如今卻提前了如此之久。
我腦中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卻快得令人捉不住。
「你是這麼想的嗎,謝重樓?」
我不再看沈袖,只將目落在謝重樓上,他側頭看了沈袖一眼,眼中萬千:
「阿袖的心意,自然就是我的心意。」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穿到大佬黑化前
時暮穿越到一部激情,懸疑與恐怖并存的漫畫里。 作為氣質俱佳,胸大腰細女反派,凡是見到她的人都想和她來一場深夜交談,最后結局被黑化的大佬賣到了國外。 時間回到十年前,17歲的時暮第一次遇見還算純良的大BOSS。 少年在陽光下瞇著眼,問她的名字。 她戰戰兢兢:“時暮……”想了想,又說,“性別男。” “……” 沒辦法,在這種愛♀情為主,劇情為輔的世界里,只有藍孩子才能保護好自己。 只是她沒想到的是,大BOSS在一個深夜突然和她說:“我要做攻,你讓我開心,偶爾也能讓你做1。” “??????” 你他媽在說啥? 為了不被太陽,時暮隱藏性別,苦練腹肌,致力美黑,德智體全面發展,可是終究—— “你真漂亮,”大佬邪魅一笑。 時暮:QAQ小老弟你是怎麼回事??? 苗疆巫女反派X惹不起大佬 排雷:女扮男裝,不是啥正統的校園日常文,別考據。
35.3萬字7.82 6042 -
完結212 章

小月牙
樂芽有聽力障礙,她父親為了積福,資助了一個叫陳漾的好學生,樂芽得知后偷偷去看他長什麼樣。 陳漾是老師們眼中的好學生,謙讓、有禮。 但全校都知道,他私下乖戾心狠,打起架來不要命。 然后她在圍墻下被陳漾抓住,強硬地渡了一口煙。 再后來,樂芽翻墻進校,剛好經過的同學都看到陳漾在下面接住,將她抱了個滿懷,一向無欲無求,偏偏這時滿腔柔情。 只有樂芽知道,陳漾是死死勒住她的腰,吻她唇角。 “就是死,你也只能死在我懷里。” 被資助的那天起,他就盯上了象牙塔里的公主。 陳漾的人生,第一次動怒為她,第一次生病因為她,所有的第一次都是她的。 陳漾:“我一無所有。” 樂芽:“我養你啊。” 沒二手煙,假的。 病態窮小子x有錢小軟妹
31.1萬字8.18 3842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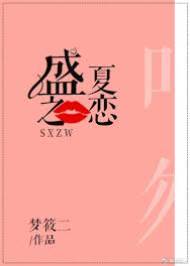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9024 -
完結651 章

太太不裝乖了,禁欲前夫寵又撩
薑聽生得美,溫柔又體貼,一身白大褂也難掩風姿。但誰也不知道,她結婚了。老公不僅不常回家,難得回來一次,還是為了提出離婚。薑聽隻愣了一秒,藏好孕檢單點頭同意了。可誰知,科室空降綠茶實習生,背後靠山竟是她老公!薑聽作者:?這誰能忍?拜拜就拜拜,下一個更帥。手續辦完後,她的小日子愈發風生水起。科研拿獎無數,升職又加薪,就連桃花都一朵一朵開。後來,前夫真香打臉了。“老婆,複婚吧。”薑聽笑了,“朋友一場,給你在眼科加了個號,先治好了再說。”
116.1萬字8 19507 -
完結162 章

超甜!重生后霸總老公專寵我
【重生➕甜寵 ➕萌娃 軟萌小撩精x超寵小撩精的高冷霸總 】上一世,蘇檸慘遭繼妹和白月光男神算計,含恨而死。而她,到臨死前才知道,原來自己最痛恨的那個男人,愛她到深入骨髓。 這一世,她發誓,她親手手撕渣男賤女,讓他們永世不得超生!她還要把全世界最寵的愛,通通都給墨景懷! 整個帝都都知道,墨氏集團墨景懷只手遮天,富可敵國,為人陰鷙又偏執,卻唯獨對家里的小嬌妻,萬般寵愛! “老公~那個粉鉆項鏈好好看!” “買。” “老公~最近D家上市了新款包包誒!” “一個系列的都給你買回來!” “老公~我還想買……” “買。” …… “老公~今晚有點累,我可不可以休息一晚?” 墨景懷一把拉住女人,附身在她耳邊,嗓音沙啞又魅惑,“寶寶,什麼都答應你,這個可不行哦。”
28.9萬字8 1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