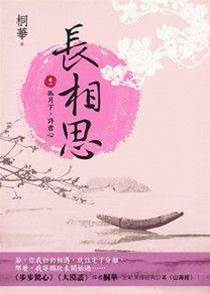《掌中嬌臣》 第222章 被繼妹牽著
翁汝舟心中登時一喜。
正要一句“兄長”,云錦斕的眼睫卻慢慢垂下,目若有若無之間,似乎落在他的手上。
他的小指指尾,正被繼妹牽著。
翁汝舟目也跟著看去,看見自己的手,心中險些跳兩拍。
連忙收回指尖。
溫熱一消退,指尾重新被冰冷包裹。
翁汝舟見云錦斕狀況奇差無比,連忙吩咐后邊的下人上前,將云錦斕抬到擔架上。
大夫已經派人去請,估計很快就到府邸上,府里還有治皮外傷的藥,現在還能派上作用。
心里七八糟地想著一堆事,旁經過的下人道:“二小姐,大公子似乎有話要跟你說。”
翁汝舟忙收回神,半蹲在擔架旁,“兄長。”
云錦斕的似乎也沒有了,薄薄一抿,半晌才吐字:“過幾日是中秋宮宴……”
宮宴?
Advertisement
翁汝舟有些懵,不明白云錦斕為何提此事,只聽他又繼續道:“衙署一定多事,你去把這一段時日未理的卷宗給我抱來。”
竟是為了公事?
翁汝舟看著云錦斕這幅半死不活的樣子,還要強撐著子勞公事,一時心中緒漫起又落下,但也只能緩緩點頭:“好。”
*
一路來到衙署,翁汝舟輕車路,取了云錦斕的卷宗,順帶將自己的事也理了。
忙完這些事,天已然黑了下來。
翁汝舟抱著一沓文書踏下臺階,燈籠的微落在臉上,照出細細的絨,一手提著燈籠沿著宮道走前幾步,一道聲音忽然從后將住。
“喂!那個造房子的!”
翁汝舟步子微頓。
左右看了一眼,沒人,似乎是在,只能回過頭去,提起燈籠。
昏暗的空間瞬間被燈籠的暖照亮,幽暗被驅散,出一人一馬。
Advertisement
為首牽馬的子站在朱墻下,一颯然騎裝,一側的頭發用紅繩纏了個辮子,懶散地垂落在肩前,兩邊的耳釘在夜下閃著細碎的。
翁汝舟看著,疑道:“沙吾列公主?”
“知道是我,還不過來?”
“哼”了一聲,語氣頗為驕縱。
翁汝舟有些無語。
左右看了一眼,沒見邊出現侍從,連那陪伴使臣的柳大人都不知道哪去了,只好提步走到沙烏列的前,問:“公主,有何貴干?”
沙烏列此時面不太好,見翁汝舟過來,將手在這個員的面前,盯著這個清冷神的人,道:“你扶我上馬。”
上馬?
翁汝舟看了一眼公主的馬,再看向沙烏列,沒有出手,只是語氣微微嚴肅,“宮道不準騎行,除非圣上特地開恩肯允。”
見拒絕,沙烏列不由得撇撇,也知此事不能勉強,只好道:“那怎麼辦?我的傷了。”
傷了?
翁汝舟有些意外,看向沙烏列,目巡視一圈,“傷在哪個部位?”
“膝蓋。”
沙烏列說著,一把開角,將起,出里邊白皙的小還有膝蓋。
翁汝舟提著燈走去,蹲細看,只見的膝頭又青又腫,因為破了皮,還有鮮滲了出來,瞧起來目驚心得很。
猜你喜歡
-
完結532 章

侯府嫡女打臉日常
三屆最佳女配得主秦婠,一朝穿越成了侯府即將被趕出門的假千金。 這個身份一看就知道,不是女配就是炮灰! 秦婠摸了摸自己的血玉鐲,呵,當女配,她是專業的! 嬌憨、蠢白、惡毒、腹黑、白蓮,任君挑選。 被甩了巴掌的大哥:「英姿颯爽有將門之風,婠婠果然才是我侯府的人」 被眾人指責的伯府嫡女:「婠婠太可憐了,我怎麼能這麼對她?」 被罵到抬不起頭的紈絝公子哥:「婠婠說的對,我簡直一無是處」 只有某個披著羊皮的太子爺,冷哼一聲:「來,請繼續你的表演」 秦婠:「太子哥哥在說什麼,人家聽不懂呢……」 太子:「呵」
96.7萬字8 36757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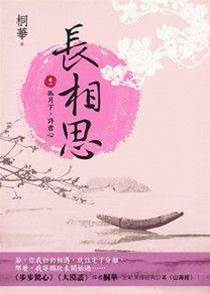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