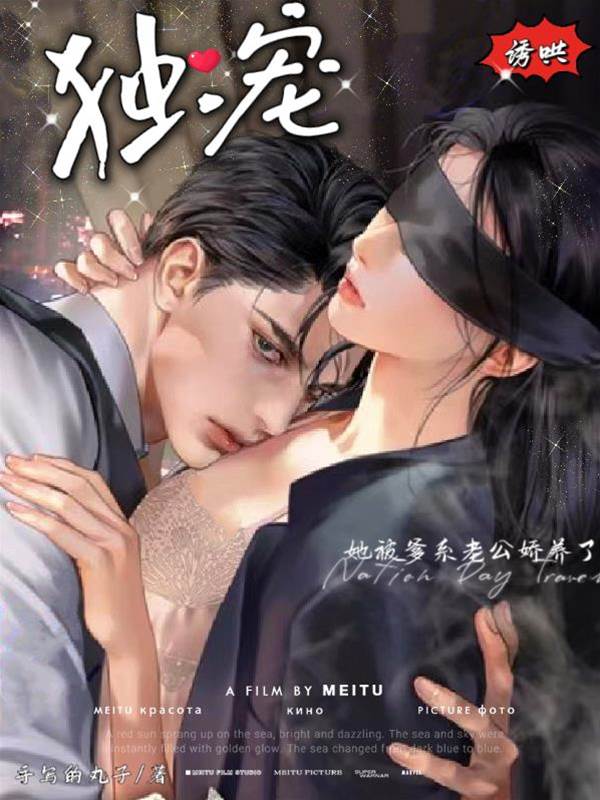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暗里著迷》 第120章 恨
紀錚角碎了,鮮紅的流了下來。
周延禮似乎沒打過癮,掄起拳頭還想來一拳,周今甜尖道:“哥,別打了。”
“哥,我和他自己解決就好了。”周今甜往前走了一步,平靜的對著紀錚說道:“我們去外面聊吧。”
兩個人走到了外面,醫院的走廊很安靜,他們能夠清晰的聽到彼此的呼吸聲。
周今甜雙手放在了后,小聲的說道:“對不起,是我哥哥太沖了。”
拿出對待陌生人的那套禮貌對待著紀錚。
紀錚懶洋洋的掀了掀眼皮,拿出無所謂的態度:“明天需要你出席公司的記者發布會,我早上來接你。”
“我不去。”周今甜拒絕的非常果斷,好像沒什麼理由幫這個男人。
紀錚抹了抹獻干涸的角,靠近一步,在耳邊低語道:“你是想讓你哥哥也一起贖罪麼?”
“你別惹他。”周今甜往后退,知道周延禮的脾氣,最后不斗個你死我活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我去,我欠你的。”周今甜故意說道。
然后轉頭走進了病房,將那個男人隔絕在外。
池景深著披散下來的黑發,臉上很自責:“甜甜,對不起,是我沒有保護好你。”
周今甜猛的抬起頭,這樣的場景實在是太過悉了。
周延禮看著兩人,問道:“甜甜,晚飯想吃些什麼?哥哥去給你買。”
“都可以。”周今甜笑著回答道。
病房里再次只剩下和池景深。
“我們,之前是不是認識?”周今甜沒頭沒尾的來了這麼一句,一抬頭,就撞進了男人的出水的眼眸之中。
被塵封的思緒慢慢從黑暗深涌起,在那些漫長無聊的歲月里,終于有一陣乍起的狂風。
Advertisement
滿地的花瓣,復古的歐式秋千,還有翩翩起舞的白蝴蝶,五歲的周今甜坐在秋千上,稚的聲音一遍一遍的喊著:“池哥哥,再推高點,再推高點。”
“好,那甜甜要抓穩了。”站在小孩后的大男孩說道,他滿臉的寵溺,“我要推了哦!”
池景深加大了力度,沒料想周今甜不知怎麼的會松了手,整個人從秋千上摔了下來。
“甜甜,甜甜!”池景深一直在喊著,自責的將扶起,然后蹲在的面前說道:“對不起,是我沒有好好保護你。”
周今甜拍了拍子上的灰塵,看到面前的人這般著急,都沒好意思哭出來,堅強的從自己的小包包里掏出了兩顆水果味的糖遞給了池景深,“哥哥,給你吃。”
池景深將兩粒糖放在口袋中,著的腦袋,輕聲說道:“哥哥以后娶你好不好?”
周今甜忘記那時的自己是怎麼拒絕的。
但是那兩粒水果糖卻被池景深收藏至今。
記憶被串一銀線,周今甜錯愕的抬起頭,“池哥哥?”
久違的稱呼讓池景深的軀也震了一下,他頓時熱淚盈眶,“甜甜,你終于想起我來了。”
兩人敘了會兒舊,周今甜嘆道:“如果這個時候能喝點小酒就好了。”
池景深很是無奈:“你到底是怎麼變現在這樣的小酒鬼的?”
“對了,既然我們認識的這麼早,那你知道我五歲以前消失的那些記憶嗎?”周今甜問出了心底里的疑,之前也不是沒有問過,但不管是周延禮還是周父,都不愿向提起。
他們只說不小心出了車禍,是一段很可怕的痛苦記憶。
池景深了下顎的牙齒,斟酌了很久,慢慢說道:“甜甜,其實......你不是出了車禍。”
Advertisement
“我回來了。”周延禮推開病房的門,他手里拎了很多食,從米飯到面條到應有盡有。
周今甜止住了剛才的話題,擰著眉站了起來:“哥,你怎麼買這麼多呀?”
“想吃什麼就吃,剩下的給哥哥。”周延禮回答道。
三個人相的其樂融融,有那麼一瞬間,他們好像真的回到了小時候。
到了半夜,周今甜躺在病床上想著池景深說的那些話,他說自己不是出了車禍,那自己到底是怎麼失憶的呢?
而且和池景深那麼小就認識,肯定是通過兩家的長輩相識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池母會不會也對當年的那些事有些了解?
星辰漸漸消失在夜幕之中,晚風低淺唱,在太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時,歌聲戛然而止。
關臨來的很早,吵醒周今甜后先是關心了一番的病,然后才說起正事:“紀總在星河灣等你。”
“直接去發布會不就行了麼。”周今甜披起昨天的那件淡紫外套,將頭發隨意的扎了一個低馬尾。
關臨解釋道:“您還需要打扮一下,而且發布會是有記者提問環節的,您可能需要背一下答案。”
周今甜嘲諷似地笑了一聲,不想多為難關臨什麼,他們都沒做錯,所以很乖的上了轎車。
悉的街景穿流而過。
關臨只把送到了電梯口,恭敬說道:“您上去吧,紀總一直在等您。”
他總是“您您您”的這麼說著,周今甜聽了好幾次想笑,但是笑意很快就又被郁悶的煩躁打敗,腦子里的不行。
周今甜摁著碼,面無表地進,再關門。
紀錚就靠在門關,長臂疊,懶洋洋的倚靠在墻上,他好像鐘這個作。
Advertisement
“服和臺詞稿呢?”周今甜冷漠的問道。
紀錚眼神一,沙啞開口:“你和池景深是什麼關系?”
網上有關他們的緋聞愈加熱烈,即使覺得再不可能的事,看到那些有眉有眼的報道時,還是會有一瞬間的焦慮。
那種相信卻無可奈何的焦慮,想要去尋找證明真相的任何蛛馬跡時,其實就已經輸了。
“什麼關系?”周今甜重復了一遍這個問題,覺得很荒唐,扯了扯角說道:“什麼關系都和你沒有關系了吧?”
他們只不過是差最后一步離婚沒完的仇人而已。
“周今甜。”紀錚咬了咬后槽牙,低聲音了一聲。
周今甜心底一,想要從這里逃離出去,轉過準備開門,門只打開了一個隙,就被后的男人“啪嗒”一聲關上了。
紀錚一只手臂撐在門上,將周今甜錮在自己的懷里。
淡淡的檀香四起。
周今甜艱難的轉過了,不愿意與他對視,有些生氣:“你到底想干嘛?”
紀錚的吻如夏日里的暴雨,銀河倒瀉,從到脖子再到鎖骨,他沒有放過每一寸的理,如同疾風如同伏雨,空氣中彌漫起旖旎。
周今甜一直在不停的掙扎,用力推開上的男人,后背抵在門把手上,生疼生疼的。
紀錚的手從的細腰旁穿過,微微拱起抵在的背后,這個姿勢讓兩個人靠得更近,他的嗓音比剛才還低沉了兩分,“你和池景深到底是什麼關系?”
“和你有什麼關系?”周今甜依舊是那個回答。
紀錚的作停頓了一秒,就當周今甜以為他會轉而走,以為一切都要結束了的時候。
男人眼框發紅,像是撕裂的野,他扯開了周今甜的領,右手著的皮慢慢游走,所到之都掀起了一陣火。
Advertisement
會發生什麼,不言而喻。
周今甜眼底漸漸彌漫起了水霧,噎噎道:“紀錚,你別我恨你。”
哭的越來越兇,淚水跟斷了線的珍珠不停的往地下落,連著整個肩膀都在止不住的抖著。
紀錚慌了,思緒被拉了回來,停下了一切作。
男人直起子,沒有多余的溫,轉走進了書房里。
周今甜靠在墻上,慢慢落。
紀錚一拳捶在了墻壁上,關節立馬紅腫了,他喝了點涼水,然后給關臨打了個電話:“上來。”
關臨進了門,大概也清了發生了什麼事,他嘆了口氣,把紀錚昨天晚上準備好的服和臺詞稿都給了周今甜,“太太,您就大概看一眼就好,回答不出也沒事。”
紀總是不會讓陷尷尬之地的。
周今甜換好了服,來了兩個化妝師,一個給做發型,另一個為化著妝,房間里很安靜。
關臨去了書房,“紀總,您是不是剛才又和太太吵架了?”
“的電影什麼時候上映?”紀錚問道。
關臨回答了一個日期,男人點了點頭,“以你的名義包個兩百場吧,錢我私人出。”
“好。”關臨記下了。
周今甜坐在鏡子前,直到關臨來,才有一些知覺。
在星河灣里只到了抑,只想快速逃離這個地方。
紀錚和在車上坐的很開,周今甜穿的是一件明的波點紗,黑的肩帶有些歪,車上暖氣很足,倒不是很冷。
男人皺了皺眉,想幫拉一下肩帶,周今甜是下意識的躲開的。
紀錚手頓在半空中,修長的手指逐漸抓,緩緩地了回去。
事,好像不應該變這樣無法挽回的樣子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許你一生空歡喜
"婚後老公卻從不碰我,那我肚子裏的孩子是誰的?出軌捉奸被趕出家門…… 九死一生後,我被逼成為老公上司的情人,孕母。 本以為隻是一場金錢交易,我不想動心動情,可我卻在他忽冷忽熱的溫柔裏,失了身,陷了情。 一場情劫過後,縱身火海,再見麵,我又該如何麵對?"
21萬字8 14587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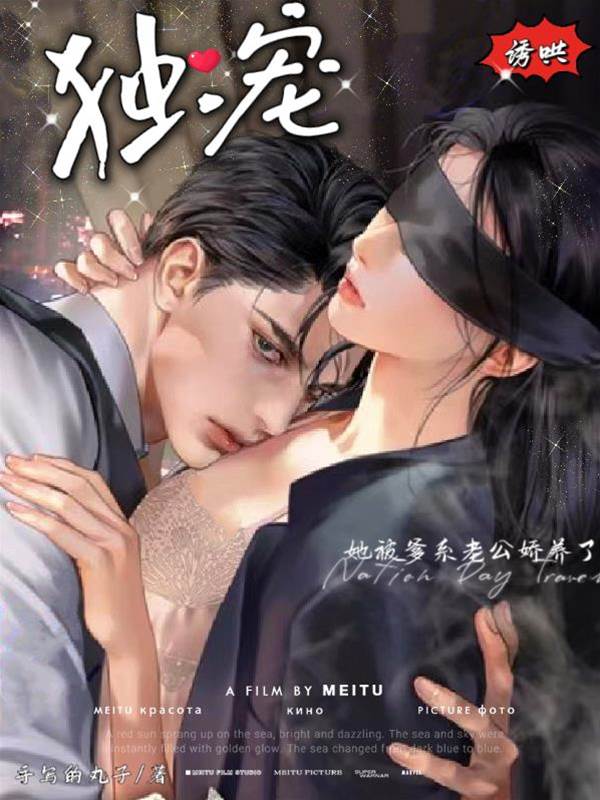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2612 -
完結182 章

嬌惹!他又野又撩,卻為我折腰
[風情萬種釣系畫家X離經叛道野痞刺青師][SC|甜欲|頂級拉扯|雙向救贖] - 只身前往西藏的第一天,宋時微的車壞在了路上。 她隨手攔下了一輛車,認識了那個痞里痞氣的男人。 晚上在民宿,宋時微被江見津的胸肌腹肌迷得五迷三道。 她溜進他的房間,將他堵在了墻角,問他:“江見津,zuo|嗎?” - 川藏南線全程2412公里,從成都到拉薩,途徑22個地點,走走停停耗時五個月整。 這五個月里,宋時微跟江見津成了飯搭子、酒搭子,還有chuang|搭子。 在拉薩逗留了半個月后,宋時微賣掉了車子準備飛機回北京。 江見津神色淡漠,只問她:“都要分手了,最后一次也沒有?” 宋時微撓了撓下巴,回:“這個倒也是可以有。” - 重逢是在一年后。 療好傷的宋時微一鳴驚人,新作品一舉拿下英國BP肖像獎的一等獎,并于同年年底在國內舉辦了首場個人畫展。 慶功宴上她見到了本次畫展最大的贊助商,那個傳說中的商界奇才。 包廂門推開,她看到的是西裝革履的江見津。 他起身跟她握手,似笑非笑地問她:“宋小姐在畫畫之前不需要征得本人的同意嗎?”
24.6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