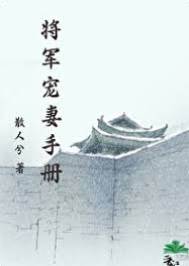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嬌女謀略》 第九百一十章 算命,貴不可言啊
先是一個道士提到自己來游說楊氏母,又是有一位表舅鼎力相助楊玉燕,并且暗示可以為楊玉燕做任何事,那怕這事還有些危險。
怎麼看這事都著玄乎。
又向楊玉燕打聽了一些那位表舅的事之后,衛月舞就讓先回去,聽消息,事還沒有到最后的時刻,切記不可枉。
當然衛月舞表示,也不會視而不見的,必然會手阻止這事的發生。
有了衛月舞的話,楊玉燕也就稍稍放了心,衛月舞的份放在這里,既然開了口,此事也就有些轉回的余地,因此就回去聽信去了。
衛月舞帶著畫末重新回了自己的清荷院。
道士,是一個游方道士,但現在正巧游到京中,據說在江南的時候見到過自己,并且游說過自己,所說的一切自己都照行了,特別是一定要和莫華亭退婚的事。
如果真的是自己執意退的親事,那麼自己和莫華亭的恩怨,就可能是自己早有預謀的,所謂的雪夜劫殺,也就不過是一場有預謀的慌言罷了。
而莫華亭就是被冤枉的。
莫華亭既然是被冤枉的,那衛艷的事是不是也有太多的不實,而自己進了京之后,李氏和冬姨娘一個接一個的倒霉,是不是就是自己有意識的害了們。
這麼一說起來,自己其實就是一個惡毒、險而且還是為了目地不擇手段的人了?
而莫華亭倒了無辜,衛艷和李氏們或者不過是犧牲品罷了!
那個所謂的表舅,起的作用就是把楊玉燕從楊侍郎府帶出來,之后便任由楊玉燕大鬧,他是楊玉燕的表舅,既便出了事,也說得過去,必竟他也是不忿楊玉燕了這麼大的委屈。
楊玉燕的事鬧大,必然會拖出道士,而道士所說又會拖出自己……
Advertisement
環環相扣,謀算不謂不細。
乍看起來是楊玉燕的事,但實際上目地卻是為了自己,而得利的人還多,一時間居然找不到誰才是下手的人。
“主子,現在怎麼辦?”聽衛月舞理清楚思路,金鈴也急了,“莫如讓世子幫著調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誰在后面害主子!”
“暫時不用!”衛月舞搖了搖手,這事燕懷涇其實是不便手的,因為關系于太子文天耀。
以燕地和京中的關系,燕懷涇對于文天耀的事絕對不能隨意的手,否則就可能引起大。
就象這次文天耀雖然要帶走自己,但出面的是四皇子,而且誰也沒提到他,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事跟他有關,但因為他是太子,代表的是京中的勢力,燕懷涇代表的是燕地的勢力,兩個人的撞代表的就是國家大事。
所以誰也不會冒冒然的讓他們兩個對上。
“那怎麼辦?”畫末也傻眼了,這事看起來怎麼看怎麼難辦,問題是雖然知道有人暗算主子,但偏偏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主子,是不是靖遠侯,他最喜歡暗算主子了!”書非咬咬牙,恨聲道,“奴婢覺得靖遠侯在這里面獲利極大,似乎事事都是主子害了他似的。”
“主子,奴婢也覺得跟靖遠侯有關,您想想,如果這些事都是您故意為之,他就是一個害者了,莫名其妙被退婚不說,還被人冤枉到現在,他現在是大皇子了,很需要一個好的名聲,所以他這樣做是極有理由的。”
羽燕雖然對莫華亭不太,但也分析的頭頭是道。
幾個丫環都覺得這個人很可能就是莫華亭,也唯有莫華亭從衛月舞進京之時就開始暗算衛月舞,甚至還想踩著衛月舞的命給他自己墊腳。
Advertisement
“走,我們去看看那座廟!”衛月舞想了想,忽然笑起來,“進京之后,我們去的最多的就是梅花庵,倒是沒去廟里看過。”
“主子,那個游方道士還不早早的走了,他只是游方道士而己,又不是廟里住著的和尚。”畫末不解的問道。
“對,主子,我們現在就去!”倒是金鈴一點既,立時點頭。
“他雖然是個游方道士,但為了扯出主子來,到時候必然要他說話,自然也會留下來,等著楊大小姐把事鬧出來!”書非也是個聰慧的,金鈴這麼一說,立時也懂了。
這接下來,便都連畫末也懂了,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奴婢想得淺了一些!”
衛月舞這次去的廟,其實倒也算得上是一座大的廟,清云寺就在京城邊上,也不是很遠。
衛月舞是帶著羽燕和金鈴去的,在府里點了一輛普通一些的馬車,并吩咐馬車上的標志取了下來。
&n
bsp; 馬車便緩緩的行出了燕王府的大門,直接城外的清云寺而去。
清云寺不同于梅花庵的幽靜,山門外居然還有一個大的集市,許多人在那里做買賣,有賣香的,還有賣蠟燭的,以及一些燒的紙之類,還有一些吃的東西,以及小孩子玩的,特別的熱鬧。
衛月舞還沒有見過這麼熱鬧的寺廟。
在山上拜過佛之后,衛月舞便戴著帷帽,和兩個丫環隨意的在集市上走了走。
集市上的人不,都是上山來參拜菩薩的香客,有些還是有錢人家的貴夫人和小姐,看得出出手都很大方。
象衛月舞這樣戴著帷帽的世家小姐也不。
這里算得上是熱鬧的場所,世家千家雖然不便過于的拋頭面,但是偶爾來到這麼熱鬧的地方,總是會想著走一走,戴著帷帽倒也是正常的很。
Advertisement
集市的一角,擺著一個不大的攤位,坐著一個神看起來并不是很神的道士,這些正趴著在那里打磕睡,邊上的招牌寫的清楚,“鐵口直斷”,旁邊還放著一個卦筒。
不過集市雖然熱鬧,他這里倒是安安靜靜。
但看他這麼一副樣子,就知道他沒生意也是理所當然的,昏昏睡,而且還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找他鐵口直斷的才怪,也不知道楊玉母是怎麼找上這麼一位的。
“喂,有人沒有!”羽燕過來不客氣的道。
偏偏這位還真的睡著了,這會睡的天昏地暗,竟然沒聽見羽燕的話。“喂,有人沒,送錢來了!”金鈴手一,直接拍在桌面上,大聲的道。
“錢,誰送錢來了,賭的錢送來了?”道士被驚醒了,大喜著東張西道,怎麼看都著幾分委瑣,哪里有半點得道高人的樣子。
“我們主子想問一卦!”金鈴手又是一拍,這才把道士的注意力轉移了過來。
看清楚面前的主仆三人,道士馬上滿臉陪笑:“這位主子,您要算什麼啊?”
“你這算的準不準 ?”金鈴冷著眉道。
“準,當然準,不準不要錢。”道士哈哈笑道。
“那你算上一算,我們主子是誰?”金鈴上來就給道士一個難道。
“這個……還需要你們主子的一件件……或者主子寫一個字也可以!”道士點頭哈腰的笑道。
他長年招搖撞騙,也不是沒有一點本事的,最會的就是查觀,這會一看眼前這幾位的氣勢,就知道是非富則貴的。
衛月舞拿起一邊放置的筆,隨意的寫了一個“問”字,然后扔下了手中的筆。
道士接過,看了看,立時滿臉的驚意,抬頭看了看衛月舞:“這位主子小姐,貴不可言,貴不可言啊!”
Advertisement
“如何一個貴不可言?”衛月舞淡淡的出聲道。
“主子,您的份尊貴,您以后的份會更尊貴,將來更是會……”道士說道這里聲音放輕了下來,手沖著一個方向指了指,“您以后會在那邊做主的。”
衛月舞順著那個方向看了看,皇宮的方向,或者說東宮的方向也在那里。
“你胡說,我們主子己經嫁人了!”金鈴大怒,手拍了拍桌子。
“嫁人了也沒關系啊,那些命之的,又豈是個個一嫁就嫁對了的!”道士滿不在乎的道。
“命?你是說我們主子……”羽燕一臉驚駭的接過話題,但聲音也低了下來,“之前不是有命一說,那是靖大小姐……”
“靖大小姐的事就這麼一說而己對吧!你們別不相信我,我這里是鐵口直斷,等將來你們主子貴不可言之后,就會明白我沒有胡說。”道士越說越玄乎,而且一口咬定衛月舞就是貴不可言的,當然將來的事還需將來考證,誰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的。
但既便不是真的,誰不愿意自己將來貴不可言呢!
“你這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衛月舞問道。
“當然是真的,主子,您將來如果真的貴不可言了,可別忘記了我!”道士搖頭晃腦,繼續忽悠道,他這幾天天天在這里睡覺,倒是沒什麼生意,好不容易一個生意上門,當然是能忽悠繼續忽悠了。
“好,你跟我過來,到那邊說話!”衛月舞指著山徑小路的一個小的亭子道。
“行,行,主子您說什麼是什麼,主子您雖然貴不可言,但必竟還有一段路要走,我這里有幾個卦正要送給主子。”道士一邊忽悠一邊收拾東西。
想不到還會有筆意外之財過來,心里豈會不高興……
猜你喜歡
-
完結1601 章

邪王寵妻:廢材狂妃要逆天
一朝穿越,她成了被人丟青樓的大學士嫡長女。親爹為前途廢嫡立庶,夠狠;姨娘貪材私吞她嫁妝,夠貪;庶妹虛偽奪她未婚夫,夠賤;比狠,火燒太子府;講貪,一夜搬空國庫;論賤,當街強搶美男。若論三者誰之最,當數司徒大小姐第一。某天,司徒大小姐滿腔怨怒:「左擎宇,你真狠!」「多謝愛妃誇獎。」靠近她的所有男性一個不留。「你太貪!」「必須的。」一天三餐還不飽,半夜還要加宵夜。「你真賤!」
286.3萬字8 36945 -
完結426 章

迫嫁為妾
大婚前夕,連續七夜被人擄走再被送回,唯一記得的便是那裊裊檀香中的幾度糾纏。未婚而錯,被浸豬籠,她求速死,卻連死都變成了奢侈!想要嫁的,終未成嫁。恨著的,卻成了她的天她的地,一朝得寵,卻只落得風口浪尖上的那一隻孤單的蝶,蝶舞翩躚,舞着的不是情,而且他給予她的深深罪寵
71.7萬字8.18 57844 -
完結344 章

邪王霸寵:逆天六小姐
世人皆知,君府六小姐靈力全無,廢材草包,花癡成性;世人皆知,當今景王天賦異禀,風姿卓越,邪魅冷情;她,君府草包六小姐,世人辱她、罵她、唾棄她。他,北辰皇室景王爺,世人敬他、怕他、仰望他。他們雲泥之別。然而,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她,是他的‘天情’。
90.7萬字8 59938 -
完結991 章

別人修仙我修命,女主也沒我命硬
【穿書、修仙、女強、系統、火靈根、槍法、無官配。】楚落穿書到修仙界,綁定氣運系統,開局氣運倒扣9999點。原來是因為自己和雙胞胎姐姐是并蒂雙生花的命格,自己的氣運全都被胞姐,也就是原小說中的女主給吸走了,而自己的親人竟然為了讓女主成為氣運之女,想要將自己徹底殺死!憑著最后一口氣,楚落逃出了那修羅地獄,此后開啟新的人生。“我是個倒霉蛋,我師尊是個死變態。”“他們住碧落峰,我住在黃泉谷。”“但那又如何,我一日不死,就命硬一分。”“待到氣運負值清零那日,便是你我決一死戰之時。”“你,敢來赴約嗎?”
175.8萬字8 15949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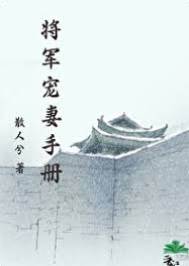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