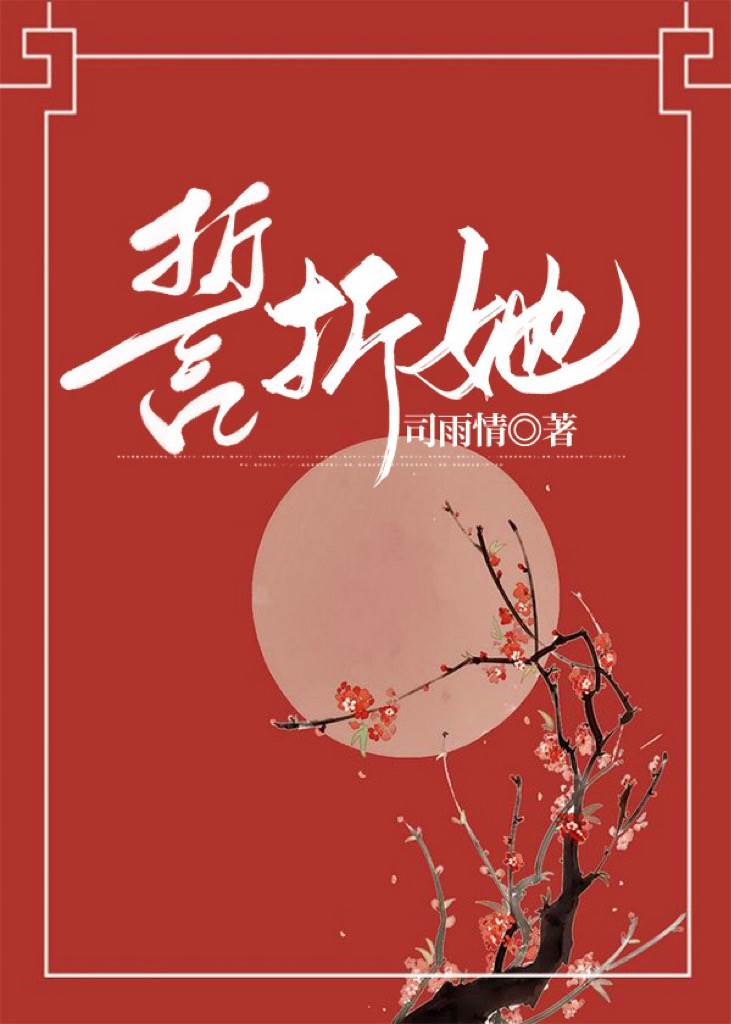《燕辭歸》 第272章 請她吃個飯
宮門外。
徐簡與單慎前后下了轎子。
不久前宮里使人來傳信,說是太子殿下回東宮了,他們兩人便過來了。
單大人打了一把傘,抬頭看向徐簡。
輔國公亦打了傘,傘面得偏低,單慎看不見他的神,只覺得國公爺哪怕狼狽、也比自己看起來拔些。
“真不用收拾收拾?”單慎心里不踏實,一面問,一面甩了甩自己漉漉的、還能再滴點水的袖子。
案子急,雨又不見小,先前他也就沒顧上這些。
剛宮里一催,他自己也急,就這麼來了。
直到到了宮門外,一子不自在就從后背冒出來了。
他單慎為多年,何曾如此儀容不整地進過宮?
落湯,能進宮?
“不打,”徐簡道,“殿下此刻也狼狽,單大人收拾得整整齊齊,反倒不是辦案子的樣子。”
單慎想了想,也對。
卻是沒料到,徐簡后頭還跟了一句:“大人清早見到太子時,比現在還糟糕吧?太子應是見怪不怪。”
單慎:……
他昨兒半夜還見著了溜溜的太子殿下,他往后是不是無論殿下穿什麼,也該見怪不怪了?
徐簡本意就是上尋了樂子,見單大人一臉無奈,便又笑了聲,打著傘先往宮門去。
宮人在前頭引路,一直引到了東宮外。
單慎是頭一次到太子宮室來,左右一看,總覺得不太對勁。
“人手這麼?”他低聲與徐簡嘀咕。
“原先的侍衛都被大人去順天府了,”徐簡亦看了兩眼,“侍宮確實了,還眼生。”
這麼一說,兩個人都心知肚明。
東宮的人手已經撤換了。
那些只護著太子,往圣上那兒傳報太子狀況時說一半、留一半的人,都被換了。
Advertisement
現在換上來的,應當都是曹公公耳提面命、挑選出來的兵良將。
一位侍上來迎接:“輔國公、單大人,太子殿下正在沐浴,兩位坐一會兒。”
徐簡打量他。
這侍四十出頭模樣,個頭不高,眼睛很小。
徐簡認得他。
他姓郭,很得曹公公信任。
徐簡和單慎等了差不多有一刻鐘。
郭公公的茶泡得不錯,但他讓廚房送來了姜茶,另有點心,是膳房的手藝。
單慎滿腦子惦記著案子,沒顧著自己的手,一塊接一塊,等他發現時,已經大半碟都進了肚子。
“哈、哈哈……”他尷尬地笑了笑。
徐簡抿了口姜茶,道:“大人從昨晚上忙到現在,都沒顧上填肚子吧?”
單慎臉上紅。
確實很,確實很香,但這都不是他在東宮吃這麼多的理由。
也就是太子殿下太慢了……
正想著,李邵總算出來了。
他換了干凈裳,長發披著,一邊走,他一邊拭上頭的水珠。
“讓你們久等了,”他坐了下來,“我回宮后不太舒服,怕雨后寒就趕去洗了洗。平日里怎麼請太醫都無所謂,這個當口上說‘病了’,不像回事。”
單慎忙道:“您要。”
再怎麼說,這位都是圣上的寶貝兒子。
淋了大雨后就這麼問案,真有個病痛,他單慎也麻煩。
就像是萬塘,橫沖直撞、厲害得不得了,他能把劉迅丟出去淋雨醒酒,卻不敢太子一下。
李邵醒來,順天府里還得趕上姜茶。
如此想著,單慎又道:“先干頭發,再喝點姜茶緩一緩,問事不差這一時半會兒。”
李邵拿起茶碗,一口喝了:“這就問吧,不能再耽誤你們查案子。”
Advertisement
單慎點頭,把案子的來龍去脈,又問了一遍。
徐簡陪坐在旁,一言不發。
不得不說,李邵這會兒老實得過了頭。
單大人問什麼,他就答什麼,答不上來的,就直接說“不知道”。
如此態度,頗有一種摔狠了之后、突然醒悟了的通。
可徐簡清楚,這些都是表象。
因為李邵這人無藥可救。
視線從李邵時而繃、時而舒緩些的眉宇間,落到了他的坐姿,又落到了他藏在桌案下的手上。
因著角度關系,單慎看不到太子殿下的手,徐簡卻窺到了些。
李邵的手攥了拳,極其用力。
那是克制。
不是克制煩躁、惱怒,而是克制興。
在單慎喝茶潤嗓的間隙,徐簡開了口:“殿下,您先前去了哪里?”
“永濟宮,”李邵道,“我跟父皇也是這麼說的,我被二伯父罵了一通,自己也曉得闖禍了,就干脆去了永濟宮,看看犯錯的皇子是個什麼樣的。”
徐簡又問:“見到永濟宮里那位了嗎?”
“見到了,一個瘋子,我不會聽他的。”李邵前說過一遍,此刻面對徐簡,自然也是同樣的話語。
徐簡聽完,微微頷首,沒有再問什麼。
等單慎全部問完,兩人起。
李邵送他們出大殿,站在廊下看著雨簾,道:“給你們添麻煩了,我就不送了,讓郭公公送你們。”
徐簡行禮,舉著傘往外走。
李邵目送他們離開,直到那兩人出了東宮,他勾著角冷笑一聲。
口震,其中余下的緒作“痛快”。
看吧!
他是皇太子,是父皇最看重最喜的兒子,不過是足些時日而已。
因為他又一次,從書房里全而退了。
腦海里回憶著從永濟宮出來,直到剛才的一幕幕,李邵想,他理得真是太完了。
Advertisement
父皇沒有質疑他,單慎問來問去也就那些,就連里沒一句好話的徐簡,亦是奈何不了他。
先前晾他們一刻鐘,徐簡和單慎能說什麼?
不一樣要勸他保重嗎?
畏懼在邁出書房的那一刻已經消散了,但那激一直延續了下來,直到這一刻,依舊鼓著他的心。
李邵又笑了下。
李浚無疑是個瘋子。
瘋子教他的那些,不用聽也不用信。
但瘋子也會有一兩句說得對的話。
明明怕得要命,但渾都起皮疙瘩的激與興,真的很讓刺激。
他也很喜歡。
可惜,不得不收斂些日子了。
再想嘗到這滋味,還得再過一陣子。
父皇會關他多久呢?
李邵現在拿不準,唯一能肯定的是,不會晚于九月二十五。
那是母后的忌日。
另一廂,徐簡與單慎行走在宮道上,誰也沒有談的意思。
宮里人多雜,不是個商談的好地方。
直到回到順天府,單慎才松了松繃的神,活了下酸脹的筋骨,問道:“從太子的說辭來看,那幕后之人藏得很深啊。
衙門里嘛,看似是抓回來八九十十幾號人,結果都是棄子,加一塊都說不出點花頭來。
老萬若是在宅子里再沒點收獲,我都不知道明日早朝有人問起來,要答些什麼。”
“這也怪不得單大人和萬指揮使,”徐簡道,“那人險,有備而來,前后謀劃這麼久,自然不好抓。”
“話是這麼說,但該給的結果也都要給,”單慎重新翻看了師爺整理出來的供詞,苦惱著問,“我要是一問三不知,沒一點進展,不了差。國公爺,我總不能到時候拿太子邊的侍衛可能妄圖綁過人這種破事去差吧?”
Advertisement
徐簡呵地笑了笑:“單大人要是不想當順天府尹了,可以試試。”
他應對坦然又隨意,一如既往地著點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意思,本不像與綁人案子有一丁點聯系的模樣。
單慎當然也沒有看出來,只苦笑兩聲。
兩人正說著,張轅快步進來,臉不太好。
“還有一個舞姬至今未醒,還起熱了,燒得厲害,”張府丞說道,“早知道先前請安院判都查看一遍了,當時只顧著太子、沒顧著旁的,我剛又讓人去請大夫了。”
單慎一聽,苦笑徹底變了苦。
出人命,和沒出人命,是兩回事。
徐簡又翻了些案卷,起去陳米胡同。
兩個衙門的人手都還在忙,萬塘與徐簡問候一聲,指著院子里那些高大樹木道:“我恨不能連拔起來。”
徐簡想了想,道:“不行就還是拔了吧,我四轉轉。”
萬塘長嘆一口氣,示意徐簡隨便轉。
徐簡在宅子里轉了一個時辰,全無收獲。
他對此也不意外。
被道衡背后的人扔出來的斷尾,肯定都被收拾干凈了,不想被他們察覺到的線索,定然是一點都不會留下。
而留下來的,十之八九就是故意喂給他的“餌料”。
那雙手向來都是這樣。
天暗下來前,雨停了,從天看,再明日天亮之前應該都不會再有落雨。
徐簡回到順天府,與單慎說了宅子那兒的狀況。
單慎苦惱萬分。
“那舞姬醒了嗎?”徐簡問。
“迷迷糊糊給喂進去一點水,”單慎搖頭道,“燒得很兇,我又厚著臉去請安院判來了一趟,他說不樂觀,就看能不能自己熬過去了。”
這種事,原本哪里敢勞煩太醫院?
還不是眼瞅著滿城風雨,再讓外頭知道出了人命,更加糟糕。
單慎對著滿桌子鋪開的文書,只覺得這輩子沒辦過這麼棘手的案子。
牽扯到的人,很麻煩。
背后線索,毫無蹤跡。
他一辦案的本事,眼瞅著使不上勁。
聽見腳步聲,單慎抬頭看了一眼外頭,是參辰抱著一布包來了。
“什麼東西?”他不由問了一。
“干凈裳,”徐簡從參辰手上接了,又與單慎道,“隔壁屋子借我收拾一下。”
單慎挑了挑眉。
輔國公今兒沒淋雨,真在乎不的,堅持不到現在。
可既然都到這會兒了,有必要在衙門里就換新的嗎?
以往在順天府,國公爺是有多晚就陪坐到多晚,從沒有提早走人的時候,今天即便想休息,等回到府里洗個熱水澡、再換裳,不是正好?https:/
單慎不解,不多時,就見徐簡穿戴得整整齊齊從隔壁出來了。
干凈、矜貴,和他們這幾個奔走了一整天的落湯,截然不同。
見單大人打量,徐簡輕笑了聲:“勞煩郡主幫了個忙,請吃個飯,邋邋遢遢過去不是回事。”
單慎噎了一下。
徐簡又道:“不遠,一會兒給單大人也帶些回來。”
“客氣客氣,”單慎聞言,心神順暢許多,“那我等著。”
徐簡走出順天府。
劉靖正好趕到。
下朝后,他與徐緲說完事后,就又回去了千步廊。
倒不是不關心兒子,他擔心劉迅擔心壞了。
可他只能如此。
如果不務正業,到找關系去求,不止幫不上迅兒,還會愈發壞事。
圣上沒有停他的職務,他還是鴻臚寺卿,那就必須做好政務。
無頭蒼蠅一樣的臣子,是不了圣上的眼的。
現在,他每一步都不能走錯。
兩廂打了照面。
勢不同了,劉靖開口時十分克制,沒有一點惹事的意思。
“迅兒在順天府還好嗎?”他問,“有代出什麼有用的消息嗎?”
徐簡道:“劉大人可以去問單大人,親屬關心案,只要能說的部分,衙門肯定會告知。”
“你讓你母親和阿娉去廟里住了?”劉靖又道,“也好,我這幾天顧不上們,廟里清凈些。”
徐簡無意與劉靖多言,見馬車備好了,便收傘上車。
劉靖見狀,轉進順天府。
桃核齋的后院里,何家嬤嬤正備菜。
林云嫣先到了,從書房里拿了手爐出來,問嬤嬤添了點炭,試了試溫度。
進宮出宮,又是順天府,又是陳米胡同,確定徐簡今日沒有拿手爐。
偏今兒雨大涼意重,腳肯定不舒服。
剛攏好,徐簡也就到了,隔著廚房的門看林云嫣。
何家嬤嬤見了他,笑道:“爺和郡主稍候,熱菜一炒就能上桌了,小火上熬了點姜茶,您先用一點。”
徐簡應了聲,又道:“今日喝了不姜茶。”
林云嫣朝他走過去,側著子從門里往外,把東西塞給徐簡:“今兒一定沒有拿手爐。”
說完這句,就往書房那側去了。
徐簡輕輕掂了掂手爐。
熱氣烘烘的。
小郡主火氣也烘烘的。
得虧換了裳才來,要不然,有的哄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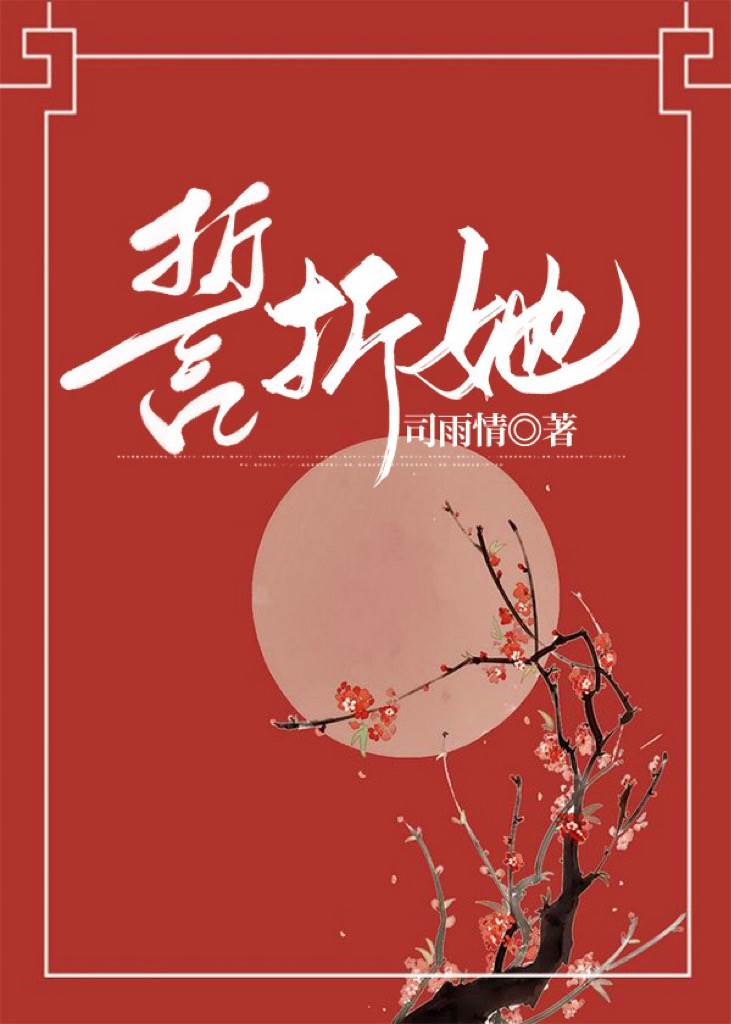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170 章

娘娘嫵媚妖嬈,冷戾帝王不禁撩
一紙詔書,廣平侯之女顧婉盈被賜婚為攝政王妃。 圣旨降下的前夕,她得知所處世界,是在現代看過的小說。 書中男主是一位王爺,他與女主孟馨年少時便兩情相悅,孟馨卻被納入后宮成為寵妃,鳳鈺昭從此奔赴戰場,一路開疆拓土手握重兵權勢滔天。 皇帝暴斃而亡,鳳鈺昭幫助孟馨的兒子奪得帝位,孟馨成為太后,皇叔鳳鈺昭成為攝政王,輔佐小皇帝穩固朝堂。 而顧婉盈被當作平衡勢力的棋子,由太后孟馨賜給鳳鈺昭為攝政王妃。 成婚七載,顧婉盈對鳳鈺昭一直癡心不改,而鳳鈺昭從始至終心中唯有孟馨一人,最后反遭算計,顧婉盈也落了個凄然的下場。 現代而來的顧婉盈,定要改變命運,扭轉乾坤。 她的親夫不是癡戀太后嗎,那就讓他們反目成仇,相疑相殺。 太后不是將她當作棋子利用完再殺掉嗎,那就一步步將其取而代之。 如果鳳鈺昭命中注定要毀在女人手上,那麼也只能毀在她顧婉盈的手上。
32.1萬字8 1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