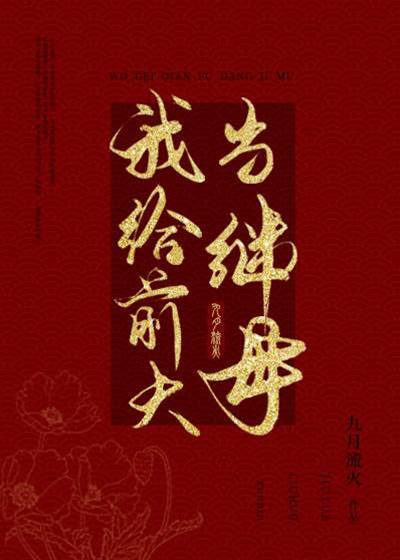《殊色誤人》 第58頁
可只是微微掙扎了一下手腕,掙不開,玉容頓時委屈下來,眼尾微紅,泫然泣道,"可這難道不是蕭郎君自己猜測的嗎?妾可從未說過,箱子里是亡夫。"
說著,另一只手解開未上鎖的鎖扣,將箱籠的木蓋打開。
一箱卷軼,就這麼突然出現在蕭緒桓眼前。
猝不及防,他甚至沒反應過來,目落到最上層的幾本書之上,上面赫然寫著《觀濤軒主人文集》《小幽山史編》等字樣。
“這兩箱文稿,皆是亡父的手稿和藏書,可不是什麼亡夫,”他怔愣片刻,才聽到耳邊之人小聲哀怨,“蕭郎君誤會了妾的心意,還說不會對妾怎樣呢——嘶……”
崔茵重新掙了一下他的手,冷吸一口涼氣。
蕭緒桓回過神來,立即松開手,卻為時已晚,他一開始并未用力攥的手,只是剛才失神間沒掌控好力道,在手腕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紅印。
他懊惱萬分,看著箱子里的書冊,驚詫不已,見崔茵幽怨地看著自己,頓時愧難當。
不過片刻,他便回味過來。
怪不得方才崔茵一定要不依不饒惹怒自己,原來是知道自己誤會所在,定要看自己的好戲。
卻也怪不了旁人,是他誤會在先,遷怒于。
正同賠不是,手臂卻被纏了上來,崔茵杏眸亮亮地著自己,好整以暇輕輕綻開了一個得逞的笑。
蕭緒桓覺得自己嗓間干,將方才想說的話咽了回去。
Advertisement
果不其然,下一瞬間,崔茵吐氣如蘭,鼻尖幾乎到他的下,聲音里帶著調笑的意味,將他曾經說給自己的話原封不送還回去。
“蕭郎君這是吃醋了。”
*
那兩箱書冊最終崔茵也不曾帶走,蕭緒桓忙了幾日,這日夜里重新趕制徐州城的城防圖紙。
抬眼,便看見燭下那兩口箱子擺在書架旁邊,箱子被打開,里面的書冊只剩寥寥幾本,剩余的被整齊放在書架原先空缺的一角,像是白日里有人來整理過的樣子。
他匆忙別開視線,看見這兩口箱子,就能想起那日自己的窘迫和失態。
懊惱又悔恨。
婁復已經從軍營領罰回來了,敲了敲書房的門,進來回稟。
“將軍,夫人白日里過來整理書架,問我可否在書房添一張書案,夫人說,想在這里抄錄整理典籍。”
蕭緒桓聞言,手中的筆頓了頓,“依的意思便好。”
婁復回稟完,想起還有件事,小心翼翼道,“還有一事——”
“是阿姐,又找你做什麼了?”蕭緒桓神淡淡的,仿佛并不意外。
婁復如實道,“郡主問小的這幾日為何被罰去軍營練,小的按照您說的,搪塞了過去,郡主敏銳,察覺到不對勁,雖沒有繼續問,卻又重新跟小的打探,確認夫人本家和夫家的姓氏名號。”
蕭緒桓笑了笑,“隨去吧。”
并不是他非要瞞著阿姐,而是崔茵的份與外人而言實在是個麻煩,李承璟的結發妻,崔家的郎,樣樣都是阿姐的忌諱。
Advertisement
就連最親近的阿姐都不可能接崔茵這樣的來歷,遑論沈汲程改之他們這些部下。
當初誰不曾被崔家趕盡殺絕死里逃生過。
崔茵何其無辜,但一時半會兒,無法跟人解釋,能瞞一時算一時,總要等崔茵與他有些進展了再說。
眼下,二人的關系應當是向好之態了。
他只等崔茵肯放下戒備,對他再信任幾分,肯自己坦白份,屆時,他也定然坦誠相待。
婁復疑,“將軍,夫人夫家的別院就在鐘山,萬一郡主查到了那里,該怎麼辦?”
蕭緒桓微微一笑,“不妨,這原本便都是假的。”
婁復以為自己聽錯了,假的?陳夫人的份是假的?那都是在騙大司馬不?
他瞪大了眼睛,卻見蕭緒桓沒有半分氣惱之意。
婁復不敢多問,告退出去,翻來覆去想了半日,忽然明白過來。
這麼說,大司馬一開始就知道夫人的份是假的,是在騙他,所以才如此從容?那這樣的話,他和郡主發出的同樣的那個疑也有了答案。
大司馬先前便認識夫人,并且夫人似乎不記得他了。
**
戌時剛到,崔茵坐在梳妝臺的銅鏡前,抿了抿涂好的口脂,起挽上披帛,輕盈地轉了個圈。
“春草,好看嗎?”
春草連連點頭,“娘子穿什麼都好看。”
想了想,用了一個十分切的詞語,“艷人!”
崔茵抿笑笑,出門,沿著長廊往前堂書房走去。
Advertisement
婁復來與說,書房里的書案已經安置好了,大司馬今晚在里面忙公務。
崔茵今晚雖心妝扮,卻只是規規矩矩地坐在一側的書案旁抄錄阿爹留下的卷軼,連一個眼神都不曾向旁邊的人。
蕭緒桓的余里,見垂眸,支腕認真謄抄,鬢間的珠釵偶爾折出璀璨的影,似乎沒有要同自己說話的樣子。
紙頁輕翻,靜的只有沙之音。
半個時辰過去,方見活了一下手腕,將筆擱在一旁。
蕭緒桓間微,忍不住先開口。
猜你喜歡
-
完結831 章

花顏策
太子云遲選妃,選中了林安花家最小的女兒花顏,消息一出,碎了京城無數女兒的芳心。傳言:太子三歲能詩,七歲能賦,十歲辯當世大儒,十二歲百步穿楊,十五歲司天下學子考績,十六歲監國攝政,文登峰,武造極,容姿傾世,豐儀無雙。花顏覺得,天上掉了好大一張餡餅,砸到了她的頭上。自此後,她要和全天下搶這個男人?--------
198.9萬字8 139249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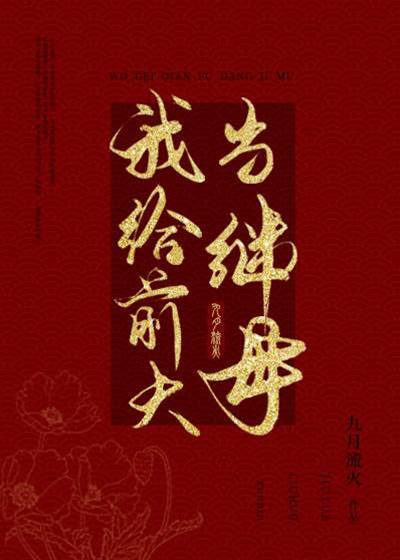
我給前夫當繼母
【微博:晉江九月流火】林未晞死了一次才知,自己只是一本庶女文中的女配,一個用來反襯女主如何溫柔體貼、如何會做妻子的炮灰原配。 男主是她的前夫,堂堂燕王世子,家世優越、光芒萬丈,而女主卻不是她。 女主是她的庶妹,那才是丈夫的白月光,硃砂痣,求不得。 直到林未晞死了,丈夫終於如願娶了庶妹。 她冷眼看著這兩人蜜裡調油,琴瑟和鳴,所有人都在用庶妹的成功來反襯她這個元妻的不妥當。 林未晞冷笑,好啊,既然你們的愛情感動天地,那我這個姐姐回來給你們做繼母吧! 於是,她負氣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前世未曾謀面的公公——大齊的守護戰神,喪妻后一直沒有續娶,擁兵一方、威名赫赫的燕王。 後來,正值壯年、殺伐果決的燕王看著比自己小了一輪還多的嬌妻,頗為頭疼。 罷了,她還小,他得寵著她,縱著她,教著她。 #我給女主當婆婆##被三后我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已開啟晉江防盜,訂閱比例不足70%,最新章需要暫緩幾天,望諒解】*************************************************預收文:《難消帝王恩》虞清嘉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女配文里的原女主。 呵呵……反正遲早都要死,不如活的舒心一點,虞清嘉徹底放飛自我,仗著自己是嫡女,玩了命刁難父親新領回的美艷小妾。 這個小妾也不是善茬,一來二去,兩人梁子越結越大。 後來她漸漸發現不對,她的死對頭為什麼是男人?他還是皇室通緝犯,廢太子的幼子,日後有名的暴君啊啊啊! ***本朝皇室有一樁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比如皇室男子雖然個個貌美善戰,但是卻帶著不可違抗的嗜血偏執基因。 慕容珩少年時從雲端摔入塵埃,甚至不得不男扮女裝,在隨臣後院里躲避密探。 經逢大變,他體內的暴虐分子幾乎控制不住,直到他看到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每日過來挑釁他,刁難他,甚至還用可笑的伎倆陷害他。 慕容珩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樂趣,可是總有一些討厭的,號稱「女配」 的蒼蠅來打擾他和嘉嘉獨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也沒有人可以奪走你,你獨屬於我。 他的嘉嘉小姐。 註:男主偏執佔有慾強,祖傳神經病,女主虞美人假小妾真皇子與作死的嫡女,點擊作者專欄,在預收文一欄就可以找到哦,求你們提前包養我!
36.9萬字8.36 64041 -
完結735 章

和離后,禁欲殘王每天都想破戒
前世,她用盡全力地去討好夫君和家人,可換來的卻是無盡的漠視和冷落。經歷一世凄苦的她最終慘死在信任的堂姐手里。重生后,花芊芊果斷與眼盲心瞎的丈夫和離,與相府斷絕關系。憑借前世的記憶和超高的醫術力挽狂瀾。斗婊虐渣,帶著疼愛她的外祖一家青雲直上。當發現前一世一直救她護她的人,竟然是她的“大表哥”時,她紅了眼,緊緊摟著那人不撒手。欲拒還迎的男人緊繃著唇角:“青天白日,成何體統!” 可他那冷情的眉眼,都已經彎成了月牙。聲音啞沉地道:“關門!”
133.5萬字8.07 1571050 -
完結199 章
寵妃升職記
面對選秀,安如意只是個小小的庶女,為了避開嫡母安排的親事, 做別人的小妾和做皇帝的小妾,她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 有個金手指空間做後盾,本來她只想到皇宮去養老的,可是後宮也不安全,每個人都能欺負她, 而皇帝的寵愛更是把她推到了風口浪尖,你們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讓你們好過。 等她鬥倒了所有的人,看著虎視眈眈的皇帝,她慫了,她不想再生孩子了,都一堆了。
33.9萬字8 110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