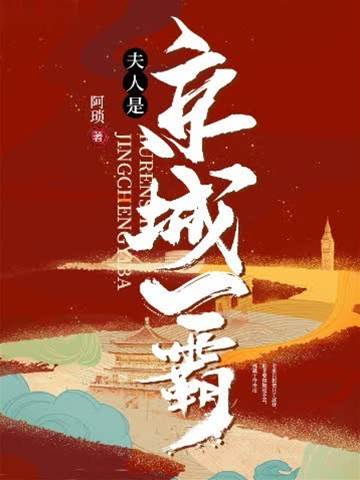《舊時燕飛帝王家》 第25頁
驍王聞言一挑眉,似笑非笑地看了飛燕白凈的面龐一眼,便不再言語。
武戲還沒有打完,皇后許是疲累了,便由太子陪伴著起先行回中宮休息了。眾人起恭送,飛燕留意到那皇后從始至終都未曾與霍尊霆說過話。
看來因著沈家的緣故,這沈皇后似乎著惱得不輕。皇后走后,那樂平立刻又是神qíng雀躍了不,在侍的攙扶下,竟是起去了后臺要去打賞戲子。
驍王也準備帶了飛燕出宮,走到了了戲園子的門口時,飛燕低頭走在驍王的后,無意中瞥見在院子路旁的花壇里,靜躺著一朵蘿卜花兒,這花兒倒是與其他眷冰碗里的一般模樣,似乎是被人匆匆替換下來……
“怎麼了?”這時驍王轉問道。
飛燕定了定神,說道:“沒有什麼……”
公主納禮后的第五天,便是王家正式迎親的日子。
驍王自然是要去參加禮。可是飛燕若去便是不大好看了,畢竟那王家也曾與有過婚約,去了反而是不自在。
借著這個機會,便離了王府,回轉了叔伯的家中。飛燕回轉了府里,發現叔伯不在,說是去尋訪舊友去了。
近日賢哥兒很是刻苦,書院的先生也是大力盛贊,囑咐他準備著來年的恩科開考,見堂姐回來,寒暄了一會,便說要回書房用功去了。與敬在閨房里說了子話,便想去看看正在書房里用功的敬賢。
還沒走到書房門口時,飛燕順著那書房的窗戶往里了進去,發現敬賢正在聚jīng會神地看著一封書信。當飛燕含笑推門而的時候,那賢哥兒嚇得渾一抖,快速地將書信夾放進了一本《詩經》之中。
飛燕倒是不以為意,只當是這小兒qíng竇初開,認識了哪家的小姐,暗中書信傳qíng。便是只當沒看見,問起了敬賢的功課來。
Advertisement
可是那敬賢竟是個存不住事兒的,見堂姐遲遲不肯出去,便是有些焦躁,對答起來竟是有些驢不對馬。
飛燕原想著等到恰當的時候,再變著法兒的提醒下敬賢,男兒當先立業再思家,現在看來,竟是孽緣深陷的模樣。叔伯向來心,可千萬別任著小兒癡qíng,敗壞了別家姑娘的名聲,犯下了有rǔ門楣的事qíng來。
想到這,便說道:“說得有些口燥,賢哥兒,去給姐姐倒一杯熱茶。”
敬賢不疑有詐,便起去了旁邊的桌前倒水。飛燕趁這個機會指捻起那張書信一看,當信紙上的字跡映眼簾,登時臉為之一變。
這書信上的字竟然是與前幾日收到的如出一轍!都是出自那人的手筆。
敬賢回時發現堂姐看到了自己藏的書信,登時也是臉一變,手中的茶水潑灑了不。
飛燕逐行逐句地看了手里的那張信紙,便慢慢抬頭看向自己的堂弟。
“你什麼時候跟他聯系上的?當真是不顧自己一家的死活了嗎?”
尉遲敬賢見堂姐發現了,索xing不再瞞,理直氣壯地說道:“樊將軍乃是二叔的舊部,有名的抗齊名將,當得上男兒錚錚傲骨,如今他在北方就霸業,卻念念不忘二叔家眷的安泰,聽聞了你要被迫嫁與那大齊的狗皇子為妾,樊將軍才托人輾轉給了我一封書信,要我們一家老小做好準備,待得時機,便接我們一家離京去呢!”
飛燕只覺得執著信的指尖都是微微發涼,低聲音道:“這書信還有誰見了?”
敬賢也是被堂姐異常嚴肅的臉有些驚嚇到,可又覺得自己做得無錯,便qiáng自賭氣說:“爹爹素來膽小,我也是怕他嚇得失了分寸,并未曾給他瞧見。”
Advertisement
尉遲飛燕這才緩了口氣,沉聲說道:“如今圣上并未因著我家乃是前梁武將之家而薄待,姐姐也不是被迫嫁與那二皇子……他……為人謙良,也算是良配。我們何苦要跟那北方的叛軍攪合到一……”
尉遲敬賢真是打死也沒有想到堂姐竟是這樣詆毀他一心敬仰的樊景將軍,當真是倒吸了一口冷氣,說話的語氣登時有可些年的刻薄。
“堂姐,莫不是真如樊將軍在信里所言,因著你以前在二叔軍營里與他相時,他曾允諾要娶你為妻,只因為他為了復興大梁,娶了通古族長的兒,你便因為這兒私qíng怨尤了他?”
飛燕抿著,瞪著自己的堂弟,而那敬賢便只當是堂姐默認,接著憤憤然道:“若真是這樣,這樊景的確是可恨,竟是辜負了堂姐,可是大義應在兒私qíng之前,就算樊將軍是個負心人,但堂姐也不該賭氣嫁給那大齊的皇子,不然二叔泉下有知,豈會瞑目?”
尉遲飛燕略顯疲憊地向自己的堂弟,心知如今他已經長年,自有自己的一番想法,倒不像小時那般天真,若是聽聞有人欺負了姐姐,管他是誰,都要揮舞著小拳頭上去一頓捶打。堂弟誤會自己因著小兒的qíng傷,而拒樊將軍的好意于千里。只是自己去了白山的那幾年,到底都是說不得的。
他倒是口才漸有長進,竟是把這番小時無猜說得是天無fèng。
“敬賢,你也漸大了,有些話,姐姐也是可以說與你聽的了,世人都道大梁將軍尉遲瑞戰死在沙場,可是有誰知道,我的父親在那戰場上,是背后中箭而亡……”
尉遲敬賢從來未曾聽聞過,當年二叔的靈柩回京,俱已經是穿戴了整齊的,他那時還小,自然也沒有人告訴過他關于二叔傷口的事qíng。只是堂姐如今這般的提起,倒像是有qíng一般……
Advertisement
“彼時父親在高昌死守,孤軍戰抵齊軍。那時大齊的兵馬已經拿下江山過半,岌岌可危,先帝便萌生了議和的心思,想要與齊軍劃江而治。可父親當日死守高昌,齊軍折損無數,前去議和的大臣也被齊軍扣押,加上佞臣讒言,那大梁的皇帝竟是一連數道圣旨,急召父親歸京,可是父親死守數月,一旦撤兵,齊軍乘勝追擊,勢必要折損大半的將士,便是違抗圣命,一意待得齊軍撤退。
那皇帝竟是惱了,下了道圣旨,收買了父親的一個手下,趁著與齊軍對陣之際,從背后……向父親she了冷箭……”
尉遲敬賢以前從來未曾聽過二叔的離世竟是這般qíng,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氣,他一向以自己乃前梁忠良后代而自傲,現在竟是如五雷轟頂一般,不知所措。
“那……那后來為何沒有聽聞了先帝與齊軍議和的消息?”他依然不信,頑qiáng地找著姐姐話語里的dòng。
飛燕苦笑著說:“因著這霍家人俱是有些潑皮無賴,家父乃是大梁軍隊的脊梁,他若沒了,霍允豈會甘心平白了半壁江山,與那蠢不可及的梁帝劃江而治?所以父親事后,便是一路勢如破竹,沒有多久便京城淪陷了……”
飛燕看著堂弟震驚的模樣,竟是一如自己在一年前聽聞真相時彷徨無措,便是慢慢地將心里的郁氣呼出,接著道:“爹爹生前,曾經跟我講起那紙上談兵趙括的悲劇,怎知父親竟是也落得如此下場,戰場用兵有律可依;朝堂狡詐、人心愚鈍竟是無法可循……所以,堂姐也是疲累了,如今大齊政局康定,百姓安居樂業,哪個平頭的百姓想要那前梁再重新復辟?敬賢,你如此推崇那樊景,究竟是一心為民想要山河平定,百姓安康,還是想要重新恢復前梁,以待重現尉遲家昔日的輝煌?”
Advertisement
敬賢到底是個聰明的孩子,被堂姐這麼一問,子一震,便久不再言語,過了一會才遲疑地說:“堂姐,難道是那樊景she了我二叔?”
尉遲飛燕搖了搖頭,似乎不想再提及往事:“他倒沒有那般的卑劣,只是他野心甚大,豈是北方一隅之地所能滿足的?堂姐只希你用心讀書,將來憑借自己的實學為,踏踏實實地為民做些實事,這才是復我尉遲家的正經途徑。千萬莫存了投機的心思,年熱便生出了禍及家人的心思……你是將來尉遲家的門面,一步都是錯不得的。”
一時間,姐弟二人又長聊了一陣子。敬賢向堂姐保證,以后再有這樣的書信要當著送信之人的面撕得碎,絕不與他們沾染后,才起出了書房。
此時天漸漸昏暗,似乎不久會下一場bào雨,口氣悶得有些不過來。回頭掩門的時候,看見堂弟依然愣愣地坐在桌旁,便是又深深嘆了口氣。
執著了許久的信念,一朝坍塌的滋味的確是難得很,那時應該也是如堂弟這般。姓埋名,白山落糙為寇,一心念及的大梁復,竟是如此蠢不可及!
一心以為此生的良人另娶,父親的死原來另有qíng,苦心煎熬的崢嶸歲月俱了水中打撈不起的殘月鏡花水影……
那時的,真是有種萬念俱灰之……不過,幸好還有叔伯一家,回京的這段日子,竟是在父親亡故后,最快樂的一段時。
自己這剩下的唯一的親人們,應該和泰安康地度過一生,誰也不能攪這已經平靜的一池湖水!
回到自己的閨房里,也不點燈,便是默默地坐在了黑暗中許久。不多時,外面下起了瓢潑大雨。
不會那寶珠撐著傘來到門口,興沖沖地喊著:“小姐,二殿下來了,帶了食盒加菜,要在府里留下用晚餐!”
第26章
外面的雨下得甚大,隆隆的雷聲里時不時的打閃。
霍尊霆居然冒著大雨前來尉遲府上食飯,著實出乎了飛燕的意料。當站在屋檐下時,看見他并沒撐傘,反而上披掛著一件蓑,戴著小沿的斗笠,因著材高大倒是不顯得臃腫,像是江邊剛剛打魚歸來的模樣。
事實的確是如此,原以為他拿來的食盒是在趙府打包的喜宴,可是侍們展開了食盒才發現里面俱是些生ròu碟子,還有一些時鮮的瓜果圍碟一類,一個小廝拎著兩個大大的魚簍進了廚房,讓尉遲府上的廚子把里面的活魚料理妥帖了。
“今日大雨,城郊錦湖的閘口鯰魚都冒了頭,一網下去打撈了不,正好借著雨天燒烤來吃。”驍王解下了蓑,笑著對飛燕說道。
這當哥哥的怎麼喜酒還吃到了錦湖那?飛燕有些不解,便是出言問道。
驍王半垂著眼兒說:“過了禮后,借著酒醉便走了,我素來不喜熱熱鬧,倒不如去湖邊躲下清凈。”
飛燕直覺這婚禮上應該是有些事qíng,可是他不說,也懶得問。下意識地從侍的手里接過了巾帕呈給坐在椅子上的驍王拭下俊臉上的雨痕。
若是平日,這小妮子絕不會這般的恭謙,驍王注意到有些懨懨的,似乎有些心事。不心道:莫不是因為那無緣的未婚夫婿了禮,因而倦怠了jīng神?
猜你喜歡
-
完結45 章

繁花落盡暮白首
仙霧之下,九州之上。她身為九天神女,一血誅盡天下妖魔,一骨盪盡九州魑魅。但她身為天妃,卻被自己愛了千年的男人一休二棄三廢,直至魂消魄散。「帝旌,如有來生,願不識君……」
4.6萬字8 7157 -
完結572 章
回眸醫笑:逆天毒妃惹不起
她,二十一世紀頂級醫學女特工,一朝重生,卻成了大將軍府未婚先孕的廢物大小姐。渣爹不愛?渣姐陷害?沒關係,打到你們服為止!從此廢物變天才,絕世靈藥在手,逆天靈器隨身,還有個禦萬獸的萌娃相伴,風華絕代,震懾九荒,誰敢再欺她?可偏偏有人不怕死,還敢湊上來:「拐了本王的種,你還想跑哪裡去?」納尼?感情當年睡了她的就是他?某王爺十分無恥的將人帶上塌:「好事成雙,今夜我們再生個女兒給小白作伴。」
98.1萬字8.18 45505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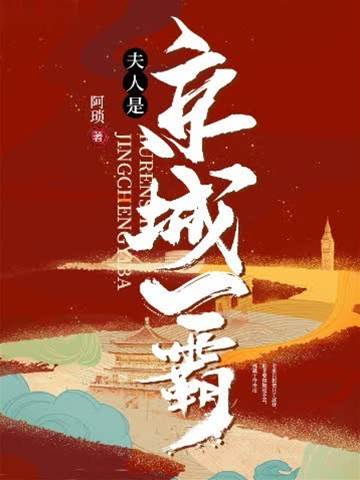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209 章

云鬢楚腰
陸則矜傲清貴,芝蘭玉樹,是全京城所有高門視作貴婿,卻又都鎩羽而歸的存在。父親是手握重兵的衛國公,母親是先帝唯一的嫡公主,舅舅是當今圣上,尚在襁褓中,便被立為世子。這樣的陸則,世間任何人或物,于他而言,都是唾手可得,但卻可有可無的。直到國公府…
68.7萬字8 26115 -
完結698 章

神醫娘親她特會講理
她來自中醫世家,穿越在成親夜,次日就被他丟去深山老林。四年里她生下孩子,成了江南首富,神秘神醫。四年里他出征在外,聲名鵲起,卻帶回一個女子。四年后,他讓人送她一張和離書。“和離書給她,讓她不用回來了。”不想她攜子歸來,找他分家產。他說:“讓出正妃之位,看在孩子的份上不和離。”“不稀罕,我只要家產”“我不立側妃不納妾。”她說:“和離吧,記得多分我家產”他大怒:“你閉嘴,我們之間只有死離,沒有和離。”
121.9萬字8 162108 -
完結184 章

紅酥手
蕭蔚看着爬到自己懷裏的女子無動於衷:餘姑娘,在下今晚還有公文要審,恐不能與你洞房了。 餘嫺抿了抿嘴脣:那明晚? 蕭蔚正襟危坐:明晚也審。 餘嫺歪頭:後夜呢? 蕭蔚:也要審。 餘嫺:再後夜? 蕭蔚:都要審。 餘嫺:我明白了。 蕭蔚:嗯……抱歉。 餘嫺笑吟吟:沒事。 蕭蔚疑惑:嗯? 餘嫺垂眸小聲道:白天? 蕭蔚:?(這姑娘腦子不好? 爲利益娶妻的腹黑純情男x爲真愛下嫁的天真軟萌妹 簡述版: 男主:對女主毫無愛意卻爲利益故作情深,作着作着走心了 女主:對男主頗有好感卻因人設假裝矜持,裝着裝着上癮了
29.2萬字8.18 42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