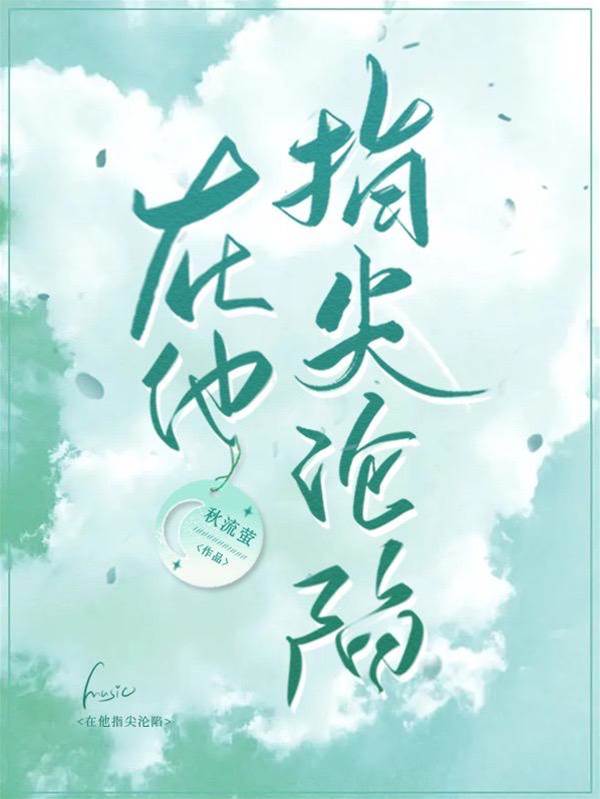《梟寵成癮:病嬌少帥的嬌妻是大佬》 第77章 多管閑事
席蘭廷言語很慢。
哪怕夫妻那等親關係,說話也要注意分寸,更何況他和雲喬什麽也不是,僅僅是席氏大園子裏兩個作伴的年輕男。
他有什麽資格,對的生活指手畫腳?
他說過,不喜去國外求學,可轉頭還是替尋了個英文老師,隻因想。
這才是紳士。
席蘭廷刻薄慣了,裝紳士需得用力。若在不經意間,他就要出他的小心思,不怎麽講理。
雲喬聽了,卻不怒。
不怒。
對方還是七叔,對很好的七叔,更不值得怒。
“我外婆是這樣,誰拜碼頭,瞧著有可取之,就會同意。庇護這些人,教他們規矩,也給他們好,指他們一條明路。”雲喬道,“但是我不同,我隻會接納自己選擇的門徒。”
Advertisement
比如說羅筠生,他六歲被賣到戲班,打小嗓子就出,將來肯定有一碗飯吃。
然而他時運不濟,戲班老板總是出事,他自己單獨幹過,也跟其他戲班搭夥,但總壁。
唱了十五年,二十出頭,最好年華快要過去了,他還是籍籍無名。
有人指點他,讓他去見蕭婆婆。不過,見蕭婆婆,需要有人引薦,還需要蕭婆婆那邊同意了,才能登門。
一年之後,二十二歲的羅筠生終於見到了蕭婆婆。
他上自己生辰八字,主認作門徒,跪拜蕭婆婆。
蕭婆婆指點他:“離開北平,去燕城。城西有家戲園子,老板,甭管什麽份,也別管什麽條件,你去唱就是了。”
他果然來了。
的確有個老板,長得不好看,穿短靴馬、剃著比男人還短的頭發。為人非常苛刻,擅長刁難人,比一般男人都心狠,極其難相。
Advertisement
這戲園子,合作過的戲班都走了,慢慢落寞。
落寞而已,混口飯吃還不問題。
羅筠生主來了。
時來運轉,他短短半年紅遍了燕城。北平、上海那些響當當的權貴,親自驅車到燕城,隻為聽他一曲。
老板還是很苛刻,但戲班願意傍上羅筠生,故而很不人來搭戲,分一杯羹。
羅筠生和老板慢慢相,發現這個人規矩極嚴。
說早上五點吃飯,你起來吃,就會高興。而一口吐沫一個釘,說五點就五點,風雨不改。
了門路,和相並不算難。
給錢大方;應付權貴有一套;會打罵戲班的人,但打罵都有道理,隻是自己不說。WwW.com
羅筠生這兩年紅極一時。
雲喬卻不會接這樣的門徒。
Advertisement
會以醫為主,就像薑燕瑾的妹妹,求到了跟前,而想要救。
“……七叔,外婆的餘威,總有散盡那一天。到時候,我拿著舊時分去求人,不可笑嗎?”雲喬又道。
席蘭廷聽罷,微微笑起來。
他端起茶喝了口,神淺淡:“是我多管閑事了。”
他不肯再談。
一晚上,兩人都在聽戲,沒有再開口說話。
周日晚上,雲喬待四房眾人吃晚飯的時候,回去了。
幾個人都停箸看著。
雲喬恍若不覺,簡單了聲媽,就快步上樓去了。
。您提供大神明藥的梟寵癮:病帥的妻是大佬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無法抗拒的他
蘇雲被綠了,怒甩渣男。 將真心收回后再不肯輕易給人。 戀愛麼,何必那麼認真。 何勉偏要蘇雲的心,徐徐圖之。 何勉:「要不要和我談戀愛,不用負責的那種」 蘇云:「……好」 後來。 何勉:「你不對我負責沒關係,我對你負責就行」 蘇云:「為什麼是我?我有過去的」 配不上你。 何勉:「沒事,誰都有瞎的時候,我不怪你」
3.6萬字8 847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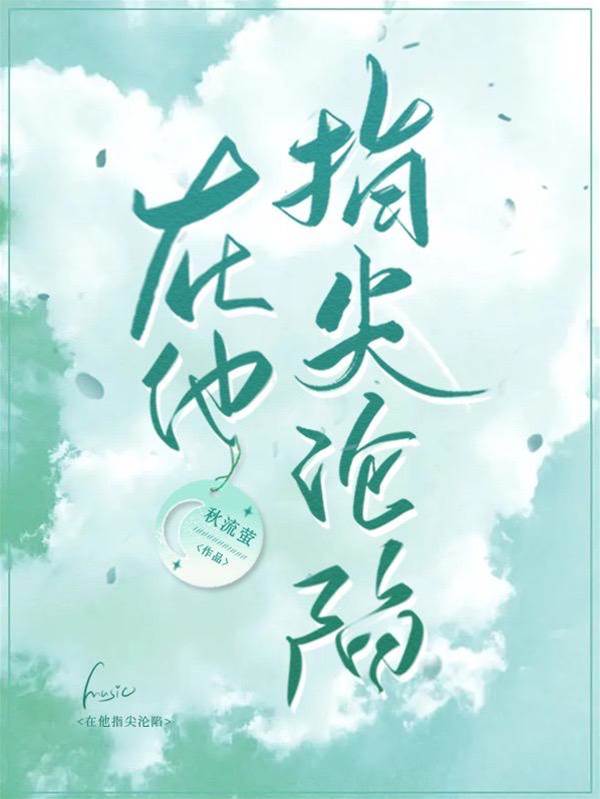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18 22009 -
完結959 章

王妃帶崽重生,九王叔被娃怒取狗命顧南喬墨子謙
【1V1+雙強+萌寶+雙向奔赴+重生爽文】毒醫雙絕的軍醫顧南喬重生了兩世,第一世穿越因識人不清而落得凄慘而死,再次重生歸來,她勢要顛覆這渣男江山。可有一日,兩只
86.3萬字8.18 11218 -
完結112 章

炙吻
今年18歲的許芳菲,父親早逝,家中只一個母親一個外公,一家三口住喜旺街9號。 喜旺街徒有其名,是凌城出了名的貧民窟。 許母開了個紙錢鋪養活一家,許芳菲白天上學,晚上回家幫母親的忙。 日子清貧安穩,無波無瀾。 後來,樓下搬來了一個年輕人,高大英俊,眉目間有一種凌厲的冷漠不羈和刺骨荒寒。男人經常早出晚歸,一身傷。 故事在這天開始。 * 又一次相見,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雄鷹掠過碧藍蒼穹,掠過皚皚白雪。 許芳菲軍校畢業,受命進入無人區,爲正執行絕密行動的狼牙特種部隊提供技術支援。 來接她的是此次行動的最高指揮官。 對方一身筆挺如畫的軍裝,冷峻面容在漫山大雪的映襯下,顯出幾分凜冽的散漫。 看他僅一眼,許芳菲便耳根泛紅,悶悶地別過頭去。 同行同事見狀好奇:“你和鄭隊以前認識?” 許芳菲心慌意亂,腦袋搖成撥浪鼓,支吾:“不。不太熟。” 當晚,她抱着牙刷臉盆去洗漱。 走出營房沒兩步,讓人一把拽過來給摁牆上。 四周黑乎乎一片,許芳菲心跳如雷。 “不熟?”低沉嗓音在耳畔響起,輕描淡寫兩個字,聽不出喜怒。 “……” “你十八歲那會兒我執行任務,拼死拼活拿命護着你,你上軍校之後我當你教導員,手把手教你拼組槍支,肉貼肉教你打靶格鬥,上個月我走之前吊我脖子上撒嬌賣萌不肯撒手。不太熟?“ “……” 鄭西野涼薄又自嘲地勾起脣,盯着她緋紅嬌俏的小臉,咬着牙擠出最後一句:“小崽子,可以啊。長大了,翅膀硬了。吵個架連老公都不認了。” 許芳菲:“……”
61.9萬字8 1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