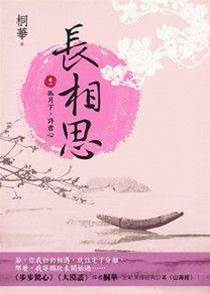《御前新賜紫羅裙》 第123頁
七爺因為擔心陸史的安危,為了盡快找到,除了明面報人員和探,將他與四爺埋的暗線也用了。
四爺疾之后。七爺在明面上,四爺轉為暗,說是閑賦在家,但實際卻在培養一批暗士,這些人輕易是不會,因為,霍家兩兄弟始終提前準備著霍家的退路問題。若是有一天,一旦天變,這些安在各路的死士,便是最后接應的底牌,不能暴。這些人暗中培養起來,不蛛馬跡,但這回為了尋找陸史,卻是連他們也用。
霍寧珘開口道:“發現陸史的時候,就與那商隊的人在一起?”
藺深頷首:“是的,七爺。”
“商隊……”霍寧珘道:“真的是商隊?”
藺深道:“目前查到的,確是如此,這商隊過去便曾經過數城,都是守城軍士驗過份的,且隊里都是臉孔,所有蹤跡都有跡可循,做的也的確是正經生意。這次與陸史在一起的,都是商隊中的臉孔。”
“但……”藺深微頓:“陸史怎麼和他們湊到一起,還得晚些問本人。”
“那個男人又是誰?”霍寧珘看著陸蒔蘭與那男子相時稔,放松的神態。所以……這不算擄,陸蒔蘭自己也本沒有逃跑和反抗之舉。
陸蒔蘭做了員以后,在場表現得十分謹肅端凝,在這個男人面前,倒是玩心未褪的樣子,像個小年。說明兩人相識于年,份也沒有高低之分,私的確很好。
Advertisement
“正是陸史的師兄,裴夙,曾在國子監求學。”藺深趕道:“這師兄也是被發現時,就與陸史在一起。”
霍寧珘聞言,沉默下來。
·
裴夙那邊則道:“師弟,我們再去街上逛一逛,然后回客棧可好?”
陸蒔蘭答:“好。”畢竟在南京待過那樣多年,是有的,故地重游,也良多。便道:“要不,去先前哥哥猜燈謎的地方,繼續罷?”
“好。”裴夙知道,陸蒔蘭還放不下陸槿若。
因為要上臺,周圍看熱鬧的人太多,裴夙便給陸蒔蘭戴了一張白繪紫蘭的面,自己也戴了一面白繪蘭草的,才跟著上臺去。
這家花燈老板的燈謎不知去哪里收集的,很是有巧思,陸蒔蘭這一猜,就猜上了癮。那老板著汗,這個看起來文質纖弱的小公子是要將獎品全部贏走?那他今晚就虧大了!
裴夙角略含笑意,突然,神微斂,側首看向人群中的一個方向。
是一個形出眾的男人。那男子慢慢上了臺階,黑繡角的擺隨著他的步伐曳,不不慢,走路的姿勢十分沉穩。卻是戴著一張惡煞面,徑直朝著裴夙與陸蒔蘭站著的地方走來。
那老板咬著牙看向陸蒔蘭,繼續取了下一盞燈,他已經拿出箱底的難題了,這人還在猜,到底要猜到什麼時候!
陸蒔蘭饒有興致要繼續猜下一道謎題,一道略低的嗓音竟然在之前就答了出來。
Advertisement
這聲音……全僵滯,腦中有一瞬空白。隨即不敢置信,轉過頭來上下看看這面男子的型,那峻自若的站姿,還有墨如錦的頭發,甚至是那悉的迫,卻不得不信。
怔怔看著面前出現的男子,了,無聲地道:“首輔……”
霍寧珘那雙眼睛朝看來的時候,能勾魂攝魄一般,陸蒔蘭愈加確信無疑。
不過,他只看了陸蒔蘭片刻,便將目投向后不遠的裴夙。
看著陸蒔蘭這反應,裴夙頓時明白了,這男人是誰,也明白了先前到的危險因何而來。雖然,他從前并未與霍寧珘打過照面,只是看過畫像。
裴夙自然知道東津衛天翻地覆地在找陸蒔蘭,只是他沒有告訴陸蒔蘭而已。直到看到霍寧珘這樣快親自出現,他這才知道,他和陸槿若,之前都低估了霍寧珘對陸蒔蘭的重視程度。
他的目也轉向霍寧珘,視線匯。兩個人都是心思叵測,深如淵海。
旁邊的那花燈老板見陸蒔蘭獨霸燈謎臺這樣久,終于被人搶答了,一臉喜氣洋洋地朝陸蒔蘭出送客的表。
陸蒔蘭現下哪里還顧得上那老板,再說猜燈謎就是為了應景好玩,本來就沒打算要這老板太多獎品,只想要那一盞讓想起阿眸的小貓燈意思一下。不過,現在,卻是連那小貓燈也忘記,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首輔來了。
但現在看熱鬧的人這樣多,首輔既然戴著面,說明不想以真實份示人,陸蒔蘭也沒有貿然上前行禮。
Advertisement
倒是裴夙還記得陸蒔蘭先前說想要那盞小貓燈,幫拎上了,說:“師弟,既然有人接上燈謎,我們便回去罷。”
陸蒔蘭躊躇片刻,覺得不好看到首輔來了就走,而且,無論從公務上,還是私人突然失蹤這件事,都有必要給霍寧珘匯報一下。盡管首輔看起來……現在不宜招惹。
陸蒔蘭又想了想,憶起這位首輔是很善于清算舊賬的,便決定主一些,低聲道:“師兄,我似乎看到了認識的人,我要先與他說幾句話,你能不能等等我?”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殺手皇妃很囂張
她是二十一世紀令人聞風喪膽的冷血殺手,從未有過任何一次失手,不斷問的自己,她活著就是爲了殺人嗎?被組織遺棄,穿越成嬰兒,這一次她要好好的活著。當冷血殺手遇上腹黑皇子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滅我家園?很好,那我就滅你國家得了,你說我沒有那個本事?那就等著瞧吧!皇宮之中,危機處處有,人人都非等閒之輩,可她偏要攪個天翻
60.8萬字8.08 29639 -
完結1816 章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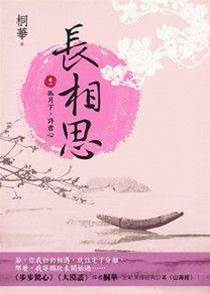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253 章

重生後,病弱世子總想讓我衝喜
白曦薇嫁給九王爺後助她登位,鏟除餘孽,封後時,那個男人毫不猶豫的賜死了她,白家滿門抄斬!一朝重生,白曦薇隻想保住白家,弄死渣男,不曾想一紙婚約,白曦薇和京城裏人人都知道隨時會死的容遲扯上了關係。衝喜?上輩子容遲十八歲就病死了,這輩子……他十七了!白曦薇天天忙著解除婚約,容遲天天忙著培養感情。白曦薇抓狂作者:“容世子,我們不合適!”“合不合的,試試就知道了!”“容遲,你自己走行不行?!”“爺是嬌花,容易碎。”“……”兩世為人,一世傾盡所有卻遭背叛,一世心如磐石卻被一個病秧子攪動了春水。白曦薇扶著腰,氣的直哼哼。什麽病秧子,都是假的!黑心黑肺的混蛋。
44.4萬字8.18 62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