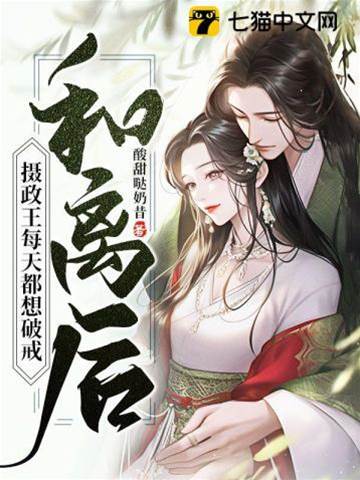《神醫魔后》 第112章 師離淵你自己品
夜溫言走了,就像來時一樣,悄無聲息地又從將軍府離開。
雖然已經知道臘月十五的伏殺是夜飛舟做的,卻終究是沒有對他做些什麼。
也不知是因為夜飛舟那副中帶的樣貌讓下不去手,還是因為許多年前原主送去的那一包糖果,了心底最的一塊地方。
前世今生,夜溫言從來都不是什麼圣母,從來都沒有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傷害過的人。
可卻在剛剛那一刻,聽著夜飛舟說過那些話,就特別想要放他一馬。
那位二哥是疼過原主的,原主心里也是真正把他當哥哥的。只可惜造化弄人,夜家大房二房經了這麼多年,最終竟是走到了這一步。
放過了夜飛舟,卻也得給心里頭這口惡氣找個宣泄口。
于是在返回炎華宮的路上,順手將仁王府的府墻弄塌了一片。
仁王殿下,先帝的第三個兒子,今年二十七歲,封號為仁,卻是假仁假義的仁。
寂靜的夜里,臨安城晚睡的人們都聽到轟隆一聲巨響,睡著了的人也在這樣的巨響中坐起來一半。人們睡眼朦朧,誰也不知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如何鬧出這麼大的聲響來。
臨安府尹池弘方也被這一聲巨響驚著了,騰地一下就從榻上坐了起來。池夫人催促他:“快去看看吧,別是哪里又出了什麼事。”
他趕披了外袍往外走,同時大聲吩咐差外出探查。
探查的差很快就有回報,說是三皇子府的圍墻突然就塌了。
池弘方納悶:“怎麼塌的?這大半夜的為何圍墻說塌就塌?”
差搖頭,“完全沒有征兆,一下子就塌了一片,連仁王府守門的侍衛都納悶呢!”差再想想,分析說,“可能是年久失修吧?”
Advertisement
“屁個年久失修!”池弘方鼻子差點兒沒氣歪了,“去年才新修的!”
差咧咧,小聲說:“反正就邪門的,我瞅著跟肅王府塌的那是一模一樣,連府墻帶府門都一起壞了。”
池弘方琢磨了一會兒,呵呵笑了起來,轉就往回走:“睡覺!今夜無事,臨安城四面太平,什麼意外的事都沒有發生過。”
差著急:“那明兒三殿下要是問起來呢?”
“問起來也是四面太平!他自己的府墻修的不結實,跟本府說得著麼!”
臨安府尹哼著小曲兒回后宅睡覺去了。
夜溫言回到炎華宮時,師離淵還在大殿里等。見回來立即就問:“怎麼樣?”
夜溫言攤攤手,“就那樣唄!”
“就那樣是怎麼樣?聽出了什麼名堂麼?”
點頭,“聽出了,所以我拆了三殿下的府墻,明兒還準備把他睡覺的屋子也拆一拆。”
師離淵說:“用不著等明兒,本尊現在就給你拆。”
“別呀!”趕把人攔住,“可著一天禍害多沒意思,那得天天拆,拆著拆著他就習慣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不拆了,他保準睡不著覺。”
他聽著這話就琢磨了開,半晌問道:“你這一肚子壞水兒是跟誰學的?”
“我壞嗎?”眨眨眼,“我不壞,我這人從來不搞謀,我都是來的。間人辦間事,繞七繞八的沒意思,要干架就直來直去的干,那才過癮。”
“那你為何不干脆找那三殿下打一架?”
“我怕把他給打死了。”實話實說,“直接手很容易手底下沒個輕重,萬一把人給打死了多無趣?”
他問出一個關鍵:“三殿下為何要與你為難?夜四小姐跟他也有仇?”
Advertisement
“可能是有吧!”開始胡扯,“你想啊!夜四小姐是魔,又是臨安第一人,興許就是從前三殿下而不得,自此就因生恨,得不到我就要毀了我。”
他手去的耳朵,“夜溫言,你給本尊說實話。”
“疼!”輕呼一聲,其實不疼,他卻信了的話,趕把手松開,還一下一下在過的地方輕輕著。笑瞇瞇地同他說,“其實也沒多復雜個事兒,就是三殿下同我那二哥關系比較好,然后夜紅妝給我二哥去信,讓他殺了我。我二哥手底下又沒什麼人,于是借了三殿下的暗衛。我如今雖然住在炎華宮,但總不能在這里住一輩子,將軍府還是得回去的。所以我不能拆了自己的家,那就去拆三殿下的家吧!”
“如何就不能住一輩子?”帝尊大人很不開心,“你要是不喜歡這里,咱們就住到別去,你指哪,咱們就在哪再蓋一座宮殿。你若不喜歡太大的宮殿,咱們就蓋小房子小屋子。總之只要你喜歡,這普天之下是哪里都可以住的。還有——”
他話鋒一轉,不打算就這麼將放過,“不拆將軍府,你可以收拾你那二哥。如今又不是十五之日,你靈力在,兜里又揣著那麼多花瓣,收拾一個凡人還不是易如反掌?怎的就偏得拐個彎兒去找三殿下?”
小姑娘撅著,半天沒出聲兒。他看出來了:“下不去手?”
點點頭,實話實說:“是有點兒。因為我在將軍府聽到他跟我二叔說話,說的盡是從前的事。于是就想起來我時曾托鏢師給他帶過糖果,也想起來他學武歸來時,給家里每一個人都帶回了外省的禮,其中還特地多給了我一份,盡是臨安城吃不到的好吃的。”
Advertisement
“所以就放過了他?”師離淵搖頭,“夜溫言,那不是你給他的糖果,他帶回來的好吃的給的也不是你。那些事是從前的夜四小姐做的,并非是你。”
“可他要殺的也是夜四小姐啊!也不是沖著我啊!”笑笑,挽上他的手臂,“我說過,既然用了這個,就得承著夜四小姐的因果,所以沒有辦法把我和分得那樣清楚。何況我也不是真的就打算把這口氣咽下去,這不是去仁王府出氣去了麼!當然,這種事也就僅只一次,下回他若再與我為難,我就斷不會再手了。師離淵,就當我有一次人味兒吧!”
“你一直都很有人味的。”他心里對這姑娘疼惜得,輕輕拍了拍挽過來的小手,“都依著你就是。只是你一定要記得,若再有下次,即使你放過他,本尊也是不會答應的。”
“好,就這一回!”笑著搖他的胳膊,搖著搖著就又問道:“你說我什麼時候回府好?”
“恩?”他一愣,“不是說好了要住到大年嗎?還早著呢,問這個作甚?”
“也沒多日子了,總得打算打算。”
他不想打算,“本尊今晚困了,這事改日再議。”說著就拖著人要往臥寢走。
不干了,“你困什麼?你又不用睡覺,打個坐不就行了嗎?你就一邊打坐一邊同我說話,咱倆把我回府的事好好合計合計。”
他卻搖頭,“本尊偶爾也是要睡覺的。就像你說的,總得沾些人間煙火。走吧!”
他拖著就走,夜溫言不樂意:“真的不幫我打算打算?師離淵,你是兒就沒想過要替我打算吧?就想一直把我留在炎華宮,對不對?”
“對啊!”他實話實說,說完又緒落寞,“但是你能留麼?”
Advertisement
搖頭,“不能。”
“所以就要珍惜眼前的日子。睡覺!”他將人往懷里一帶,直接用了挪移,下一刻兩人已經坐在臥寢的床榻上了。
小姑娘瞅了瞅眼前這位帝尊大人,恩,帝尊大人正在鋪被子,還把外袍了,又把鞋子了,然后帝尊大人鉆進了被子里,沖著出手。
不解,“你要干啥?”
“睡覺啊!”他答得理所當然。
“睡覺你拉著我干什麼?”
“不拉你本尊還能拉誰?何況這些日子你不是一直睡在這里?怎的今日不睡了?”
“可是這些日子你都沒睡啊!”有點兒崩潰,“這些日子你都是坐著的啊!”
“有什麼區別嗎?本尊就算不睡,也是坐在這榻上守著你,你每晚都抱著我的胳膊和手,那我坐著和躺著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隔著被子踹了他一腳,“坐著就守,躺著就耍流氓!你自己品!”
帝尊大人品不出來,但挨了一腳之后也實在躺不下去了,認命地起了,整理好著,然后把被子往里挪了挪。“睡吧,我守著你。”
小姑娘心滿意足地睡了下去,特別習慣地拉上他的手,嗅著淡淡的降真香味道,終于進了夢鄉。
帝尊大人看著這一幕,心頭也是無奈。他就納了悶了,活了四百多年,老天爺都拿他沒辦法,天道都弄不死他,怎麼一著這丫頭他就這麼慫呢?他師離淵這四百多年慫過嗎?沒有吧?這究竟是哪里出了偏差?
仁王府。
三皇子權青允坐在榻上生悶氣,地上還坐著個剛剛大怒之下一把扔出去的小妾。
大半夜府墻突然塌了,這什麼事?去年剛修的府墻,堅固程度直皇宮,怎麼能說塌就塌了?這事兒傳出去讓他的臉放哪放?
猜你喜歡
-
完結1410 章

傾世獨寵:娘娘又出宮了
一頓野山菌火鍋,沐雲清成了異時空的王府小姐,父母早亡哥哥失蹤奶奶中風,她被迫開始宅鬥宮鬥。 對手手段太低級,她鬥的很無聊,一日終是受不了了,跑到了蜈蚣山決定占山為王,劫富濟貧,逍遙快活。 可誰知第一次吃大戶,竟是被燕王李懷瑾給纏上了。 山頂上,沐雲清一身紅衣掐著腰,一臉怒容:“李懷瑾,我最後一次警告你,我此生隻想占山為王與山為伴,王妃王後的我不稀罕!” 在戰場上煞神一般的燕王李懷瑾此時白衣飄飄站在下麵,笑的那個寵溺:“清清,你怎麼知道我還有個彆名叫山?” 沐雲清氣結:“你滾!”
267.3萬字8 34344 -
完結382 章

深宮策·青梔傳
她的眼看穿詭術陰謀,卻不能徹底看清人心的變化; 他的手掌握天下蒼生,卻只想可以握住寥寥的真心。從一個為帝王所防備的權臣之女,到名留青史的一代賢後,究竟有多遠的距離?一入深宮前緣盡,半世浮沉掩梔青。梧桐搖葉金鳳翥,史冊煌煌載容音。
77.2萬字8.18 25607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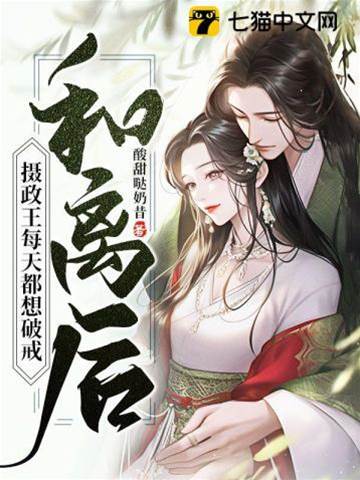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