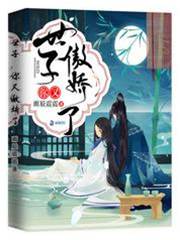《在三國的非鹹魚生活》 第1214章 聖裁
延熙十三年二月初一,長安未央宮,大朝議。
這是開年以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大朝議。
正月的時候雖然也進行過一些朝會,但基本都是禮制上規定的朝會,比如說天子祭天,祭祖,或者是百朝賀等禮節事件.這些朝會上,是不會專門討論國策的。
畢竟,國之大事,在祀在戎嘛。
而到了二月初一的第一次大朝議,纔是真正決定大漢接下來一年甚至是數年工作重心的時候。
而這次大朝議,參加朝議的人數也是格外的多畢竟剛剛參加完正旦嘛,正好,被諸葛亮留下來,一起參加這次朝議。
朝議的前半段,沒啥特殊的,就是歷來慣有的三省和六部來回扯皮,就新一年的施政方案和財稅收分配進行來回的爭奪。
大部分的事,都是走個過場而已,畢竟大方向的事,三省和六部已經私下通過了,剩下的無非就是一些細節上的問題需要當庭辯駁一下,在皇帝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存在而已。
每年的第一次大朝議,基本都是這麼過的,劉禪自己都已經習慣了。
但是,這次大朝議的後半段,突然出現了一個意外。
兗州刺史徐庶突然出班奏事。
“.今曹魏近亡,東吳僭越之輩尚在,我大漢三興在即,豈可容之。故此,臣請陛下下詔伐吳,以正天下。”
反正這個意思呢,就是說曹魏如今已經元氣耗盡,不足爲慮了,應該把接下來的攻略重心,放到攻取東吳方面了。
但徐庶這話一出吧,朝臣中倒是沒有多人有意外,可劉禪卻嚇了一跳。
這不在這次大朝議的奏事範圍之啊。
關於是先攻魏,還是先伐吳的事,從延熙十二年的年底左右,諸葛亮等人就已經開始討論了,劉禪其實也知道,畢竟事關國家大事,諸葛亮等人討論的時候,劉禪也是按照慣例,讓關興和陳祗兩人蔘與例會,聽取諸位重臣的商議容的。
Advertisement
只是呢,按照以往的規矩,關興和陳祗兩人,是隻帶耳朵,不帶,只負責聽,聽完後把各位重臣的意見彙報給劉禪,讓劉禪知曉。
因此,劉禪是知道這個事兒,諸葛亮等人,到目前爲止,並沒有達一致的。
諸葛亮當然還是擺出了一副置事外的樣子,不表態,不發言,不決斷。
但剩下的人裡面,徐庶,龐統,姜敘是支持伐吳的,但張溪,李嚴是反對伐吳,主張先滅魏的。
兩邊各有兩邊的理由。
伐吳派認爲,如今曹魏已經不足爲慮,部又紛爭不斷,可以效仿當年曹平定河北的故智,放鬆對曹魏的力,引發曹魏部爭鬥,那麼幽州的曹魏小朝廷,必然會因爲鬥而不斷衰弱,到時候都不需要鄴城的諸葛亮出兵,在幽州的姜維就能輕易平定。
而東吳方面,孫權數年不曾對外用兵,一直在休養生息,若任由東吳如此發展下去,未必不會覬覦兗州,河之地。
因此,伐吳派認爲,應該先下手爲強,打東吳休養生息的國策,以如今的國力優勢,制東吳。
而且,如今大漢已經掌握了荊州全境,並且休養生息七年之久,兵糧足。
以荊州地利優勢,上游伐下游,兼以荊南陸路進兵豫章郡,兵臨建業。
水陸並進,縱使無法一戰滅吳,亦可奪取東吳數郡之地,剪除東吳屏障。
這就是伐吳派的出兵理由和出兵條件。
而滅魏派認爲,如今滅吳,時機不到。
一個,是因爲東吳本的實力尚在,有孫權控制大局,雖偶有朝爭,但始終沒有,外有陸遜,朱然,諸葛誕等人護衛建業,貿然全力進軍伐吳,未必能有所收穫,甚至孤軍深吳地的話,未必不會重蹈昔日赤壁之戰的覆轍。
Advertisement
另一個,如今曹魏茍延殘,必然會託庇於東吳,一旦大漢發伐吳之戰,曹魏爲了保證自己的安全,也會在幽州,冀州東部等地出兵擾,導致大漢兩線作戰,腹背敵。
如此,大漢徵吳所費頗巨,大不如集中兵力,先滅了曹魏,消除後顧之憂後,再舉兵伐吳,更加妥帖一些。這,就是滅魏派的理由。
這些事兒,其實劉禪都明白,甚至於劉禪自己,也在伐吳和滅魏之間,來回搖擺不定.他甚至以爲,這事兒不會拿到大朝議上來說,應該會在私下裡,幾個重臣達了一致後,再給自己,自己下詔用印就可以了。
可誰知道,徐庶還是在這次大朝會上說了出來,更重要的是,這事兒可沒有提前跟劉禪通氣。
劉禪並不知道自家的幾位重臣是不是已經達了什麼協議,因此,他下意識的看向了諸葛亮相父,這到底是啥意思?!
可惜,劉禪沒有從諸葛亮上得到任何提示,諸葛亮還是一副面無表的樣子,眼皮子都不帶一下的。
劉禪一時間還真的有點麻爪,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只能是按照朝議流程,就徐庶提出的問題,給衆臣商議。
然後吧,張溪就站出來反對了。
理由還是那個劉禪悉的理由,說現在出兵伐吳並不是合適的時機拉拉的。
而張溪這邊剛說完,龐統又站了出來,詳細講述了伐吳的必要,依然還是劉禪悉的那一套。
而龐統一說完,李嚴又站起來,說什麼如今天下新定,百廢待興,到都要用錢糧簡而言之還是那一套沒錢沒糧的說辭。
如果說,一開始劉禪還有點沒明白啥意思的話,越是往後聽,劉禪逐漸就開始慢慢的明白了諸葛亮的用意了。
Advertisement
一方面,諸葛亮等人確實吵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誰也無法說服誰,因此,只能把這件事放到大朝議上來說,聽取更多大臣的意見。
另一方面,諸葛亮大概也是希劉禪能在聽完後,做出自己的決定,以此來鞏固自己的威嚴和皇權。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諸葛亮在進行權利過度,所以在這麼重要的場合,諸葛亮愣是一句話都不說。
這是好事兒.陳祗都應的給劉禪傳遞了無數的眼神,讓劉禪趕站出來,一錘定音。
在陳祗看來,劉禪選擇哪一種策略,其實都不重要,因爲不管那種策略都會有重臣支持。
功了,決策之功當然就是天子劉禪的,而一旦失敗了,鍋也有支持這種策略的重臣來背.對天子只有好,沒有壞的事兒。
可劉禪卻遲遲無法下定決心。
他也知道,作爲一個天子,他在這件事上不管說什麼都有人會支持自己.但是吧,事關國策,事關數萬將士的生死存亡,他本不敢輕易下決定。
一旦做錯了決策,可是要有數萬人送命的。
劉禪到底還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生,說好聽點,他是太過於仁慈,說難聽點,他就是有些優寡斷,沒有帝王該有的心狠手辣。
再一個,劉禪是真的不習慣,這種國家大事,要由自己來裁決。
因此,劉禪再次下意識的看向了諸葛亮,猶豫了一下,還是出聲詢問道,“相父以爲,此事當如何置?!”
諸葛亮無奈的擡頭,看了眼劉禪,默默的在心裡嘆口氣。
天子到底還是缺乏了一些果斷.但其實,這也在諸葛亮的預料之中,畢竟之前的十幾年,都是諸葛亮把所有的事都辦完了,天子缺乏歷練。
但這次吧,諸葛亮決定,還是不能太慣著天子天子,就該有天子的覺悟。
因此,諸葛亮出班,對劉禪拱手一禮,說道,“此事,還請天子聖裁。”
這話一出,給劉禪都噎了一下.我要是能有主意,還問相父作甚?!
可如今是大朝議啊,諸葛亮都當衆這麼說了,剩下的事兒,就是劉禪二選一了,不可能有其他的選項。
劉禪也是無奈,只能是自己來回權衡,琢磨了良久,最後決定.
“此事,容後再議!!!”
猜你喜歡
-
完結253 章
黑道王妃傻王爺
霸氣的黑道女王,一朝穿越嫁入神秘王府,傻王爺張牙舞爪的撲過來要跟她生娃娃.她堂堂黑道女王,怎麼可以跟一個傻王爺成親?被關冷宮的妃子突然離奇死亡,她沉著,冷靜,一步步走近陰謀的中心,危機時刻總有神秘面具男子出手相救十年前的真相正在慢慢浮出水面,而她身陷其中,越走近他,便越發覺他身上揹負著太多的秘密,亦真亦假,哪個纔是真正的他?
37.1萬字8.2 143903 -
完結6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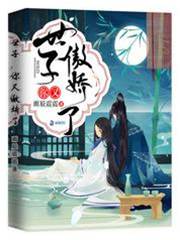
世子你又傲嬌了
【本文男強女強,身心健康,女主穿越,概括來說,就是兩個腹黑的人找到彼此,開啟了坑別人模式的故事。】 聽說,皇上下旨賜婚,慕王府的慕淵世子,要娶俞太師家的孫小姐俞琬琰為世子妃。 卞京城裡,上到王孫貴族,下到普通百姓,集體懵逼 慕淵世子?就那個傳言活不過25歲,整天知道讀書,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病秧子? 沒見過。 俞琬琰?俞太師傳說中的那個毫無存在感的孫女? 更沒見過。 一場賜婚,在卞京城的地界上,投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石子,沒有激起一點水波。 然而隨著兩人的一場婚禮,卻掀起了東慕國裡的權貴交替,眾人這才後知後覺的感嘆,我皇果然是我皇,眼界就是獨特! ———————————— 精彩片段: 慕淵:“聽聞世子妃畫技天下無雙,可否給為夫留下一幅肖像?” 俞琬琰莫名其妙:“天天看到你,留肖像做什麼?” 慕世子遺憾感嘆:“世人都傳本世子活不過25,總要給世子妃留下一點念想。” 某世子妃嘴角微抽,那個狡詐如虎,沒人的時候上躥下跳生龍活虎的人,是誰? “那你準備一下。”
110.6萬字8 35201 -
完結193 章
穿越之改造人生
白岐一穿越就是退婚現場,未婚夫摟著梨花帶雨的堂妹白薇薇,告訴他白薇薇才是他的真愛,讓他退出成全他們。作為凶殘BOSS,白岐哪裡受過這種鳥氣,正要讓他們原地逝世,就被系統告知不可以,否則六級雷擊伺候,並且要求他從此以後必須行好事、做好人,不做就是死亡威脅。 白岐:…… 沈止淵,學神大佬級禁慾高嶺之花,一個傳聞中不近女色、沒有世俗慾望、身負無數傳說的男人,據說連靠近都是褻瀆的存在,在某個人身後輕輕俯下`身,乾燥溫涼的手指搭在對方的手背上,問他:“哪裡不會?” 白岐:……傳聞是不是哪裡不對勁?
43.2萬字8 16650 -
連載67 章

虧錢做拖拉機,這坦克什麼鬼?
重回2012年,陸凡綁定虧錢系統,開局辦煤氣罐廠,然后虧著虧著,他發現自己怎麼就成空軍、陸軍、海軍裝備供應商。而且,連帶著兔子裝備全都升級,鷹醬、大毛直接懵逼。
9萬字8.18 18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