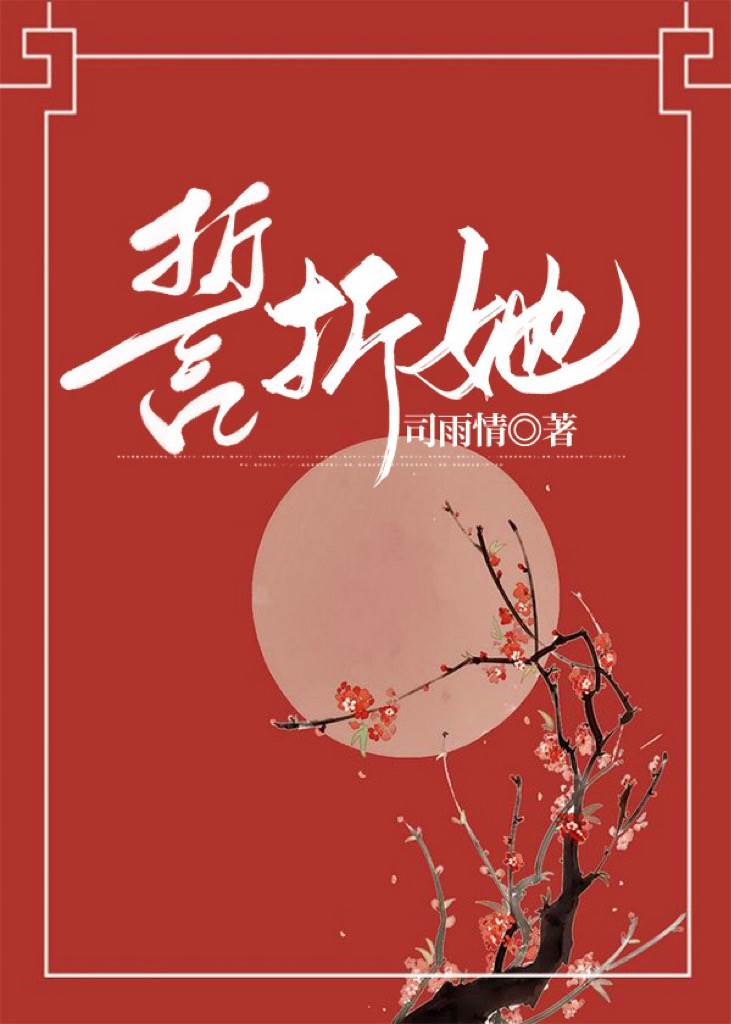《囚春情:清冷權臣破戒後》 第184章 番外:婚後日常(上)
揚州地大博,風景如畫,不僅吸引眾多文人墨客前往,連五年一度的江南畫會也定在了此。
夜裏,大街上熙熙攘攘,燈火通明,江畔畫舫輕搖,竹之聲隨風飄遠,傳到岸邊人的耳中。
熱鬧繁華的夜市上,灌灌一手拉著謝梔、一手拉著裴渡,蹦蹦跳跳地穿過一個又一個小攤。
“阿娘,這次我們出來,爹爹怎麽跟來了?”
“因為你爹是個跟屁蟲!”
謝梔穿著一家常的水藍杭綢翠煙衫,出一削蔥細指,點了點灌灌的腦袋,眉目多了幾分溫。
裴渡聽見母子二人的談話,看謝梔一眼,輕哼一聲:
“有人要生小娃娃了,還不肯在府裏待著,爹爹不得跟著?”
灌灌聽見這回答,轉頭看一眼謝梔微微隆起的小腹,好奇地問:
“阿娘,妹妹還有多久才出來?為什麽我每天和妹妹說話,都不理我?”
謝梔肚子,算了算日子,思忖道:
“約莫還有三個月吧,冬天你便可以見到了。”
那時,恰好是和裴渡婚滿一年的日子。
“該回別院了,夜裏風大。”
裴渡瞧一眼天,鬆開灌灌的手,褪下上的披風給謝梔披上,帶著母子往回走。
“難看死了,不想穿。”
謝梔一漂亮的被暗披風擋了個嚴實,有些不滿地去解係帶。
裴渡修長的手來,將的手摁下:
“幾歲了?灌灌都比你懂事。”
灌灌的目卻依舊落在謝梔的肚子上,忽然意識到什麽,一臉嚴肅地發問:
“阿娘,為什麽妹妹在你肚子裏?”
謝梔一怔:
“不在阿娘肚子裏,難道會在你爹肚子裏?”
“那為什麽灌灌是從蛋裏出來的?為什麽我和妹妹不一樣?”
“這……”
謝梔與裴渡對視一眼,看到了他眼中的幸災樂禍。
Advertisement
見灌灌的眉頭已然皺起,也往下撇,謝梔眨了眨眼,說道:
“是這樣的,你聽我解釋……”
可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
“阿娘你說嘛,為什麽妹妹在你的肚子裏,灌灌是從蛋裏出來的?”
見謝梔被噎住,一臉為難的模樣,裴渡忍不住勾輕笑。
直到謝梔有些惱地瞪他,他才出言解圍:
“妹妹也是從蛋裏出來的。”
“是這樣的,你阿娘貪吃,把小鳥下的蛋吃了,所以蛋到了肚子裏,阿娘隻能自己把妹妹生下來了。”
灌灌驚訝地看向謝梔:
“阿娘,你什麽時候吃鳥蛋的?我每日逃學都給你帶好吃的,你怎麽可以這樣!”
“你差不多得了。”
謝梔拿帕子了臉,不想理他們兩個,率先走到街尾,由侍扶著上了馬車。
“爹,你怎麽知道的?你看著阿娘吃嗎?為什麽不告訴灌灌?”
灌灌又抬頭問裴渡。
“爹說過,你一日隻能問二十次為什麽,今日的額度已然用完了,恕不回答!”
……
一家三口帶著侍從在揚州盤桓十餘日,等畫會結束,裴渡的休沐日也要告一段落了。
他如今為朝廷要員,任尚書令一職,比從前忙得不止一點兒,這回也是遞了好幾道折子上去,才能得這短暫的休沐之期。
等重新坐上車,往碼頭趕時,謝梔開始犯惡心,不斷喝著提前備下的酸梅湯。
“阿娘,那個地方為什麽破破的?”
灌灌坐在旁,指著路旁一廢棄的舊宅,問。
謝梔放下酸梅湯,順著灌灌的視線一路看去,神怔了怔。
此乃是揚州最為繁華的民居,在這裏住的也都是非富即貴之家,可這宅邸卻荒廢得太過惹人注目。
……
馬車停下,一家三口走到那舊宅門前。
Advertisement
謝梔推開那扇早已腐朽的門,正要抬步,一路過的老婦勸道:
“哎!貴人留步,你們是外地來的吧?這宅子不吉利,可別進去了。”
灌灌一臉好奇:
“老婆婆,為什麽不吉利?”
“此乃從前揚州刺史謝晉淮的府邸,謝晉淮罪惡滔天,被抄家後,沒有人願意買下這宅子,此便荒廢了下來,近些年,還時有鬧鬼的傳聞呢!”
那老婦人說罷,提著一籃子新鮮蔬菜,步履蹣跚地離開了此。
謝梔同裴渡對視一眼,扶著肚子,慢慢往裏走。
曾經的金銀窟,早已過眼雲煙,眼前的庭院,已然雜草叢生。
這便是,和裴渡初見的地方。
不知不覺中,十年飛逝。
一路走來,見此此景,隻覺心中蒼茫。
可眼前的景象在灌灌眼裏,卻是天然的遊戲之地。
等三人行至一不起眼的小院前,灌灌驚呼:
“哇!好多草啊!長得比灌灌還高!好好玩!”
“哎!快拉著他,別讓灌灌被蟲子咬了。”
見灌灌撲騰進草地裏,謝梔推一把裴渡,讓他把灌灌弄出來。
裴渡去抓灌灌,灌灌得了趣般往牆角跑,跑到那破敗的牆角,腦袋立馬被磕了一下。
“爹!討厭你!”
灌灌著腦袋,有些委屈地控訴他。
裴渡走到他麵前蹲下:
“子這般跳,往後如何能大事?等回府之後,你若再不好好上學堂,和他們幾個瘋玩,我就……”
灌灌這一下撞得不嚴重,生氣兩下就不在意了,也沒仔細聽裴渡的話,一雙眼睛到轉,很快就指著牆邊道:
“爹爹!看,這裏有幾道劃痕!上麵還刻、刻字呢!”
裴渡湊近,見果然如此,隻是那字跡上染了塵垢,已然看不太清了。
見父子二人都蹲在那牆邊,謝梔小心翼翼踩過石碎草,朝他們走來。
Advertisement
瞧見灌灌用袖子著那牆上的髒汙,有些不悅:
“髒孩子!”
“阿娘,快來看!”
灌灌跑上前拉住,把謝梔帶到那麵牆前。
裴渡已然辨別出了那上頭的幾道刻痕和字跡,低聲念出來:
“阿梔兩歲、阿梔三歲、阿梔四歲、阿梔五歲……”
也隻到阿梔五歲。
因為的母親,在五歲時便去世了。
謝梔走到他後,看見那幾行字,腳步停住。
再環顧四周,仔細辨別之後,這才驚訝道:
“原來,這裏是我從前的院子,十年過去,竟已不認得了。”
謝梔走到那麵牆前,手挲著那幾行字,眼眶泛紅:
“我阿娘是被父親賣到這裏做妾的,隻為給弟弟換上學的束脩,那年才十五歲,去世時,也不過二十一歲。”
“從前我在這裏住時,常常想,我和,是否都是親緣淺薄之人,才會那般孤苦。”
裴渡察覺到立刻低下來的緒,站起攬住:
“可你現在有我、有灌灌,還有即將出世的孩子,怎會是親緣淺薄?嶽母大人在天之靈,也會保佑你的。”
灌灌十分興,並沒有注意到母親神的變換,站到那刻著“阿梔五歲”的橫線前,笑著對道:
“阿娘,這條線才到灌灌脖子!這是誰呀?好矮!”
謝梔看他那稽的模樣,終於破涕為笑。
一家三口立在夕下,畫麵繾綣而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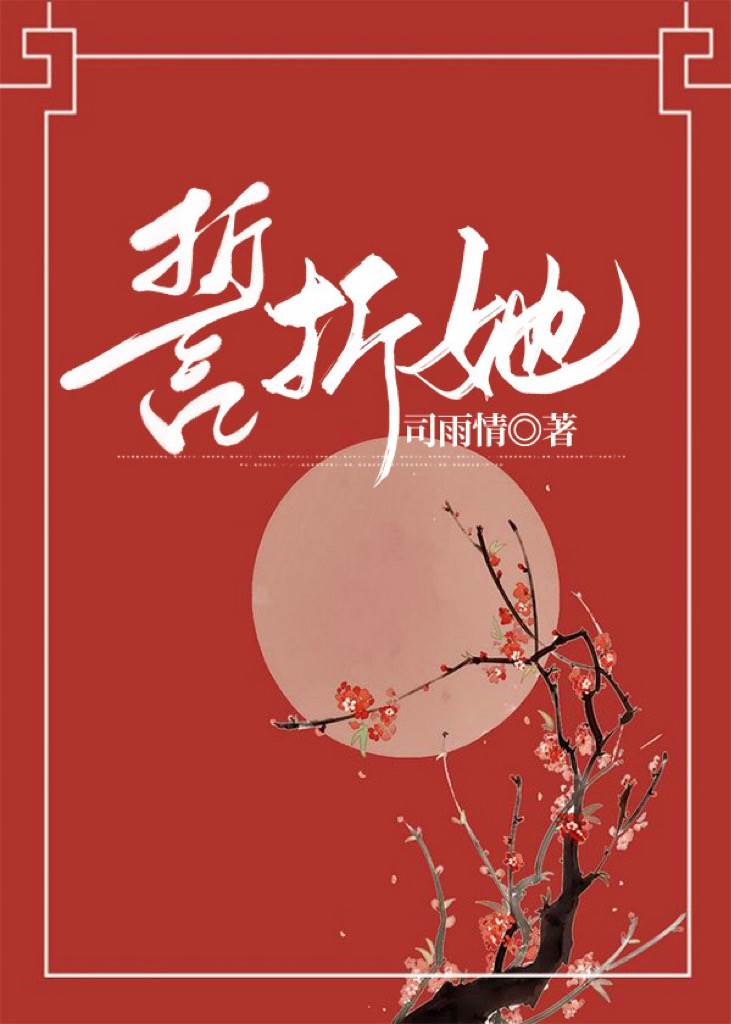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170 章

娘娘嫵媚妖嬈,冷戾帝王不禁撩
一紙詔書,廣平侯之女顧婉盈被賜婚為攝政王妃。 圣旨降下的前夕,她得知所處世界,是在現代看過的小說。 書中男主是一位王爺,他與女主孟馨年少時便兩情相悅,孟馨卻被納入后宮成為寵妃,鳳鈺昭從此奔赴戰場,一路開疆拓土手握重兵權勢滔天。 皇帝暴斃而亡,鳳鈺昭幫助孟馨的兒子奪得帝位,孟馨成為太后,皇叔鳳鈺昭成為攝政王,輔佐小皇帝穩固朝堂。 而顧婉盈被當作平衡勢力的棋子,由太后孟馨賜給鳳鈺昭為攝政王妃。 成婚七載,顧婉盈對鳳鈺昭一直癡心不改,而鳳鈺昭從始至終心中唯有孟馨一人,最后反遭算計,顧婉盈也落了個凄然的下場。 現代而來的顧婉盈,定要改變命運,扭轉乾坤。 她的親夫不是癡戀太后嗎,那就讓他們反目成仇,相疑相殺。 太后不是將她當作棋子利用完再殺掉嗎,那就一步步將其取而代之。 如果鳳鈺昭命中注定要毀在女人手上,那麼也只能毀在她顧婉盈的手上。
32.1萬字8 1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