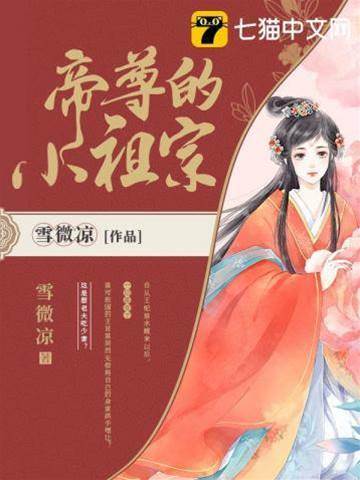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赴良宵》 第79章 信
可巫師卻神復雜、眸帶懼怕得看向范靈枝。
范靈枝亦面無表得回著。
巫師像是又想起了什麼可怕的事,的聲音帶著抖:“天、天機不可泄,總之,奴家日后定會為貴妃肝腦涂地、死而后已。”
不肯說,倒是勾起了范靈枝的好奇心。
試探道:“你可是看到了滿大街跑的小車車、又或者是有人在里頭說話的小黑盒子?”
巫師搖頭:“那倒沒有。”
范靈枝未免有些失。
巫師對著范靈枝又敬畏跪下:“貴妃乃是世間最尊貴之人,日后更是不可限量。”
范靈枝輕笑起來:“很好,本宮就需要你這種睜眼說瞎話的人才。”
巫師大為:“謝貴妃贊賞!”
范靈枝:“皇上已將你給我置,日后,你便是我的人。只要你乖乖的,本宮自能保證你一生富貴、高枕無憂。”
說罷,范靈枝用眼神示意阿刀打開牢門。
然后走到巫師邊,低頭在耳邊低聲輕語了幾句。
巫師聽罷,忍不住抬起頭愣神看。
范靈枝的臉帶著說不清的幽深:“可記住了?”
巫師怔怔點頭:“記、記住了。”
范靈枝低笑:“記住了就好。”又看向阿刀,“阿刀,將半仙請出大牢。”
阿刀領命,當即指了兩個奴才將重傷的巫師抬出來,一行人這才浩浩得一路走了。
巫師名花池,廿八歲,至今未婚。
范靈枝將花池安排在了芙蓉宮,讓安嬤嬤照顧,又讓王太醫日日來給診治,務必要將上的重傷醫治妥當。
Advertisement
王太醫得令,自是
賣力,當即使出了渾解數,為花池行針灸之,務必要向貴妃證明自己的高超醫。
花池在安嬤嬤的照料下,洗凈了臉上的易容和,倒是顯得更好看了。只可惜頂著個禿頭,否則也是個漂亮的子。
芙蓉宮此時除了巫師,還有祁嬪此時也住在這。
只是祁嬪被皇上在此,因此只能整天窩在芙蓉宮,日日坐在院子里,著頭頂偶爾飛過的烏,出羨慕的眼神。
烏尚且如此自由,可竟只能屈居在這小小一方天地,還得日日看著花池那個巫婆,讓的心又恨又苦。
眼下,祁葵坐在院子賞著角落的狗尾花,偏殿的花池也被安嬤嬤攙扶了出來,坐在了院子西北角眺視野。
馮嬤嬤看到花池就氣不打一來,當即冷著臉走了過去,冷聲道:“沒看到祁嬪正在賞花嗎?閑雜人等還不速速離開!”
花池哼了一聲,對安嬤嬤道:“安嬤嬤,讓我住在芙蓉宮,可是靈貴妃的安排。眼前這刁奴竟敢讓我離開,難道比貴妃還要厲害?”
安嬤嬤當即冷笑:“半仙何必和那等狗奴才置氣。”又說,“了芙蓉宮的妃子,便是被打了冷宮,日后怕是連見皇上一眼都懸咯。”
祁葵猛得抬頭瞪著安嬤嬤,眼神鷙,十分可怕。
馮嬤嬤更是氣得沖上前來,作勢就要掌摑安嬤嬤,幸好安嬤嬤深宮經驗厚,當即迅速躲避了開去,甚至還反手給了馮嬤嬤一掌。
直打得馮嬤嬤落下淚來,嚎啕大喊:“虎落平被犬欺,你們、你們且給我等著——”
Advertisement
花池對著馮嬤嬤吐了吐舌頭。
安嬤嬤對著馮嬤嬤吐了口口水。
祁葵氣到恍惚,當即二話不說拉著馮嬤嬤回了房去,再不想見到后的花池。
寢房,十分簡陋。就連床榻,都是一米二的單人床。
祁葵和馮嬤嬤二人相互擁抱著取暖,祁葵靠在馮嬤嬤懷中,抑制不住得痛哭:“嬤嬤,這樣的日子,我怕是……堅持不下去了!”
馮嬤嬤留下了痛苦的淚:“娘娘不如休書一封,老托人將信送出去,讓老爺和夫人給您撐腰!”
祁葵哭得傷心至極:“皇上如今已是鬼迷心竅,中了范靈枝的毒,怕是就算讓父親宮來,也于事無補。”
祁葵聲音愈弱:“且父親子愈加不好,怕是連宮的力氣都沒有。兒不孝,竟還要如此勞煩他為我心……”
馮嬤嬤道:“娘娘怎能如此氣餒?難道你忘了,那范靈枝可是喪失了生育能力的?這樣的子,又怎能當上大齊的皇后!”
聞言,祁葵雙眸逐漸亮了起來,就像是絕之人抓到了一救命稻草。
是啊,本不會生育,無法為溫惜昭生下一兒半。
如此一來,又有什麼資格做大齊的皇后呢?
想及此,祁葵當即沉沉道:“拿紙筆來。”
馮嬤嬤當即取來紙筆,放在祁葵面前。
祁葵拾筆速寫,然后將信紙吹干疊好,裝袋中遞給馮嬤嬤。
> 馮嬤嬤很是歡喜,當即親自出了芙蓉宮去,將信紙給了自己在宮安排的眼線,讓他們將信送出宮去。
當日晚上,范靈枝看著阿刀截胡送上來的信,陷了短暫的沉思。
Advertisement
祁葵要抓著不能生育這一點大作文章,還讓父親去聯合左相,共同覲言。
阿刀見范靈枝一臉若有所思的樣子,忍不住道:“主子若是覺得困擾,直接將這家書撕了便是?”
范靈枝卻彎起眼來:“這信可不能撕。”
阿刀好奇。
范靈枝道:“好好利用,便是另外一副結果了。”
說罷,范靈枝在阿刀耳邊低語了幾句,這才讓阿刀將這信按照原路送回去,務必要讓祁府的人收到。
等范靈枝敷完面、又做了會兒瑜伽,溫惜昭終于來了。
今日依舊是他勤于正事的一天,溫惜昭為皇帝,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大齊愈加繁華、國泰民安。
他每日從書房下了班就會過來,范靈枝早已習慣。
繼續做自己的瑜伽,橫豎已經把他當做自己的室友,他做他的,自己忙自己的,互不打擾,合作愉快。
只是范靈枝翹著屁在做瑜伽作時,就看到溫惜昭正站在一旁,眸幽深得盯著自己的……小蠻腰。
范靈枝當即收回作,對他嘿嘿笑:“皇上不,我下面給你吃啊?”
溫惜昭雙眼散發出狼的:“真的?”
范靈枝翻了個白眼,蓋上被子、閉眼睡覺。
只是睡著睡著,突然就到自己腰間多了一抹炙熱。
猜你喜歡
-
完結1747 章

鬼面梟王:爆寵天才小萌妃
一道圣旨,家族算計,甜萌的她遇上高冷的他,成了他的小王妃,人人都道,西軒國英王丑顏駭人,冷血殘暴,笑她誤入虎口,性命堪危,她卻笑世人一葉障目,愚昧無知,丑顏實則傾城,冷血實則柔情,她只想將他藏起來,不讓人偷窺。 “大冰塊,摘下面具給本王妃瞧瞧!”她撐著下巴口水直流。 “想看?”某人勾唇邪魅道,“那就先付點定金……” 這是甜萌女與腹黑男一路打敵殺怪順帶談情說愛的絕寵搞笑熱血的故事。
316.4萬字8.09 152892 -
完結1039 章
絕寵世子妃
前世被親人欺騙,愛人背叛,她葬身火海,挫骨揚灰。浴火重生,她是無情的虐渣機器。庶妹設計陷害?我先讓你自食惡果!渣男想欺騙感情?我先毀你前程!姨娘想扶正?那我先扶別人上位!父親偏心不公?我自己就是公平!她懲惡徒,撕白蓮,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重活一世,她兇名在外,卻被腹黑狠辣的小侯爺纏上:娘子放心依靠,我為你遮風擋雨。她滿眼問號:? ? ?男人:娘子瞧誰礙眼?為夫替你滅了便是!
196.7萬字7.75 191914 -
完結107 章

蕓蕓卿州
魂穿貧家傻媳婦,家徒四壁,極品後娘貪婪無恥,合謀外人謀她性命。幸而丈夫還算順眼,將就將就還能湊合。懷揣異寶空間,陸清蕓經商致富,養萌娃。鬥極品,治奸商,掙出一片富園寶地。
17萬字8 27651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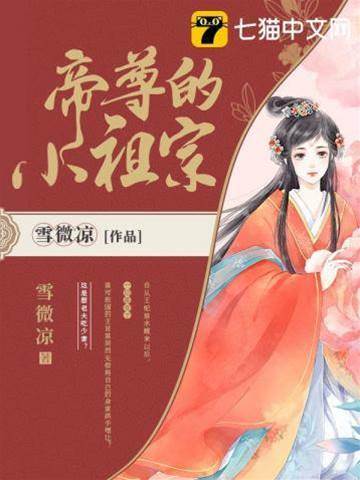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