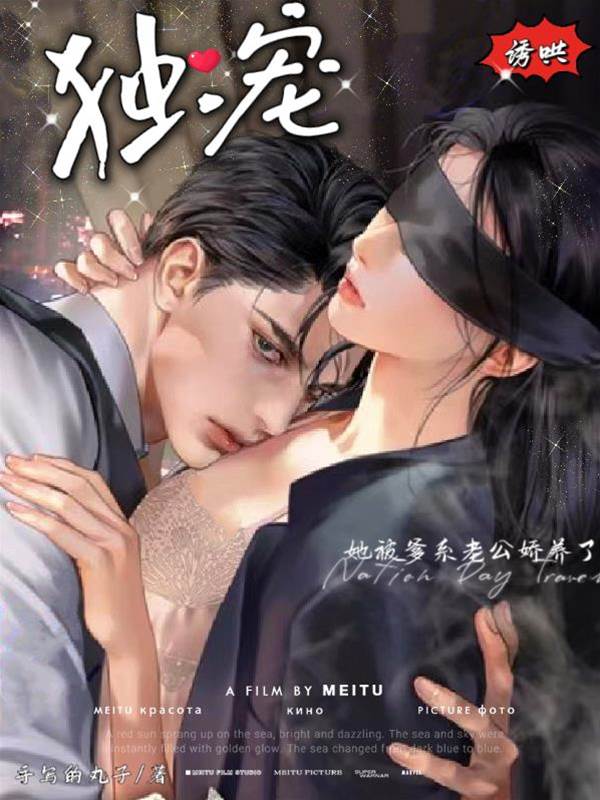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頂級溺寵!嬌軟小漂亮被病態圈占》 第41章 被惡龍抓到山洞裏的小公主
水流澆在地上的枯枝敗葉,在夜晚中聲音格外清晰。
那人穿著一的工裝,裏哼著歌,搖頭晃腦。
後約傳來樹枝被踩響的腳步聲,那人頭也沒回,直接開口,
“找這麽快?這麽快就回來了哥們?”
腳步聲近,對方沒有回答。
那人拽了拽腰,還沒來得及把腰帶扣上,就聽到什麽沉重的東西劃破空氣,隨即“砰——”地一聲,敲在了他後腦勺上。
拽著腰的手失去了力度,那人使出最大的力氣扭頭,瞳孔瞬間驚恐張大,
“你——”
隻是他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出口,那塊巨大的石頭再次迎麵而來,狠狠砸在了他的臉上。
穿著工裝的在空氣中搖晃了兩下,最後失去了所有支撐,癱倒在已經澆的枯枝敗葉上。
借著那兩三道月,渙散的眼神中出現了一張堪比修羅的沉臉龐。
痛覺麻痹了他的神經,溫熱的鮮在臉上蔓延,鼻尖嗅聞到的全是鹹腥的鐵鏽味。
紅的鮮穿過睫落到眼睛裏,眼前猩紅一片。
他張了張,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隻能眼睜睜的看著那個森恐怖的男人,嫌棄的踢了踢他的子,然後從他懷裏掏出了槍。
消音安裝完,保險栓被拉開。
那人用盡最後的神智,裏發出“支支吾吾”的聲音,哀求著對方放過他。
那個臉沉的男人材高大,緩緩的舉起了手中的槍,對準了他的膛。
地上的人努力蠕,但是卻帶不了自己的。
他眼睜睜的看著男人手臂緩緩下移,扣扳機。
隻聽“砰”地一聲,破空而出的子彈打在了他臍下三寸的地方。
“老張?”
遠傳來約約的呼喊,可惜地上的人再也沒辦法應聲。
他已經完完全全的痛暈了過去,跟條死豬一樣。
Advertisement
遠傳來腳步聲,臉沉的男人稍稍偏了偏子,高大的影匿在壯的樹幹後麵。
不多會兒,一個影影綽綽的形出現,他裏罵罵咧咧,一邊喊著地上人的名字。
“你他媽躺在地上在搞什麽——”
看清對方的形之後,他裏的話戛然而止——
兩分鍾以前還在跟他聊天的老張,現在跟死人一樣躺在了地上。
如果他沒看錯的話……
地上大片大片流的影是流出的鮮。
而迸濺在他腦袋旁邊的白凝膠狀……
那人睜大了眼睛,驚恐的從懷裏要出槍。
然而,“啪嗒”一下,鞋子踩在地麵上的聲音再度響起。
周而複始的循環再次開始。
就像剛剛一樣。
-
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蜷在稻草上的小人覺得有些冷。
一直覆蓋在邊的熱源消失了,躺在這裏,覺四麵八方的冷風都朝自己襲來。
薑杳杳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手指在眼皮上了,慢吞吞的坐了起來。
悉的腳步聲從口的方向響起,抬著一張白玉小臉看了過去,線太黑又沒打開手機,看不到來人的模樣。
有些張。
下一瞬間,就聽到男人的聲音響起,帶著寵骨髓的溫,
“杳杳什麽時候醒的?”
不過片刻的功夫,男人頎長的影裹挾著外麵來的寒氣,單膝跪在麵前,輕輕的了的腦袋。
就連向來低沉的聲音都帶著小心翼翼的意味,
“我不是故意要離開的。”
“杳杳醒來沒看到我,是不是害怕了?”
小人緩緩的眨了眨眼睛,然後有些遲鈍的乖乖點了點腦袋,聲音的,
“有點兒。”
晚上喝的酒度數好高,吹了風,睡了一覺,現在頭已經開始作痛了。
Advertisement
抬手了自己的腦袋,下一瞬間就有手指代替了的作,
“是不是頭疼?”
男人修長的手指有規律的按著頭上的位,繃的神經和頭痛的覺都得到了緩解,對方的聲音很低,像是生怕驚到了,
“我幫杳杳按一按,很快就能好了。”
“是不是還是有些困?現在離天明還很早,一會兒不疼了,杳杳可以繼續睡覺。”
“離天明還很早嗎?可是我覺自己睡了好長好長的一個覺……”
乎乎的聲音回在黑暗的山裏,尾音微微上揚,帶著撒的意味。
裴珩半垂著眼睛看著自己的小仙子,輕聲回答:“很早。”
他的杳杳又乖又,就這樣抬著一張漂亮小臉,白的在黑夜中都幾乎能發。
像是被惡龍抓到山裏的小公主。
又纖細又脆弱,乖乖的坐在床上,等著自己安。
就這樣全心的依賴著自己,像是一朵開在午夜的孱弱山茶花,似乎沒有自己的澆灌。
就會凋零枯萎。
衰殘頹敗了。
不多會兒,頭痛已經得到緩解的小人攥住了男人修長的手指,輕輕的拉著對方的手臂,連聲音都格外乖巧,
“裴珩,你有沒有睡覺啊?你是不是也困了?”
男人輕輕地“嗯”了一聲,將他的小仙子擁進了懷裏。
鼻尖似乎縈繞著一點腥的氣味,但是仔細再聞的話,又找不到了。
仿佛是自己的幻覺。
薑杳杳還是不放心,抓著男人口的服,聲氣地詢問對方,
“裴珩,你傷了嗎?剛剛遇到了壞人嗎?”
“沒有。”
男人聲線平穩,
“什麽也沒有遇到,杳杳放心好了。”
他的聲音低沉,恍若在耳邊的輕語,格外有讓人信服的力量。
薑杳杳沒有再繼續糾結,乖乖合上了眼皮。
Advertisement
大概是這個山裏的氣味不好,剛剛聞錯了。
山中再次恢複平靜。
濃墨暈開的黑中,男人上清冽的氣息將團團包圍,格外有安全。
兩道呼吸聲均勻,平緩。
隻是原本應該閉眼睡覺的男人緩緩睜開了狹長的眼眸,眼底暗詭譎。
他輕輕的吻了吻懷中人的發,寬大的手掌有一下沒一下地拍著纖細的肩背,像是在哄,睡不著覺的小孩。
視線落到口的方向,收起來的兩隻手槍硌在他的後腰。
黑暗中,男人的角勾起一點冰冷弧度。
似乎是在好奇,是剩下的人自投羅網快一些,還是他的人過來更快一些。
答案像即將揭開的賭注一樣讓人興。
男人懶懶地起眼皮。
眼底興味滿滿。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許你一生空歡喜
"婚後老公卻從不碰我,那我肚子裏的孩子是誰的?出軌捉奸被趕出家門…… 九死一生後,我被逼成為老公上司的情人,孕母。 本以為隻是一場金錢交易,我不想動心動情,可我卻在他忽冷忽熱的溫柔裏,失了身,陷了情。 一場情劫過後,縱身火海,再見麵,我又該如何麵對?"
21萬字8 14587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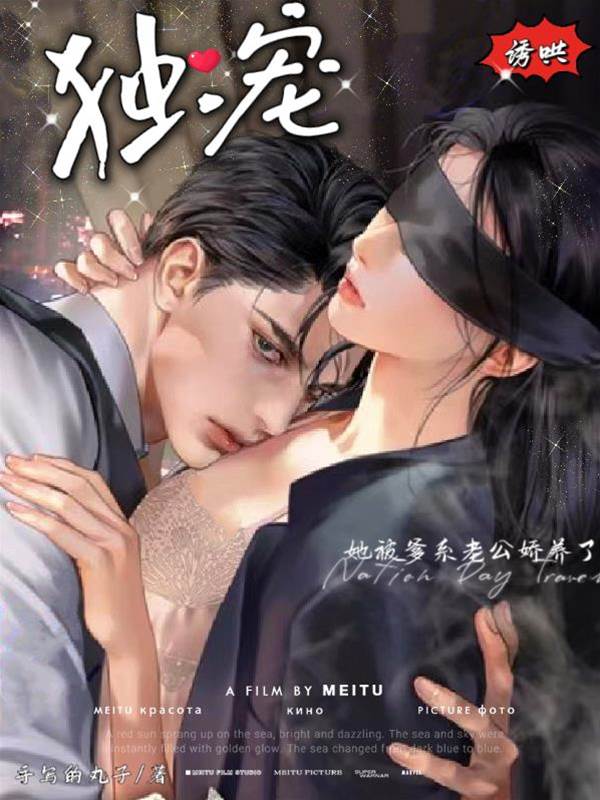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2612 -
完結182 章

嬌惹!他又野又撩,卻為我折腰
[風情萬種釣系畫家X離經叛道野痞刺青師][SC|甜欲|頂級拉扯|雙向救贖] - 只身前往西藏的第一天,宋時微的車壞在了路上。 她隨手攔下了一輛車,認識了那個痞里痞氣的男人。 晚上在民宿,宋時微被江見津的胸肌腹肌迷得五迷三道。 她溜進他的房間,將他堵在了墻角,問他:“江見津,zuo|嗎?” - 川藏南線全程2412公里,從成都到拉薩,途徑22個地點,走走停停耗時五個月整。 這五個月里,宋時微跟江見津成了飯搭子、酒搭子,還有chuang|搭子。 在拉薩逗留了半個月后,宋時微賣掉了車子準備飛機回北京。 江見津神色淡漠,只問她:“都要分手了,最后一次也沒有?” 宋時微撓了撓下巴,回:“這個倒也是可以有。” - 重逢是在一年后。 療好傷的宋時微一鳴驚人,新作品一舉拿下英國BP肖像獎的一等獎,并于同年年底在國內舉辦了首場個人畫展。 慶功宴上她見到了本次畫展最大的贊助商,那個傳說中的商界奇才。 包廂門推開,她看到的是西裝革履的江見津。 他起身跟她握手,似笑非笑地問她:“宋小姐在畫畫之前不需要征得本人的同意嗎?”
24.6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