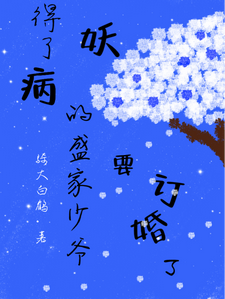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囚禁野玫瑰》 第83章 地下室裏好像關了個人
什麽時候開始的,怎麽總是被鬱歡牽緒?又是從什麽時候開始信這些虛無的?他自己就是醫生,求人不如自渡。
可想歸想,他還是記進心裏了,等鬱歡好了,要帶著一起去寺廟,給孩子立一個牌位。
屜裏的藥吃完了,他很久沒去拿了,看來不能斷,緒穩定很重要。
畢竟有句話這樣說,醫者難自醫。
時屹回了辦公室,周姨看著他越走越遠才長舒口氣,然後對著手機發了消息。
沒一會周景辭就從拐角出來了,周姨輕聲說:“時先生剛走,嚇死我了,被撞見就完了。”
周景辭點點頭,看著病床上一團的小人,手還捂在小腹的位置。
“你進去看看吧,萬一時先生回來了也好有地方躲。”
他搖搖頭,隻是看著鬱歡出神:“不了,好不容易睡了會,別吵醒了。”
“也好,剛剛時先生進去鬱歡就被嚇了一跳,睡的不踏實。”
周景辭沒說話,隻是一直盯著鬱歡看。
一種莫名其妙的愫在心底蔓延,周景辭想抓住研究一下,可手剛出去那種覺便從指溜走了。
指尖麻了一下,麻的緒跟著到了心頭。
喜歡和不一樣,雕塑很,立在那裏高貴優雅,你會覺得很欣賞,但沒有想要占為己有的意思,因為它沒有生命,冷冰冰的不會回應。
但呢,周景辭不清楚,此前對鬱歡或許是欣賞,但從今天開始大概要變了。
因為他看到了鬱歡的悲傷,眼前的人有有,鮮活的就在眼前,甚至臉上還帶著淚痕,看到難過他會揪心,很想抱著安,想說一聲“一切有我。”
這緒來的莫名其妙,他問周姨:“奇怪,也沒見過幾麵,不知道為什麽就想幫。”
Advertisement
周姨笑了幾下:“你這子我還不知道,最講究的是個眼緣,小時候看見大提琴哭著喊著要買,那麽貴,你媽不舍得,買了個什麽吉他騙你說一樣,你還真執拗,當真是一下沒,自己攢著歲錢買了大提琴回來,自此這輩子,大提琴再沒離過手。”
他輕聲問:“什麽意思。”
“什麽意思你還不懂嗎?用你們年輕人的話來說就是一見鍾,大概是鬱歡太漂亮了,你看上人家了。”
周景辭聽到了,也跟著疑了一下,是一見鍾嗎,還是見起意。
不知道,反正見鬱歡第一麵的時候就覺得這小孩真漂亮,氣質又那麽清冷溫婉,就跟月亮似的,可遠觀卻不能。
直到今天他才有了占為己有的想法,總是不開心怎麽能行,他想看鬱歡笑。
可惜玫瑰花上有刺,也總有蟲子來擾,他願意做那個護花使者。
這兩次逃跑他有了教訓,跑沒用,鬱歡總是會被抓回來,隻要時屹地位一天不倒就總是奢,既然如此,為什麽不從搞垮時屹呢?
他知道,時家還有個小三上位的母親,領了個私生子,那位時太太是有點手腕的,一直對時氏集團虎視眈眈。
不止是份,他還想從心搞垮時屹,讓時屹從雲巔跌落,滿心傲氣一點點消失殆盡。
他說:“周姨,你說當醫生的是不是最驕傲的就是那雙手了。”
“那是當然了。”
“是啊,那當然了。”周景辭笑了笑,神還是一如既往的溫和,隻是總覺得笑裏帶了刀尖:“手廢了還算什麽醫生呢。”
周姨不知道他的意思,看了看周圍低聲說:“對了,別墅地下室裏好像關了個人。”
周景辭一愣,側頭看向周姨:“什麽?”
Advertisement
“時先生總是讓我多做些飯,他隔三差五就帶著飯去地下室,”周姨神張:“所以我覺得地下室裏關了人,鬱歡好像也知道。”
周景辭略微皺了皺眉,清雋的臉龐帶上一不解:“地下室關了人?等我好好查查。”
周姨點頭:“你盡管放手去做,鬱歡這邊我會照顧好的,就等你趕快把救出來,這孩子,太可憐了。”
他沒說話,隻是又抬頭看過去,鬱歡還是一不,保持著一團的姿勢。
得盡快了,鬱歡還在等著自己。
臨走前周景辭又想起什麽,從服裏拿出來一個小藍牙和一封信,他給周姨:“幫我轉給鬱歡,小藍牙你自己收著,可以給放音樂,調解緒不錯。”
周姨收了後放進兜裏。
周景辭開車出了醫院,手隨意放在方向盤上,他的視線由前方慢慢下移,看著骨節分明的手,隨後輕輕一笑。
這雙手是用來拉大提琴的,不能沾上。
好在他已經挑到了一位合適的人選。
時屹大概想不到,隨手一辦的事幾乎要了別人全家的命。
鬱歡回了雲楓,時屹很忙,總是早出晚歸,每次都是鬱歡睡下後才能聽到窗外停車的靜。
不一會臥室的門就會被推開,腳步由遠及近,帶著清冽的夜的氣息,鬱歡閉著眼,生怕被他看出來。
時屹停在床邊,手了的臉蛋,待了片刻手又進了被窩向的小腹。
鬱歡眉頭蹙起,時屹的手很涼,帶著幾分薄繭,的很不舒服,於是往後了一下,幅度不大,但眼前人還是察覺到了。
他開口問:“還裝睡?”
鬱歡還是不做聲,眼睛閉,隻是整個子僵的厲害,保持著防姿勢。
眼前亮了幾分,時屹摁開了臺燈,接著是悉悉索索的服聲,鬱歡終於忍不住了:“別睡在我這裏。”
Advertisement
時屹解皮帶的作一頓,眼帶笑意看著:“舍得醒了?”
鬱歡側過不想看他:“被你吵醒了。”
時屹跪在床邊,捉住的小手放在自己皮帶上,聲音低沉厚重,迅速散在夜裏:“解開。”
可惜夜太重,看不到他眼眸中的。
鬱歡不肯,手用力往後,隻是被他死死扣著。
無奈的說:“我說了,不要睡在我這裏,你醒的那麽早,會把我吵醒的。”
時屹沒鬆手,反而抓著的指尖步步指引,皮帶終於鬆,他這才不不慢的說:“這是我家,連睡覺的自由都沒有?”
猜你喜歡
-
完結293 章

以歲月換你情長
她是寄人籬下的孤女,他是成熟內斂的商業奇才。 一場以利益為前提的婚姻,把兩人捆綁在一起。她不過是他裝門麵的工具,他卻成了她此生無法消除的烙印。 真相敗露,他用冷漠把她擋在千裏之外;極端報複,讓她遍體鱗傷。 她傷心欲絕想要逃離,卻意外懷孕;反複糾纏,他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互相傷害的死循環裏無法自拔。 四年後歸來,她不再是從前軟弱、備受欺淩的宋太太……
72.1萬字8 844570 -
完結528 章

離婚後我撿走霸總的崽
沒有生育能力的喬依被迫離婚,結束了四年的感情。心灰意冷之下去小縣城療養情傷,卻無意中拾得一個男嬰。出於私心,喬依留下孩子撫養。四年後,一排鋥亮的高級轎車停到喬依的樓下。顧策掏出一張卡:這是兩百萬,就當這四年來你撫養我兒子的酬勞。喬依把孩子護在身後:孩子是我的,我不可能和他分開!顧策邪魅一笑:那好,大的一起帶走!
80.3萬字8.09 95956 -
完結112 章

乖不如野
都說女追男隔層紗,秦詩覺得沈閱是金剛紗。明明那麼近,她怎麼也摸不到。 沈閱是秦詩的光,秦詩是沈閱的劫。 秦詩見到沈閱,就像貓見到了老鼠,說什麼也要抓到,吃掉。 原以爲是一見鍾情,後來沈閱才知道,他竟然只是一個影子。 他從未想過,他會成爲別人的替身。 那天,秦詩坐在橋上,面向滾滾長江水晃着兩條腿,回頭笑着對沈閱說:“我要是死了,你就自由了。我要是沒死,你跟我好,好不好?”
19.8萬字8 1325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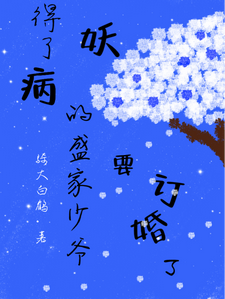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