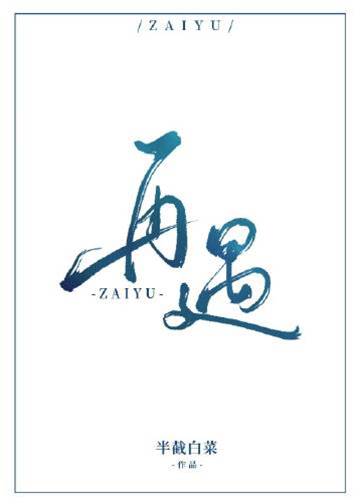《禍水》 第166章 和她結婚
梁璟坐得端莊筆直,正道,“我是我,你是你,攀扯我。”他紙巾完,站起來,“我吃飽了,先撤。”
“大哥,過來。”梁紀深吩咐慣下屬了,這句口吻半玩笑半吩咐,梁璟掃了他一眼,沒計較。
“梁副總,還有別的吩咐嗎。”
他正經了一些,“沒了,有勞大哥。”
梁璟離開后,梁紀深索徹底捅破,“您不僅指使胡大發的老婆誣陷,華寺的假和尚作偽證,也是您收買的吧。”
紀席蘭撂下筷子,“不是我。”
“不是?”他叩擊著桌沿,“除了您千方百計害,也有本事害,誰有膽量在我眼皮底下興風作浪?”
“我沒收買,我憑什麼承認?何況胡大發腦出,是下手太狠,我下手的?”
梁紀深只吸了半支煙,剩下的半支熄滅在煙灰缸,“總之,梁家的兒媳婦蹲大獄了,梁家的清譽毀了,我的前程也毀了。”
紀席蘭哼笑,“我會同意過門嗎?”
他靠著椅背沉默,越是沉默,越沒有轉圜的余地。
“延章!”紀席蘭慌神了,“你說話啊。”
梁延章端起酒杯,心中不滿,一抬頭,四目相撞,梁紀深翹起一條,角含著笑,笑不達眼底。
好半晌,雀無聲。
梁延章云里霧里的,老三的眼神實在深不可測,令他發怵了。
老三剛去中海上任那陣,比較低調蟄伏,現在一把手死了,百分百是二把手繼任,老三的行事風格沉穩老練,有大將之風,業界議論他的私生活,卻也服氣他的手段。
Advertisement
他羽翼漸,已經制不了他了。
梁延章又放下了酒杯。
紀席蘭莫名其妙,“延章?”
“行了。”梁紀深不耐煩,“我今天是通知你們,董事長的頭七之后,我領證,反對無效。”
“我碾死一個戲子易如反掌!”紀席蘭氣得滿面通紅,“老三,你掂量清楚!”
他淡笑,“您試試。”
紀席蘭一拍桌子,“我碾死又怎樣?我生養了你,你敢不孝不義嗎!”
“我的確不敢不孝不義。”男人神一寸寸崩塌下去,“您不要忘了,您是梁家的夫人,依附梁家才有好日子過,梁家盛,您風,梁家衰,您也狼狽。中海集團不如梁氏集團有錢,但勢力遠勝過梁氏,惹急了我,我斷了梁氏的財路。”
紀席蘭甩手要掄一掌,梁紀深紋不,打算挨這一下,梁延章關鍵時刻拽住,不允許爭執。
“延章,你什麼意思?是我撮合他們的,老三沒瞧上方安意,方家面掃地,我和方京儒夫婦沒法代!”
梁延章頭昏腦漲的,“我出面和方家解釋。”
紀席蘭不可置信瞪大眼,“你答應老三娶何桑了?”
他的初衷自然是不答應,可不答應,老三這勢頭,萬一真的讓梁氏集團坐了冷板凳,沒法和方家代倒無妨,他沒法和董事局代了。
梁延章沉著臉,不吭聲。
......
芳姐陪著梁璟一起回3號院。
是翁瓊雇傭的保姆,在老宅服侍四十年了,梁璟在國外時,任何風吹草是向助理通風報信。姚文姬和紀席蘭心知肚明是間諜,奈何是原配的人,不好解雇。
Advertisement
顯得沒度量,不敬原配。
反而招致流言蜚語。
一樓的客房門敞開,亮著一盞臺燈。
何桑睡姿恬靜,長發披散開,鋪了一枕頭。
梁璟轉,解開皮帶扣,在帽間取了一套居家服。
芳姐問,“我喊醒嗎?”
“不喊。”
“三公子的脾氣犟,梁董和紀席蘭拗不過他。紀席蘭添了一個平民百姓的兒媳婦,一定氣瘋了。”
梁璟隨口說,“沒那麼簡單。”
“再艱難,能有您艱難啊?夫人給我托夢了,說您不結婚清明節別去祭拜了,不愿見到您。”芳姐抱怨,“您爭爭氣,長孫或者長孫總不能他倆生在您前頭吧?”
“呱噪。”梁璟蹙眉,將芳姐擋在門外,反鎖,換服。
芳姐喋喋不休吵醒了隔壁的何桑,下床,走出臥室,梁璟也恰好出來。
“睡好了?”
點頭。
“不吐了嗎。”
何桑想起下午病殃殃的趴在梁紀深懷里,梁璟是正人君子,雖然不是刻意“膩膩歪歪”的,那副樣子終究失禮了,沒由來地尷尬,“我有暈車的病,沒大礙...”
梁璟觀察的氣是紅潤了不,“老三你過去。”
挪了挪腳,險些絆一個趔趄,扶墻穩住。
梁璟垂眸,3號院沒有士來過,芳姐來收拾衛生會自帶拖鞋,紀席蘭也識趣,在梁延章面前扮演寬厚溫的繼母,私下相很冷淡,從不登門,因此鞋架上只有男款拖鞋。何桑尺碼小,大抵是35—36.5碼,小的包子狀,穿他的43碼拖鞋,前后不著邊際,腳趾用力勾著,勉強不至于落。
Advertisement
他驀地笑了一聲,招呼芳姐,“你帶回去。”
何桑稀里糊涂被芳姐攙到玄關,扭頭,“你司機幫我開門的,他在書房,我什麼也沒。”
“嗯。”
梁璟開冰箱拿薄荷水,落地窗外種植著觀賞竹,大約有十幾株,季節已過,竹葉不及隆冬蒼翠了,也油綠綠的。他的居家服是墨綠,深刻又清爽的,和綠竹呈現平行線,如畫中。
何桑跟著芳姐進老宅,撲面而來的菜香味,胃口嘰里咕嚕的。
往餐廳里走,刺目的水晶燈照出凝重詭異的氣氛。
猜你喜歡
-
完結123 章

離婚?甭想了!
蘇棉被秦老爺子相中,嫁給了秦明遠,成為了豪門媳婦。 蘇棉漂亮溫柔賢惠,出得廳堂入得廚房,與秦明遠接受任何採訪永遠都是飽含愛意的目光,就連秦明遠的黑粉都被打動了。 #不會有人比嫂子更愛遠哥哥了!# 秦明遠對於包辦式婚姻的新婚妻子沒任何好感,處處挑剔,處處找碴,只想早日離婚。 然而,不到兩年,秦明遠漸漸習慣了溫柔的妻子,想要好好過日子了。未料就在這個時候,秦明遠發現了蘇棉畫了個以他們為原型的漫畫,溫柔賢惠的妻子真摯地吐露心聲。 “再過半年就報完恩了!可以結束這場婚姻了!” “媽蛋!豪門媳婦太他媽難當了!你這個渣渣!天天雞蛋裡挑骨頭!老娘不干了!” “影帝個屁,我演了兩年愛你的夫妻情深戲碼,你都不知道!” “嚶,和渣渣老公搭戲的流量小鮮肉好帥!我!可以!” 秦明遠:“不,你不可以。” 秦明遠:“離婚?甭想了!” #虐妻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內容標籤:豪門世家天之驕子業界精英甜文 搜索關鍵字:主角:蘇棉,秦明遠┃配角: ┃其它:接檔文《今天前妻也沒有找我複婚》
35萬字8.6 53793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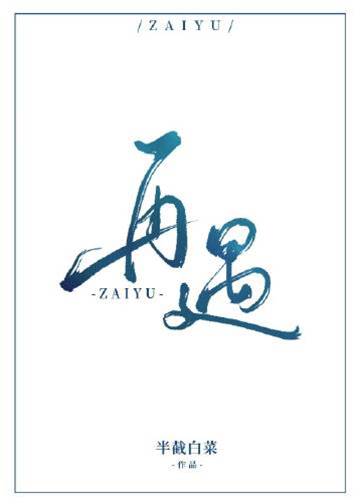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190 章

甜誘!傅爺的心尖寵她嬌又撩
【雙潔+暗戀成真+雙向奔赴+互撩甜爆】【嬌媚撩人大小姐x斯文敗類掌權者】 傅祁韞,倫敦金融界巨鱷,傅氏集團繼承人,無人染指的高嶺之花,禁欲寡情,不落俗套 可對宋大小姐來說,有挑戰性的獵物她只會更喜歡 小妖精跨坐到男人腰間肆意撩撥,纖指摩挲著薄唇,嗓音甜軟:“這里我蓋章了,你以后就是本小姐的人。” 他俯身靠向她耳畔,嗓音繾綣如愛人之間的纏綿低喃:“寶貝兒,我不是能隨便招惹的男人,撩了我,你就得對我負責。” - 不久,兩人結婚的消息傳遍帝都,所有人都認為這只是一場沒有感情的豪門聯姻 直到傅先生在畫展拍賣會上一擲千金,九十九億只為買下宋大小姐的一幅畫 面對記者的采訪,男人撫著腕骨上的曖昧咬痕,深邃清冷的眸子看向鏡頭,低醇嗓音誘哄著:“傅太太,我錯了,下次玩你喜歡的好不好?” - 他蓄謀已久,只為誘她沉溺 【男主戀愛腦,黏人精,白切黑隱藏病嬌,沒愛會死的瘋狗,占有欲超強】
25.2萬字8.18 116 -
完結448 章

野才帶勁
人生如戲,全靠演技。她本想做個安靜的女強人,殊不知一場愛情棋盤,自己被推上了風口浪尖的位置。契約婚姻,她視男人為游戲。卻不料,那個男人的出現,讓自己身心沉淪。直到那一夜,她成了他的女人。終于拋去滅絕師太的名號,她義無反顧選擇護愛。難得一見的溫柔,只為他留。
80.5萬字8 128 -
完結192 章

失算
暗戀成真/破鏡重圓 1、 江讓年少時恣肆散漫,浪蕩不羈,渾身散著股痞勁,蔫壞。身邊追求者趨之若鶩,想擇浪子心,卻從未見他對誰動過真心。 后來有人在舞蹈學院的薔薇花墻邊,看到他懷里摟著個女孩。女孩身穿芭蕾舞裙,柳腰細腿,如蝶翼的肩胛骨微收。 白色裙擺被風帶起,女
26.3萬字8 1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