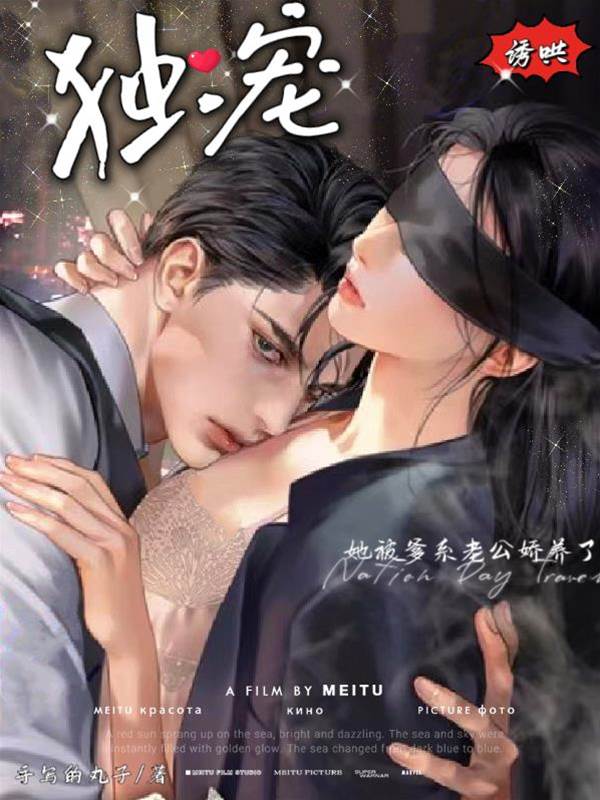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少帥輕點寵,鍾小姐吃軟不吃硬》 第110章 少帥吃醋,心煩意亂
鍾靈毓覺得,金棠並不是陳聽瀾的良配。
但鍾靈毓莫名不討厭他,反而有幾分微妙的親近。
這或許是因為,當初金棠幫了。
金棠大概是個好人,但不適合聽瀾。
飯桌上,鍾煜明跟鍾靈毓打聽陳家的態度。
鍾靈毓淡淡敷衍過去,“陳伯伯說,會力所能及幫襯著些。”
“那就好。”鍾煜明歎息一聲。
飯後,鍾靈毓上樓回了臥室。
去浴室洗了澡。
出來時,隻穿著浴袍。
係帶勾勒著纖的腰。
細膩的,被熱氣蒸騰得,泛著晶瑩剔的澤。
水珠沾了睫,眼眸愈發清湛。
剛來沒多久的沈懷洲,便看到這勾人一幕。
他朝手,“過來!”
鍾靈毓鎖好門,按滅了燈。
月暗淡,隻有零星波,從輕薄的簾子中進來。
他把拉坐在上。
作太大,腰間係帶鬆散,鍾靈毓香肩半,說不出的純。
沈懷洲抵著耳纏吻,嗓音模糊嘶啞,“今晚你去哪了?”
他這樣問,大概是知道的行蹤。
鍾靈毓能猜到,若去陳家,沈懷洲派來跟蹤的人,會向沈懷洲報告。
他們三四日沒見,他卻對的行蹤,了如指掌。
鍾靈毓心抑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要問?”
“鍾靈毓,我是不是太寵著你?”沈懷洲語氣有些危險。
鍾靈毓垂眸,清淡的語氣,帶著幾分漠然,“沈懷洲,你應該拿條鎖鏈,把我當狗一樣拴起來,這樣無論我去哪,你都不用再監視我。”
眉頭鎖,沈懷洲著的臉蛋,“跟我解釋一句,就這麽難?你不是沒進陳家,就隻和陳聽瀾說了話?”
“你什麽都知道,偏偏招我不痛快!”鍾靈毓微微別開臉。
“我不喜歡你去陳家,陳聽澤在那。所以該吃的醋,還是要吃的。”沈懷洲捧著的臉,低頭輕吻,“更何況,不痛快的人是我才對,我就問了那麽一句,你就跟我賭氣,不能好好解釋?”
Advertisement
“我答應你不跟陳聽澤接,既然做到了,我憑什麽浪費口舌跟你解釋?”鍾靈毓故意嗆他。
沈懷洲隨手從旁邊,拿出一份字帖,“那這個呢?這裏麵的字跡,跟陳聽澤的像。”
這是他方才爬窗進來時,無意中發現的。
因為他祖母很喜歡陳聽澤的書法,所以他一眼就認出來了。
他便想到,每每來鍾公館時,偶爾會看到,鍾靈毓描摹著字帖。
像是過字,在懷念人。
他早該想到,是陳聽澤。
沈懷洲心抑。
鍾靈毓淡聲道:“那是很早之前,陳聽澤給我的。”
“所以你的字,跟他的很像。”沈懷洲無比嫉妒。
他當著鍾靈毓的麵,把字帖撕碎了。
摻著黑字的雪白碎片,飄到半空,撒了一地。
鍾靈毓口起伏劇烈,忍不住生氣,“沈懷洲,你發什麽神經。”
沈懷洲不想任何與陳聽澤有關的東西,參與進鍾靈毓的生活。
包括陳聽瀾。
然而,他並不想幹涉鍾靈毓和友,這會徹底讓鍾靈毓惱了他。
他隻能把陳聽澤留下的痕跡,盡數毀掉。
沈懷洲很怕鍾靈毓對陳聽澤。
他拍了拍的腰,眼眸充斥著破壞,“陳聽澤還送了你什麽?”
“沒有...”
“靈毓,你要說實話。”沈懷洲眼眸深沉,“你知道,我什麽都能查出來。”
鍾靈毓子微,咬牙落了淚,“沈懷洲,為什麽你非得這樣?”
“聽話,把陳聽澤送你的東西給我,我替你丟掉。”沈懷洲沒有心。
他心中有鬱氣,急於發泄。
鍾靈毓深吸一口氣,攏了浴袍。
去書櫃裏,尋出陳聽澤送的字帖,還有...印章。
黑暗裏,沈懷洲視線清明。
過暗淡的燈,他看到印章上是雲素清的簡筆頭像。
Advertisement
印章,沈懷洲笑了聲,“陳聽澤倒是了解你的喜好,用這種東西討好你。”
鍾靈毓沒應,坐在床上抱著雙膝,子在發抖。
沈懷洲幾乎把印章握斷。
他拿著書和印章,從樓上一躍而下,吩咐李副,把這些東西,拿去燒了。
然後重新爬上窗戶,躺在鍾靈毓邊。
沈懷洲不帶任何,輕著的子,“你想要的,隻要我能辦得到,都可以給你,你不需要陳聽澤給的東西。”
說著,他從前的口袋,拿出一條項鏈。
他從背後擁著,把項鏈放在眼前,“瞧,你要的項鏈,我給你重新做了一條,不是要保存你母親的骨灰嗎?這個比之前的,還要堅固些。”
鍾靈毓盯那條項鏈,奪過後,狠狠砸到地上。
是比之前堅固,但狠摔了下,依舊有裂痕,盛不下雲素清的骨灰。
沈懷洲沉默。
鍾靈毓則甩開他的手,鑽進被子裏,拒絕他的。
這令沈懷洲惱火。
他燒了陳聽澤送的東西,所以把他送的,也毀了。
沈懷洲在鍾靈毓這裏,有種深深的自卑和無力。
他努力下了火氣,覆上的,繾綣研磨,“摔壞了沒關係,我再給你重新做一條。”
鍾靈毓冷落他。
把頭埋在被子裏,本不去看他。
沈懷洲用自己的方式討好。
無非是在床上那些折磨人的手段。
鍾靈毓暗恨自己的不爭氣。
明明厭惡他的偏執和霸道,偏偏在床上,總是被他牽著鼻子走。
趴在床上,額間滲出細的汗珠,烏黑的發,黏在額間,掌大的小臉滿是紅。
耳邊是沈懷洲重熱的呼吸。
他的大手按住的小腹,肆意侵占挲。
鍾靈毓眼裏溢出生理的淚水。
不住,聲道:“沈懷洲,我真的不行了...”
Advertisement
沈懷洲撥開額間的發,“舍得跟我說話了?”
“混賬!”
在床上,的罵聲蒼白無力,反倒勾得沈懷洲意迷。
他氣方剛的,如今隻有鍾靈毓一個人,又不常與見麵,難免失控。
事後,沈懷洲抱著去浴室清洗。
鍾靈毓連抬起手指的力氣都沒了。
全程都是由沈懷洲伺候著清洗。
兩人從浴室出來,相擁躺在床上。
的脊背,著他的膛。
沈懷洲喜歡這樣。
目所及是,懷裏有的溫度和香。
讓他很安心。
他摟,將臉埋在頸間。
這時,鍾靈毓突然問:“沈懷洲,你知不知道祥城金家?”
話落,莫名到沈懷洲僵了一下。
鍾靈毓轉頭盯著他,“你怎麽了?”
沈懷洲麵無異,著的麵頰,“怎麽突然問這個?”
“我今天去找聽瀾的時候,看到和金棠在一起。”鍾靈毓閉上眸子,“聽瀾說,金棠是祥城金家的子侄,祥城金家...是什麽樣的人家?”
“金家主要經營軍火生意,和各地軍閥政要,以及很多外國商人,都有千萬縷的關係。”沈懷洲在耳邊解釋。
他微微抬頭,盯著的側臉,“你這是在替陳聽瀾把關?”
鍾靈毓沒答,繼續問:“金棠呢?他是什麽樣的人?”
“我跟金棠接不多,不過他在祥城風評還不錯,沒什麽花邊緋聞。”沈懷洲把自己知道的,盡數告訴鍾靈毓,“不過有一件事,鬧得比較大。”
“什麽?”
“金棠被他大伯父養大,他大伯父,就是如今金家的家主,已經替金棠看好一位妻子。但金棠沒同意這門婚事,便離家出走。”
頓了頓,沈懷洲輕笑,“沒想到,金棠竟然跑到祥城,和陳聽瀾勾搭在一起。”
Advertisement
鍾靈毓微怒,“沈懷洲,我不允許你這麽說我朋友。”
沈懷洲親了親的麵頰,及時道了歉。
等鍾靈毓不計較了,他提醒道:“金家背景複雜,金棠不適合陳聽瀾。”
不論什麽家世背景,鍾靈毓也覺得金棠並不可靠。
聽瀾單純善良,金棠一看就很明。
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明麵上看,金棠似乎被聽瀾迷得難以自持。
實際上,主導權一直在金棠手上。
聽瀾像個乖巧的兔子,被金棠牢牢掌控。
一旦他們出現問題,重傷的,肯定是陳聽瀾。
鍾靈毓並不想陳聽瀾所托非人。
況且,金家還是軍火商...
聽起來就很危險。
鍾靈毓打算找時間,跟陳聽瀾說一說金棠逃婚離家的事。
闔上眸,漸漸睡過去。
沈懷洲卻沒了睡意。
他眉宇染上愁意。
其實,他沒說的是,近來,沈家和金家也接頻繁。
金家似有扶持一方軍閥,進而吞並沈家的打算。
靠倒賣軍火發家的金家,有著充盈先進的武庫。
若金家投靠沈家的敵人,那雲城便岌岌可危。
他父親沈大帥,親自去和談。
金家提出條件,就是要和沈家聯姻。
雙方互惠互利。
沈家為金家在其他生意上提供便利,金家為沈家提供先進的武。
而沈家適婚男人,隻有他,以及他繼母生的弟弟。
然而,他那不的弟弟,金家無論如何都瞧不上。
聯姻的事,便落到沈懷洲的頭上。
沈懷洲心煩意。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許你一生空歡喜
"婚後老公卻從不碰我,那我肚子裏的孩子是誰的?出軌捉奸被趕出家門…… 九死一生後,我被逼成為老公上司的情人,孕母。 本以為隻是一場金錢交易,我不想動心動情,可我卻在他忽冷忽熱的溫柔裏,失了身,陷了情。 一場情劫過後,縱身火海,再見麵,我又該如何麵對?"
21萬字8 14587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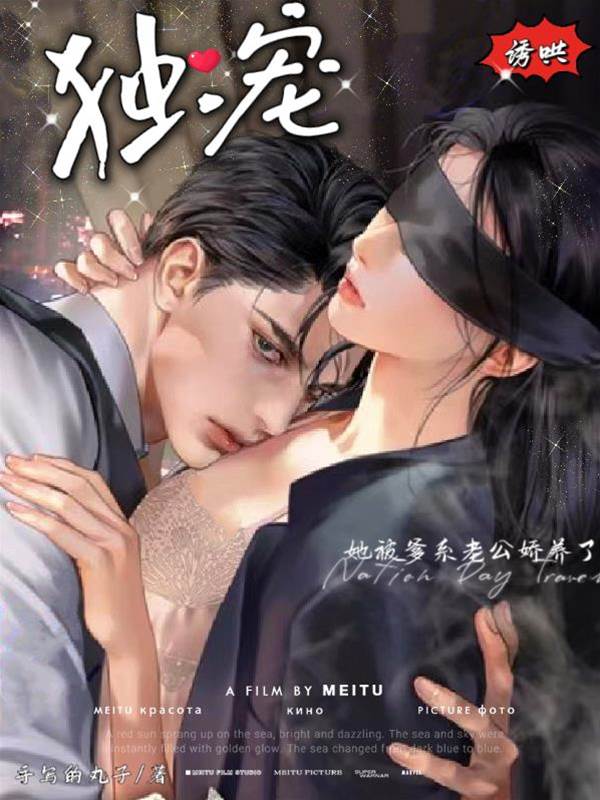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2612 -
完結182 章

嬌惹!他又野又撩,卻為我折腰
[風情萬種釣系畫家X離經叛道野痞刺青師][SC|甜欲|頂級拉扯|雙向救贖] - 只身前往西藏的第一天,宋時微的車壞在了路上。 她隨手攔下了一輛車,認識了那個痞里痞氣的男人。 晚上在民宿,宋時微被江見津的胸肌腹肌迷得五迷三道。 她溜進他的房間,將他堵在了墻角,問他:“江見津,zuo|嗎?” - 川藏南線全程2412公里,從成都到拉薩,途徑22個地點,走走停停耗時五個月整。 這五個月里,宋時微跟江見津成了飯搭子、酒搭子,還有chuang|搭子。 在拉薩逗留了半個月后,宋時微賣掉了車子準備飛機回北京。 江見津神色淡漠,只問她:“都要分手了,最后一次也沒有?” 宋時微撓了撓下巴,回:“這個倒也是可以有。” - 重逢是在一年后。 療好傷的宋時微一鳴驚人,新作品一舉拿下英國BP肖像獎的一等獎,并于同年年底在國內舉辦了首場個人畫展。 慶功宴上她見到了本次畫展最大的贊助商,那個傳說中的商界奇才。 包廂門推開,她看到的是西裝革履的江見津。 他起身跟她握手,似笑非笑地問她:“宋小姐在畫畫之前不需要征得本人的同意嗎?”
24.6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