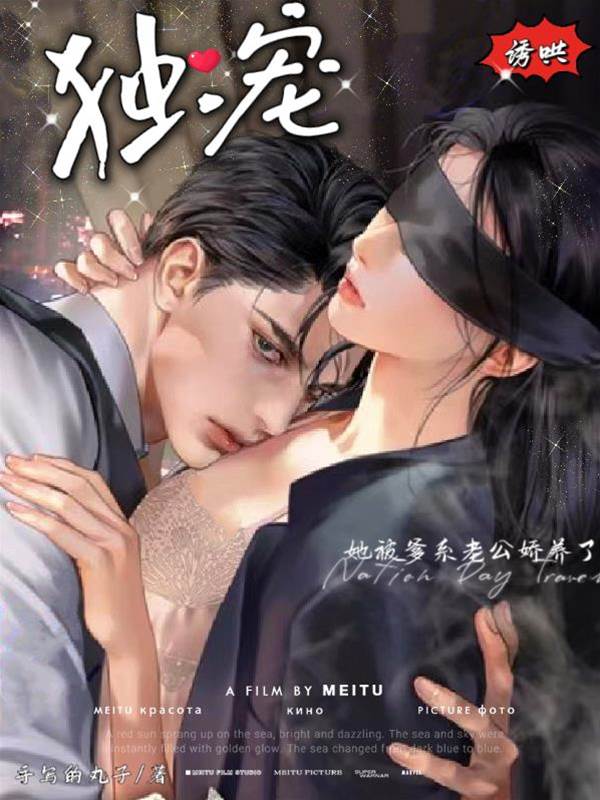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靳少,吻安》 第289章 你碰她沒有?【三千字】
許簡一忽然昏倒。
靳寒舟急得跟無頭蒼蠅似的,把人抱到副駕,安全帶係上,急忙開著車去了附近的醫院。
他的緒很躁,進醫院的時候,幾乎是大吼大的,“醫生!醫生在哪!”
夜裏醫院冷清清的。
不喊,你連醫生的影子都找不到。
護士聽到喊,從值班室裏走了出來。
護士讓靳寒舟將許簡一放到急診室的病床上。
醫生過來了解況。
見許簡一是發燒引發的昏迷,醫生立即給進行退燒治療。
退燒期間,靳寒舟一直握著許簡一的手,裏叭叭個不停。
顧西玨在一旁看著,滿是心疼和憤怒。
心疼許簡一發著高燒還要出來找尋歡作樂的丈夫。
憤怒靳寒舟大半夜不在家陪許簡一,跑出來玩樂。
顧西玨憤恨地指責靳寒舟,“為了給你生那三個孩子,孕期手腳腫得跟豬蹄似的,剖腹產大出昏迷了兩日才醒來,你他媽就是這樣回報的?”
顧西玨恨啊。
恨靳寒舟在福中不知福,有了許簡一這樣用命在他的人,還要出來尋歡作樂。
要是他……
他不得在家摟著老婆孩子熱炕頭。
靳寒舟驀地看向顧西玨,“你說什麽?”
“說你不知福!”顧西玨低吼,“你以為三胞胎那麽好生的麽?那是簡簡用命拚來的!你這輩子不把寵上天,你都對不起那個在鬼門關走了一遭,讓你一下子兒雙全的人!”
正常人懷三胞胎都辛苦,而許簡一卻在生病不能自理的況下懷的三胞胎,的辛苦,除了照看的伊諾,便隻有顧西玨知道了。
其實醫生一開始是建議減胎的。
三胎不是那麽好生的,而許簡一又是這麽一個況。
但是許簡一聽到醫生的話,就開始抗拒別人靠近,會抬手拍打靠近的人。
Advertisement
顧西玨明白許簡一這是不給人孩子做出的自我保護行為。
顧西玨本就沒有權利決定許簡一孩子去留,何況許簡一還做出自我保護的舉。
所以孩子最終沒有減,正常生。
正常人懷一個孩子都辛苦得不行了,更別說許簡一懷三個了。
整個孕後期,許簡一幾乎都在病床上度過。
因為要保胎。
靳寒舟沒有參與許簡一的孕期旅程,又怎知許簡一的孕期有多辛苦呢?
如今聽顧西玨提及,靳寒舟看向病床上的許簡一,滿滿都是心疼。
他握住許簡一的手,不斷地親吻,那心疼的勁兒恨不得代過一般。
靳寒舟裏一直碎碎念著各種心疼的話,語速極快,一句接一句,有點像渣男做錯事悔悟痛改前非跟妻子保證以後對好的既視。
顧西玨看著這樣的靳寒舟,頓時不知該說什麽好。
“好好對!”
顧西玨丟下這麽一句話,就走了。
份的尷尬到底是讓顧西玨沒有太多立場去指責靳寒舟尋歡作樂的行為。
他除了把人揍一頓為許簡一出出氣,什麽都做不了。
至於許簡一要如何理這件事,顧西玨沒法幹涉。
靳寒舟沒有理會顧西玨,他一邊親吻許簡一的手背,一邊不停地說著心疼辛苦的話。
許簡一就是在靳寒舟的碎碎念中醒來的。
歪頭看著床邊握著的手不停叨叨的靳寒舟,想起前麵看到的那一幕,許簡一心頭像是被帶刺的玫瑰打了一下,啟,嘶啞地問,“你了嗎?”
聽到許簡一聲音的靳寒舟滿是激地看向,“寶寶,你醒啦?”
他指腹輕臉頰,滿眼心疼,“是不是很難?”
許簡一沒有回答靳寒舟的問題,而是執拗地問他,“你沒有?”
Advertisement
“誰?”靳寒舟麵茫然。
“剛剛那個人,你了嗎?”
許簡一有點幹,無意識地了。
靳寒舟看到後,立馬起給倒了杯水攤涼。
他倒水的時候,解釋說,“是自己撞上來的,我沒。”
靳寒舟以為許簡一問的是剛剛服務員撞他懷裏的時候,他有沒有服務。
許簡一微微一愣,“自己撞上來?”
“有個不當人的畜生發酒瘋對耍流氓,我出手製止,就跑來跟我謝,然後就被人撞了一下,撞我上了。”
靳寒舟邊說邊吹杯中的開水,試圖將其盡快弄涼,好給許簡一水喝。
聽完靳寒舟的話後,許簡一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
那一瞬間,許簡一有種在口的巨石被搬離的輕快。
幸好……
得知靳寒舟並沒有做出背叛他們的事,許簡一麵上不自覺地流出慶幸。
許簡一無比慶幸靳寒舟沒有弄髒他們的。
許簡一從來都不是大度的人,當時能容忍靳寒舟心裏有‘別人’,無非是不夠,加上後期自我催眠,把靳寒舟當治療失眠的良藥,所以不在意他心裏誰。
但現在的許簡一容不得一粒沙子,無法接靳寒舟跟任何人親昵,有潔癖。
像是反應過來了什麽一般,靳寒舟忽然生氣地瞪著許簡一,“你以為我跟有什麽?你把我當什麽人了?”
這個話題多有點敏,許簡一不想刺激靳寒舟,省得他跟白天一樣,發脾氣把也給臭罵一頓,許簡一直接先發製人,“你大晚上不睡覺,去會所幹嘛?”
靳寒舟注意力被轉移,立馬又不生氣了,“睡不著,出來找點樂子打發時間。”
“哦。”隻要不是找人,許簡一不至於連玩樂都不給靳寒舟玩,隻是靳寒舟現在這個況,許簡一還是不放心他單獨待在外麵,“以後出去跟我說一聲,我醒來找不到你,很擔心。”
Advertisement
“好。”水溫了,靳寒舟扶許簡一坐起來喂喝水。
許簡一喝了幾口,就不想喝了。
發燒讓許簡一十分疲倦,眼皮止不住地往下闔。
眼睛快要合上時,像是想到了什麽,許簡一一把抓住靳寒舟的手。
“你也上來睡一下。”
許簡一仔細想了想,才忽然發覺靳寒舟沒怎麽睡覺。
“我不困。”
靳寒舟確實不困,還有就是他不敢和許簡一在一起,許簡一上那香一飄過來,他就上頭。
靳寒舟怕自己忍不住……
不跟許簡一在一起的時候,靳寒舟還可以借著其他事消耗過於旺盛的力,但一和許簡一挨一起,靳寒舟就能立馬躁。
許簡一拉他,“不困也上來閉眼躺一下,你一天到晚都沒怎麽沾過床,一直不睡覺,會不了的。”
怕自己態度顯得太強,許簡一者聲,帶著幾分輕哄道,“睡下好不好,你不睡,我也沒法安心睡了。”
靳寒舟可以不惜自己的,但他不能讓許簡一休息不好。
靳寒舟糾不過許簡一,躺到了旁。
兩個人在一米二的病床上,特別的狹窄,靳寒舟怕許簡一摔下去,把那邊的圍欄拉了上來,然後手環住的腰,雙重固定。
許簡一側過去環住靳寒舟的腰,把臉在他口上,輕輕呢喃,“靳寒舟,不可以找別人……”
曾經的許簡一無比自信靳寒舟不會背叛,因為能得到他那幾乎溢滿而出的意。
但現在的許簡一有時候幾乎覺不到靳寒舟的意。
靳寒舟的意好像從他說他不許簡一的時候,就徹底收回去了。
他不再和以前那般將許簡一捧於心尖,甚至在房事上,也不再注重許簡一的。
他明知道做那麽多次,許簡一的已經不堪他摧殘,但他還是被支配,試圖哄著給他。
Advertisement
許簡一今晚為什麽會忽然不耐煩。
正是因為曾在之前的房事上,多次跟靳寒舟提及自己不舒服,讓他快點結束,但靳寒舟隻顧自己發泄,哄著便繼續。
一次兩次,許簡一還可以看在他生病的份上,包容他,慣著他。
隻是人到底不是鐵打的。
人的緒崩潰,其實隻在一瞬間。
晚上靳寒舟求歡那會兒,許簡一其實已經有發燒的跡象了。
可靳寒舟沒有察覺。
又或者說他當時察覺到許簡一的溫有點偏高,但他並不在意,他隻想和許簡一做。
的不適,以及靳寒舟的‘不’,讓許簡一忍的緒,一下子發了出來,所以說了不耐煩的話。
與其說是不耐煩的話,不如說是許簡一在另類的發泄委屈。
許簡一曾過靳寒舟百分的意,麵對靳寒舟如今隻有百分之五十,甚至可能百分之五十都不到的意,心裏又怎麽可能會沒落差。
靳寒舟並沒有聽到許簡一的呢喃。
他在許簡一抱上來的時候,本就沒有得到滿足的瞬間開始躁了,他腦海裏,全是那檔事兒。
沒有去注意聽許簡一到底說了什麽。
快要睡過去的許簡一覺有什麽東西頂著自己,腦子裏迷糊了一下,隨後反應過來是怎麽回事後。
無奈地歎息。
在得知靳寒舟不停想做是因為原因,許簡一到底是心疼他的。
哪怕自己很困很累,許簡一還是把手了過去,“弄完趕睡覺。”
“嗯……”
靳寒舟裏地悶哼著。
自己手總歸是沒有許簡一手要來得舒爽。
何況許簡一手是熱的。
那個滋味,也隻有靳寒舟才能會有多銷魂。
在許簡一的幫助下,靳寒舟出來的要比自己時快多了。
發泄過一次,靳寒舟的就沒有那麽旺盛了。
漸漸的,人也開始有了點困意。
靜謐的病房裏,一米二的病床上。
夫妻麵對麵躺著,許簡一摟著靳寒舟的腰,靳寒舟摟著的背,一個臉對方膛,一個下磕著對方頭頂,就那樣安靜祥和地睡著。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許你一生空歡喜
"婚後老公卻從不碰我,那我肚子裏的孩子是誰的?出軌捉奸被趕出家門…… 九死一生後,我被逼成為老公上司的情人,孕母。 本以為隻是一場金錢交易,我不想動心動情,可我卻在他忽冷忽熱的溫柔裏,失了身,陷了情。 一場情劫過後,縱身火海,再見麵,我又該如何麵對?"
21萬字8 14587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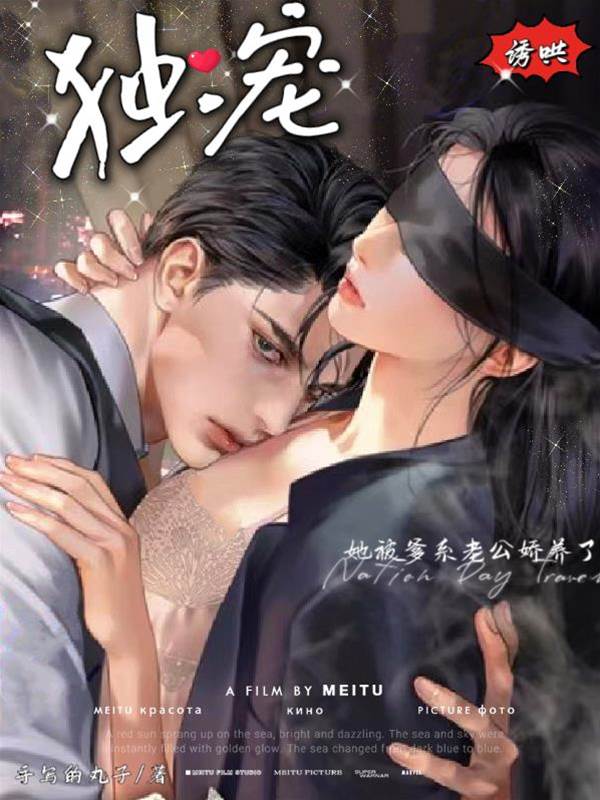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2612 -
完結182 章

嬌惹!他又野又撩,卻為我折腰
[風情萬種釣系畫家X離經叛道野痞刺青師][SC|甜欲|頂級拉扯|雙向救贖] - 只身前往西藏的第一天,宋時微的車壞在了路上。 她隨手攔下了一輛車,認識了那個痞里痞氣的男人。 晚上在民宿,宋時微被江見津的胸肌腹肌迷得五迷三道。 她溜進他的房間,將他堵在了墻角,問他:“江見津,zuo|嗎?” - 川藏南線全程2412公里,從成都到拉薩,途徑22個地點,走走停停耗時五個月整。 這五個月里,宋時微跟江見津成了飯搭子、酒搭子,還有chuang|搭子。 在拉薩逗留了半個月后,宋時微賣掉了車子準備飛機回北京。 江見津神色淡漠,只問她:“都要分手了,最后一次也沒有?” 宋時微撓了撓下巴,回:“這個倒也是可以有。” - 重逢是在一年后。 療好傷的宋時微一鳴驚人,新作品一舉拿下英國BP肖像獎的一等獎,并于同年年底在國內舉辦了首場個人畫展。 慶功宴上她見到了本次畫展最大的贊助商,那個傳說中的商界奇才。 包廂門推開,她看到的是西裝革履的江見津。 他起身跟她握手,似笑非笑地問她:“宋小姐在畫畫之前不需要征得本人的同意嗎?”
24.6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