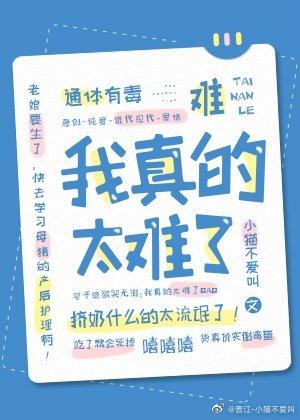《乖,別怕我》 第54頁
方澤勾起角,“所以我說是人機。”
“關鍵是俞寒……他怎麼會來?他可是年級第一。”
方澤眼底閃過不屑,“辯論賽和績有關嗎?這里又不是考場,本就沒有他施展拳腳的地方。”
在他們四個專業、參加過許多比賽的人面前,沒有可比。
而無懼隊離開,王樹澤氣得跳腳,“臥槽他們嘚瑟個屁啊,等會兒還不是要被我們往死里!”
袁家笑了,“黑炭,我發覺你有的時候還樂觀啊。”
“我就是看不慣他們臭嘚瑟那樣,搞得誰沒張似的,就他整天叭叭叭的。”
貝盈盈也被他逗笑了,原本張的氛圍頓時消散。
俞寒輕扯角,“你只要正常發揮你平時吵架的水平,我們就贏了。”
“那必須的啊……”
他們走進教室,里頭已經開始進行做準備工作了,他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貝盈盈對俞寒說:“我先去上趟洗手間呀。”
走出教室,卻沒想到剛好撞上貝疏等一群人。
怔住。
貝疏今天不是沒有比賽嗎?
貝疏看到妹妹,莞爾一笑,對旁的人說先進去,而后追上貝盈盈的步伐,住了。
“沒想到這麼快就到你比賽了,哦對了,媽媽讓我和你說,讓你放輕松,不要太當真。”
畢竟也就是場結局注定的比賽而已。
貝盈盈開口:“所以你今天來看比賽也是媽媽你來的?”
“那倒不是,只是我和無懼隊的員都是好朋友,剛好就過來看看他們比賽,怎麼了,我在這看你比賽,你很介意?”
Advertisement
貝疏仰著潔的下,笑得單純又好,只是眼底的那抹涼薄之意只有貝盈盈看得到。
貝盈盈攥出汗的手心,視線卻突然瞥到朝走來的俞寒。
貝疏順著的視線,看到走近的男生,心頭一震。
對上俞寒的目,本以為俞寒要找,誰知只見他走到貝盈盈面前,抬手輕輕蓋住的后腦勺,帶著離開,目毫沒有落在貝疏上,聲音是從未聽過的溫——
“傻乎乎的又站在這閑聊?馬上開始了。”
看著兩人離開,貝疏還未從怔愣中回過神來。
剛才俞寒竟然對貝盈盈是那種態度?!
這怎麼可能!
俞寒對那麼冷漠決絕,憑什麼對貝盈盈就像變了個人一樣。
貝疏覺又一束藤蔓纏繞著的心,讓覺不過氣來,握拳頭,眼底閃過一道狠。
-
俞寒沒有帶去教室,而是走到無人的走廊。夜晚的天空黑漆漆的,耳邊回著是樹上不曾斷絕的蟲鳴聲。
他單手撐著走廊的欄桿,側把背靠欄桿的孩半圈在懷里,聲線一如往日的低沉淡漠:
“看到,又開始張了?”
貝盈盈不想承認,只能垂著腦袋,一言不發。
“還好今天在臺下,否則要是在你對面,你不是連話都說不利索了?”他打趣。
貝盈盈聞言皺眉,小聲嘀咕:“我也不至于這麼慫……”
男生勾,看著外頭的夜,“其實看到你,該張的是。”
Advertisement
他垂頭,“現在一切的主權都在你這里,是做錯了事,對不起你。”
那一個最大的把柄,現在正握在貝盈盈的手中。
孩只要想到當初痛苦的經歷,心頭又燃起了斗志,點點頭,“嗯,我會調整過來的。”
幾秒后,他突然出聲問:“最近有沒有想做的事?”
“啊?”
“比如看電影,去游樂場等等,”他移開視線,語氣故作淡定,“你要是想,這個周末可以一起。”
貝盈盈發愣,“就……我們兩個?”
“是我們隊四個人一起,這次辯論賽結束后,大家可以放松一下,袁家說地點你來定。”
孩想了會兒,腦袋一歪,期待地看著他:“去案嶺古城怎麼樣?這里這麼出名的地方我都沒去過。”案嶺古城是T市的旅游勝地,地區金名片,很小的時候被家里人帶著去過一次。
“行,那就好好比賽。”
-
臨近比賽開始,兩支隊伍就座,他們相對而坐,中間是演講臺和后面的評委席,因為只是場初賽,所以來看比賽的人寥寥無幾,唯獨有那麼七八個個,還全都是無懼隊的親友團。
這種覺,就像足球比賽場上,滿滿的觀眾席都坐著支持東道主的球迷,東道主一拿分,全場響起沸騰聲,對于另一方隊伍來說是神上力巨大。
袁家低聲音問王樹澤:“咱們怎麼也不幾個人來啊?!也太沒氣勢了!”
Advertisement
王樹澤晲他:“個屁,隨便比比就完事了。”他好歹在大家心目中也是高二年段有頭有臉的富二代好不好!要是輸了,面子往哪擱……
誰知他話音剛落,門口就走進來好幾撥人,其中一個扎著丸子頭、濃眉大眼的萌妹看到王樹澤,彎起角,開心地朝他揮了揮手,用口型說道:“樹澤加油~”
王樹澤看著帶著姐妹欣喜地座觀眾席,腦袋轟隆一聲。
炸了炸了!
王樹澤立馬抬頭,猛扯著袁家的手臂:“你他媽快幫我看看,我服穿得整不整齊,頭發不?”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06 章

提出離婚後,隱婚大佬他慌了
【傅零珩*黎斐】【清醒獨立藝術家VS禁欲係大佬】【前期稍虐】他們兩個人的婚姻,本就是長輩施壓促成。隱婚三年,有名無實。對外,她是圈內知名藝術家,備受廣大粉絲喜愛。對內,她是溫婉得體的豪門太太,隨時配合他扮演恩愛小夫妻。“我們離婚吧!”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臉色依舊平靜無波,整個包間頓時安靜了下來。“你說什麼?”傅零珩臉上的表情瞬間凝固,原本還帶笑的雙眸立即跟著冷了下來,周身散發出駭人的寒意。“我說,我們離婚吧!”她再次重申,這句話她醞釀了很久,終於說出口了......當親眼見她與別的男人站在一起時,向來沉穩如斯的冷傲男人終是坐不住了,他不管不顧拽著她的腕骨,指腹摩挲著她的耳廓低聲沙啞祈求她:“黎斐,我輸了,你回來好不好?”
44.7萬字8 52348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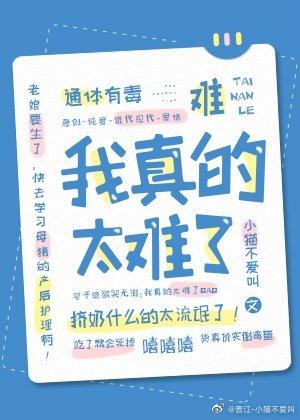
坑過我的都跪著求我做個人
容子隱是個貨真價實的倒黴蛋。父母雙亡,親戚極品,好不容易從村裏考出來成為大學生,卻在大學畢業的時候路被狗朋友欺騙背上了二十萬的欠債。最後走投無路回到村裏種地。迷之因為運氣太差得到天道補償——天道:你觸碰的第一樣物品將會決定你金手指方向所在,跟隨系統指引,你將成為該行業獨領風騷的技術大神。容子隱默默的看了一眼自己手邊即將生産的母豬:……一分鐘後,容子隱發現自己周圍的世界變了,不管是什麽,只要和農業畜牧業有關,該生物頭頂就飄滿了彈幕。母豬:老娘要生了,快去學習母豬的産後護理啊!奶牛:擠奶什麽的太流氓了!最坑爹的還是稻田裏那些據說是最新品種的水稻,它們全體都在說一句話:通體有毒,吃了就會死掉嘻嘻嘻。容子隱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後來,那些曾經坑過容子隱的人比容子隱還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求你做個人吧!1v1,主受,開口就一針見血豁達受vs會撩還浪甜心攻注:1,本文架空!架空!架空!請不要帶入現實!!!文中三觀不代表作者三觀,作者玻璃心神經質,故意找茬我會掏出祖傳表情包糊你。2,非行業文!!!任何涉及各個行業內容,請當我杜撰!!!別再說我不刻意強調了,寶貝們~請睜大你們的卡姿蘭大眼睛好好看看我備注裏的感嘆號好嗎?內容標簽: 種田文 美食 現代架空 爽文搜索關鍵字:主角:容子隱 ┃ 配角:季暑 ┃ 其它:一句話簡介:我真的太難了
32萬字8 870 -
完結234 章

哥哥們的小奶團成了滿級大佬
三個小男孩在孤兒院門口撿到小奶團子唐曦,從此以后…… 性情冷漠,從不喜歡小孩子的大哥葉沐深:“妞妞,哥哥得的獎學金,給你買的小裙子,讓哥哥親一下。“ 看見蟲子都嚇得尖叫的二哥蘇哲:“妞妞,看,這些螢火蟲像不像你夢里的星光?二哥給你抓的,讓哥哥抱抱好不好?“ 小痞子三哥林驍:“欺負我妹妹的,都給我站出來,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分開多年后,三個哥哥再次見到唐曦,還想像以前一樣,抱抱,親親,舉高高,可是,他們卻發現,他們心中那個軟萌小奶團子,居然變成了性情冷漠的滿極大佬。 拿過無數次醫學大獎的二哥:“藍星基因研究院院長,那是我妹妹!” 頂流巨星三哥:“國際著名編曲Eva,那是我家妞妞!”
43.1萬字8 140 -
完結214 章

我在豪門天天摸魚
阮青舒本以為和傅瑾修只是一場三年協議婚姻。結婚第二年傅瑾修的白月光強勢回歸,阮青舒帶著離婚協議找到傅瑾修要離婚。 傅瑾修面無表情說,“離婚可以,先交一個億的毀約金。”
38.3萬字8 1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