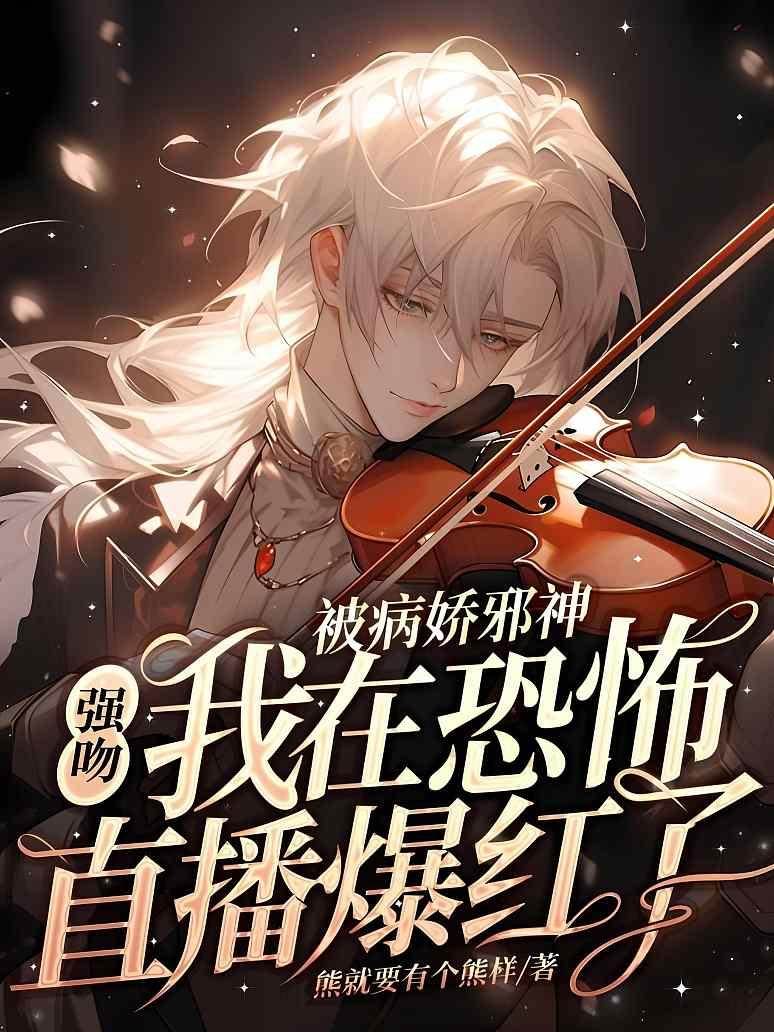《廢墟有神明》 第26章 能去你家坐坐?
狐疑歸狐疑,相比傅司九的住,馮蕪的玫瑰苑離這家會所確實近很多。
何況,還有小路可以繞。
想著今天得罪過他,馮蕪沒敢嗆聲,默默發了條導航給他,叮囑道:“你從這條小路穿過來,十分鍾就能到,我下去等你。”
“不用,”無人知曉的角落,傅司九笑的多,“我到了給你電話。”
馮蕪:“也行。”
小區一個挨著一個,臨湊的房屋高矮不一,路燈被漸漸茂的樹葉過濾掉明亮的,細雨遮天蔽日,積了水的地麵折出影綽斑駁的弱。
傅司九很小就被送來了珠城,大概七八歲的樣子。
傅家有生意在這邊,也有至親早年移居過來,他子桀驁不羈,不拘住哪裏都行。
大哥大姐覺得對不起他,這邊至親拿他當命子,邊朋友恭維忍讓,幾個發小也經常怕他孤單,三不五時就把他約到自己家吃飯留宿。
傅司九是被捧著長大的。
喧嘩的熱鬧中,他一大男人沒有過細的心思,更不會傷春悲秋。
可就在這個夜晚,他出門聞見春天的氣息,看見天上地下的。
他突然,有了一微妙的悸。
他想馮蕪。
想看見。
想跟說說話。
那被熱鬧灌滿的心髒,驟然出一個明顯的,這荒蕪,讓傅司九想起“思念”兩個字。
他輕嗤自己矯。
-
到玫瑰苑時,隔著絨針般的雨簾,傅司九遠遠瞧見站在樓道裏躲雨的孩子,穿著珍珠白睡,外麵披了件黑外套,一隻手拿了把傘,正盯著大門的方向瞧。
Advertisement
傅司九鋒利的眉皺了皺,加快步子走到樓道裏,低斥道:“不是說了,我到了你再下來?”
“沒關係,”馮蕪打量他,“你服都淋了,春捂秋凍,春天要保暖的。”
睡前才洗過頭發,一頭半長不短的發略微淩地披在肩後,包裹住掌的一張臉。
樓道寂靜,有灰塵腐朽的味道,應燈時亮時滅,說話時有輕輕的回聲。
傅司九了把腦袋,眼睛在黑暗裏灼灼:“你自己凍著了怎麽辦?”
“不會的,”馮蕪把傘遞給他,“我開車送你回。”
“......”傅司九心尖燙得不行,嗓音越發了,“不用,打擾你休息。”
細雨沙沙,像深夜的蠶在啃食桑葉。
馮蕪高隻到他肩膀,仰頭時,又俏又可人。
晃晃車鑰匙:“你是不是因為說話太欠,被行添哥他們趕出來了?”
“......”傅司九差點氣笑了,“你是吃了什麽熊心豹膽,居然敢頂了?”
馮蕪腮幫子微鼓。
這段時間的接,發現傅司九也沒那麽可怕。
跟他開玩笑,打趣他幾句,他都跟哄小孩似的,最多罵罵就過了。
要真算起來,相比於他的罵,他對自己的好才更明顯。
馮蕪:“那你要不要送,不要我就幫你車。”
傅司九,冷不防問:“能去你家坐坐?”
“不能,”馮蕪很直接,“的跟狗窩一樣,我沒打掃,不許你去。”
Advertisement
“......”
以為要說什麽“深更半夜”、“孤男寡”之類推拒的話。
傅司九膛輕振,笑息淺淺,嗓音溫的跟細雨一般:“你還能再直接點?”
“這段時間忙,”馮蕪好脾氣道,“我自己住無所謂的。”
很舒服,很自由,想擺爛就擺爛,就是不適合接待客人。
除了樓道裏的腐朽味,傅司九還聞到了空氣中的雨水和泥土腥氣,但在這些複雜的味道中,他敏的捕捉到一縷花香。
這花香很淡很淡,完全踩在了他的嗅覺點上。
就這麽一點香味,放大了他所有,讓他流連忘返。
同樣的香水用在不同人上,釋放出來的味道卻不盡相同,而馮蕪上的味道,完全擊中了傅司九的心髒。
他彎下腰,與視線齊平,佯裝不經意把距離拉近,低低的嗓音:“香水用了?”
“......”馮蕪又開始聞袖子,“這味很重嗎,怎麽你們都能聞到。”
傅司九:“還有誰?”
“小桃啊,”馮蕪嘀咕,“我自己就聞不見。”
沉思數秒,訕訕抬睫,小心問:“你朋友是不是告白失敗了,所以把香水丟給了你?”
“......”傅司九頓了頓,玩味地問,“怎麽?”
“如果是這樣的話,”馮蕪覷他,實話實說,“我沒噴香水哦,甜品店工作不能用香水,會影響食和客人的覺,我就...拿來熏房子了。”
Advertisement
“......”
馮蕪:“既然是你朋友不要的,那我噴廁所也可以的吧。”
傅司九額角。
他抿抿,憋了句:“可以,想噴哪就噴哪。”
馮蕪眼瞼彎出臥蠶,笑起來不知不覺的甜。
傅司九跟著笑,借著樓道外映進來的,很想把摁進懷裏。
“我送你回家,”馮蕪細聲細氣,“你是不是喝多了?”
聞到了酒味。
傅司九不置可否,定定看了一會,磁沉的聲音問:“你對誰都這樣?”
不管是誰,深更半夜來找借傘,都會熱的送對方回家?
馮蕪眼睫抬上幾分,出黑白分明的瞳仁:“不會啊,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
“......”傅司九頓了下,“我對你好嗎?”
馮蕪歪歪腦袋,鬢邊碎發彎括弧,的模樣:“我媽媽走後,無條件對我好的人,隻有九哥一個。”
傅司九與的關係,沒有緣、法律和自長大的分在。
他完全可以不對好。
畢竟,他們之前連朋友都算不上。
傅司九心口梗住。
他才不是。
不是無條件的。
他想要。
一切的接近,都是蓄謀已久。
“其實有條件也沒關係,”馮蕪齒間含糊道,“我沒什麽可回報你,幫你做點力所能及的事。”
一句話落,無形中仿佛有盆冰水,兜頭澆了下來。
傅司九從腳底涼到了頭發。
他瞳底下意識涼了,嗓子被磋磨過似的,喑啞著:“你對許星池,就是這樣?”
猜你喜歡
-
完結891 章
顧少,你老婆又帶娃跑了
在雲城,無人敢惹第一權貴顧遇年,關於他的傳聞數不勝數。陌念攥著手裡剛拿的結婚證,看著面前英俊儒雅的男人。她憂心道:“他們說你花心?”顧遇年抱著老婆,嗓音溫柔,“我只對你花心思。”“他們說你心狠手辣?”“要是有誰欺負你,我就對誰心狠手辣。”“他們說你……”男人伸手,把小嬌妻壁咚在牆上,“寵你愛你疼你一切都聽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還是你的。寶貝還有什麼問題嗎?”婚後。陌念才知道自己上了賊船。她偷偷的收拾東西,準備跑路。卻被全城追捕,最後被顧遇年堵在機場女洗手間。男人步步緊逼,“女人,懷著我的孩子,你還想上哪去?”陌念無話可說,半響憋出一句,“你說一年後我們離婚的!”男人腹黑一笑,“離婚協議書第4.11規定,最終解釋權歸甲方所有。
130.5萬字8 30545 -
完結978 章

孽火
繁華魔都,紙醉金迷。我在迷惘時遇到了他,他是金貴,是主宰,把我人生攪得風起云涌。我不信邪,不信命,卻在遍體鱗傷時信了他,自此之后,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253.1萬字8 16987 -
完結679 章

財閥大佬,您的夫人A炸了
【萌寶+馬甲+女強男強+打臉爽文】 正式見麵前: “找到那個女人,將她碎屍萬段!” “絕不允許她生下我的孩子,找到人,大小一個也不留!” 正式見麵後: “我媳婦隻是一個被無良父母拋棄的小可憐,你們都不要欺負她。” “我媳婦除了長的好看,其他什麼都不懂,誰都不許笑話她!” “我媳婦單純善良,連一隻小蟲子都不捨得踩死。” 眾人:大佬,求您說句人話吧!
124萬字8.25 732289 -
完結7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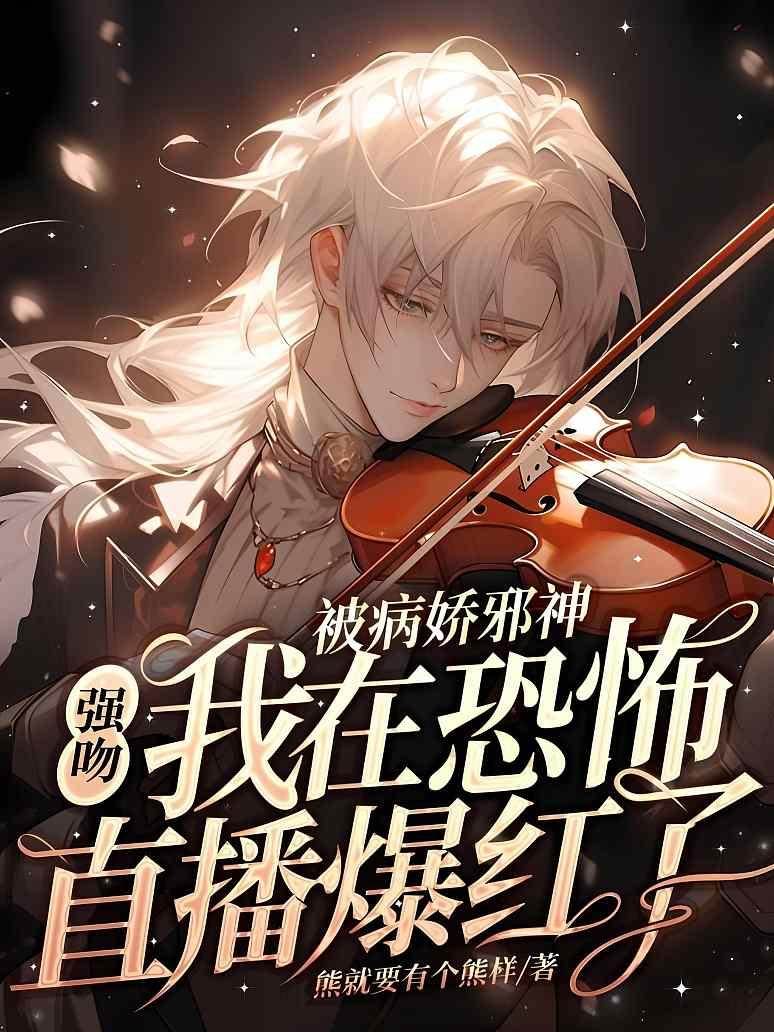
被病嬌邪神強吻!我在恐怖直播爆火了
桑榆穿越的第一天就被拉入一個詭異的直播間。為了活命,她被迫參加驚悚游戲。“叮,您的系統已上線”就在桑榆以為自己綁定了金手指時……系統:“叮,歡迎綁定戀愛腦攻略系統。”當別的玩家在驚悚游戲里刷進度,桑榆被迫刷病嬌鬼怪的好感度。當別的玩家遇到恐怖的鬼怪嚇得四處逃竄時……系統:“看到那個嚇人的怪物沒,沖上去,親他。”桑榆:“……”
123.3萬字8.1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