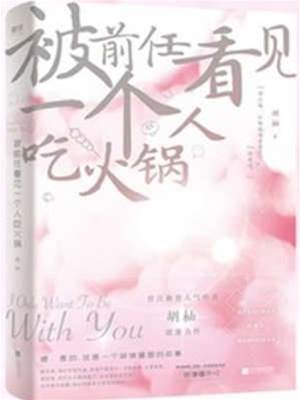《先生別虐了,太太要嫁你死對頭了》 第306章 想把他眼珠子扣下來當炮踩
這四個男人,留著絡腮胡的名為趙剛。
旁邊瘦小一點的六子,看上去有點營養不良,麵黃瘦。
另外兩個方臉小眼睛的雙胞胎,一個李奎,一個李瑞。
他們都是土生土長清河鎮的人,趙剛莽夫一個,祖輩都是這清河鎮的獵戶,到他這裏從事了屠夫,偶爾也去山上晃悠晃悠。
六子則屬於老實本分的一掛,自己和媳婦開了個小賣部。
另外這倆兄弟一個開網吧一個開臺球廳,不過都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瞎混瞎玩。
酒過三巡,四個男人都喝得上了頭。
飯館裏的人也漸漸走完了。
李奎,李瑞熱的將外下來,著個膀子。
“兄弟,不是我給你吹,就沒人比我更了解淵山,老子前段時間還進去打過一隻野狼,六子,給哥們看看你脖子上的狼牙!”
說著,趙剛一把將六子扯過來,作勢就把他脖頸裏的狼牙掏了出來:“這可是正兒八經的狼牙,辟邪護,我這兄弟八字輕,弱多病還做噩夢,帶著這個好不呢。”
墨子淵瞧著六子前的狼牙,桃花眼微微瞇了瞇:“你還有這本事。”
“那你說的,我不是給你說了我爺爺,我爺爺的爺爺都是絕頂的獵戶出,這十裏八鄉的誰不知道。”
赫連珩見他們都喝的差不多了,這才幽幽開口:“我來之前聽人說過淵山的一個傳聞,不知道真的假的。”
“什麽傳聞?”趙剛咣當又幹了一杯啤酒,挑眉道。
“聽說淵山深有一個彼岸村,村裏都是些喜歡怪力神的人,是麽?”赫連珩低頭將酒倒滿,目沉沉的問。
Advertisement
咣當!六子手上的杯子在地上摔了個碎。
他臉煞白的從地上把杯子撿起來,趕忙道:“沒……沒拿穩。”
趙剛對著他的頭就是一掌:“出息玩意!瞧給你慫嚇得,什麽彼岸村,那都是嚇唬小孩的玩意。”
說著,笑瞇瞇的看向赫連珩:“不好意思啊老哥,我這兄弟別的沒有就是膽子小,前些年,他跟我進山裏了一趟,回來就病倒了。”
“本來也就是喝了不幹淨的水,染得包蟲病,偏我們村口那神婆子非要說我們六子染了什麽彼岸村的蠱蟲,可給我們六子一頓嚇。”
“那蟲我們都沒見過,確實很嚇人。”六子現在想想還後脊背發涼。
“怎麽個事兄弟,說來聽聽。”赫連珩跟趙剛了杯子。
趙剛立馬擼袖子風風火火的講起來:“也就五六,七八年前?那陣子我們鎮長兒生了怪病,神婆子說要是能去淵山搞個什麽人參靈芝啥的補補,肯定好得快。”
“我們鎮長讓人去城裏找,找回來都是殘次品,喝了本沒用,我們兄弟幾個就想,淵山裏麵肯定有,當時鎮長開價兩萬,兩萬啊,我們想都沒想就一猛子紮了進去,想運氣。”
“但我們運氣不好,八月份的天氣,淵山裏麵竟然起了霧,本看不清路,我們這老本地人也在裏麵迷了路。”
“當時那霧大的,他站我跟前我都沒看見。”李奎手舞足蹈道。
“誰說不是呢,我們迷路迷了幾天來著,幾天來著……”趙剛掀著迷離的眼睛細細想著。
“五天!我記得很清楚,第三天的時候我們吃的就吃完了,第四天找了一天才找到兩隻野兔子。”李瑞接道。
Advertisement
“也是第四天,六子喝了那河裏的水,喝完就喊著肚子疼,又吐又拉,發著高燒還說夢話,非要說河裏有個人頭。”
“是啊,媽的,要不是那時霧散了我們幸運,索了一條路回來,六子這貨可能就活不到現在了。”趙剛一拍桌子道。
“然後呢?”墨子淵聽上了癮,瞪著雙桃花眼急切的問。
“我們回來以後,六子就高燒昏迷了,裏一直嚷嚷著人頭人頭,可給我們嚇得不輕,村裏人看見都以為六子中了邪,趕喊了神婆子。”趙剛繪聲繪道。
“神婆子一聽我們遇到大霧還在山裏轉悠了快一周,說我們是誤闖了彼岸村的鬼門,被人下了蠱了,我草,這我們能信嗎?還是拉著六子去了醫院。”
“鎮上的醫院檢查半天說是食中毒,喝了藥沒用,我們沒辦法,湊了所有的錢帶著六子去了城裏的醫院,人家一拍片,誒,你猜怎麽著,因為喝了生水,肚子裏長蟲了。”
“那蟲子這麽老長,黑漆馬虎的很嚇人。”李瑞比劃著。
“去你媽的,哪有那麽長,也就小手指那麽長,細嘎嘎的,惡心倒是真惡心,蟲子取出來以後我們六子元氣大傷,這不,這麽多年沒養回來。”趙剛了六子的頭道。
赫連珩和墨子淵對視一眼。
墨子淵皺眉,赫連珩的蠱蟲,他們用最先進的儀檢測了,但並未在髒中發現蟲子或者蟲卵。
也有可能,六子當時真的是喝生水導致的,所以蟲子寄生在胃部,肝部,正好能看到。
而赫連珩的蠱蟲,在前期不斷移,現在要想查到在哪裏,還是有點費勁的。
Advertisement
更何況,查到也不能完全手治療。
按照顧南音所言,若是休眠蠱,若是沒有一擊而中,開始瘋狂逃竄,那就麻煩大了。
為今之計,還是要先確定蟲子類型,再做定論。
“你們那個神婆,如今還在嗎?”赫連珩問。
“在是在,不過要見可是很費勁的,生人是不見的。”趙剛聽到赫連珩對神婆興趣,酒意都清醒了不,當即瞇著眼睛嘿嘿笑道。
墨子淵翻了個白眼,這群窮瘋了的,又想要開始訛人了。
坐在收銀臺上的小姑娘正聽得神,突然看到從門口進來兩個孩。
年紀都不大,穿著很休閑的黑運棉服,一頭長發像瀑布似的淌下來。
這樣的棉他們這裏可沒見過。
要說從外地來的這幾個穿的都是很單薄,這零下十幾二十度的天,他們是怎麽扛下來的。
其中一個帶著黑鴨舌帽和口罩,低著頭看不清的長相。
另外一個長得若天仙,纖細的材,白到發的臉,畫著淡妝,就跟電視裏的明星似的,比明星還好看。
“兩位姐姐,要……要吃飯嗎?”小姑娘急匆匆的跑過去,眼睛一順不順的盯著看。
好漂亮啊,真的太好看了,原來城裏真的有這樣的仙。
聽到這麽晚了還有人來,座上的幾人齊齊往門口去。
這一看不要,墨子淵的眼睛差點跌在地上。
顧南音?怎麽會在這裏!
後的人是誰?慕念嘛?
“兩碗餛飩。”顧南音微微一笑,說完便抬腳往赫連珩他們那桌而去。
而戴著黑鴨舌帽的孩轉坐在了一個空桌子上,並未跟過去。
“好的,現在就給您做。”小姑娘應聲,歡快的跑向後廚。
“珩爺,墨先生。”顧南音衝兩人點頭的功夫,長一抬,勾了把椅子坐在了趙剛邊:“我來給你們送點東西,剛才聽到這位大哥說什麽神婆,我很興趣,能不能帶我也見見?”
趙剛看著眼前若天仙的姑娘,眼睛瞪得大大的,口水都快從角淌出來了。
“妹妹,你上好香啊。”趙剛一副癡呆模樣,盯著顧南音晃了神。
墨子淵的臉當即黑下來,想把他眼珠子扣下來當炮踩!
猜你喜歡
-
完結1795 章
婚內燃情:三叔,別這樣!
“我會負責。”新婚夜老公的叔叔在她耳畔邪惡道。人前他是讓人不寒而栗的鐵血商業惡魔,人後卻是寵妻狂。他對她予所予求,為她鋪路碎渣,讓她任意妄為,一言不合就要將她寵上天。隻因多看了那件衣服一眼,他就直接壟斷了整個商場在她的名下。他說:“隻要你要,傾我所有!”
166.3萬字8.08 304871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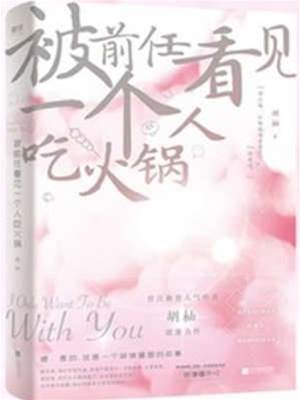
被前任看見一個人吃火鍋
【葉陽版】 葉陽想象過與前任偶遇的戲碼。 在咖啡館,在電影院,在書店。 在一切文藝的像電影情節的地方。 她優雅大方地恭維他又帥了, 然后在擦肩時慶幸, 這人怎麼如此油膩,幸好當年分了。 可生活總是不盡如人意。 他們真正遇到,是在嘈雜的火鍋店。 她油頭素面,獨自一人在吃火鍋。 而EX衣冠楚楚,紳士又得體,還帶著纖細裊娜的現任。 她想,慶幸的應該是前任。 【張虔版】 張虔當年屬于被分手,他記得前一天是他生日。 他開車送女友回學校,給她解安全帶時,女友過來親他,還在他耳邊說:“寶貝兒,生日快樂。” 那是她第一次那麼叫他。 在此之前,她只肯叫他張虔。 可第二天,她就跟他分手了。 莫名其妙到讓人生氣。 他是討厭誤會和狗血的。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讓她說清楚。 可她只說好沒意思。 他尊嚴掃地,甩門而去。 #那時候,他們年輕氣盛。把尊嚴看得比一切重要,比愛重要。那時候,他們以為散就散了,總有新的愛到來。# #閱讀指南:①生活流,慢熱,劇情淡。②微博:@胡柚HuYou ③更新時間:早八點
19.1萬字8 7230 -
連載601 章

這主播真狗,掙夠200就下播
189.5萬字8.18 8244 -
完結146 章

那月光和你
大學畢業,顧揚進了一家購物中心當實習生。 三年后,他作為公司管理層,和總裁陸江寒一起出席新店發布會。 一切看起來都是順風順水,風波卻悄然而至。 高層公寓里,陸江寒一點點裁開被膠帶纏住的硬皮筆記本,輕輕放回顧揚手里。 那是被封存的夢想,也是綺麗華美的未來。 再后來。 “陸總,您能客觀評價一下顧先生嗎?” “對不起,他是我愛人,我客觀不了。”
41.4萬字8 6805 -
完結122 章

月光渡我
時衾二十歲那年跟了傅晏辭。 離開那天。 傅晏辭懶散靠門,涼涼輕笑:“我的衿衿急着要長大。” 時衾斂下眸子:“她不可能永遠是你的小女孩。” 夜深。 時衾咬着牙不肯。 傅晏辭發了狠,磨得人難捱,終於得償所願換到一句破碎的細語—— “衿衿永遠是你的小女孩。”
18萬字8 122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