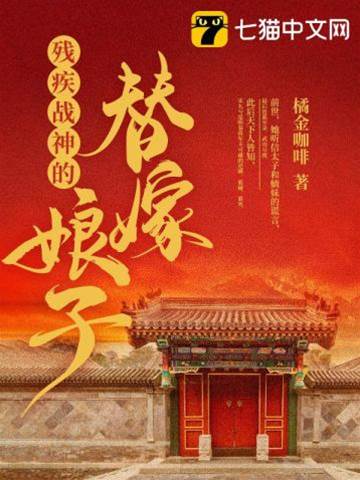《被嫡姐換親之后》 第96頁
從前都是碧月姐姐全權管著姑娘的梳妝打扮,和春澗只是幫手。現下碧月姐姐出去了,這差事下來,們心里還不太有底。
坐在妝鏡前,紀明遙想了想,說:“新婚還是得穿紅,頭發沒,抿一抿就行了,首飾戴幾樣——”
決定:“我從前在家里怎麼樣,最多再多兩簪子就好,也不用上胭脂水。”
上輩子一直是短發,簡單清爽好打理,很省時間,從沒想過留長。這輩子頭發是不可能剪的了,也不是不喜歡金銀珠玉,但只喜歡拿在手上欣賞,不太喜歡戴在頭上上發沉的覺……
以后要在崔家過一輩子,不可能裝一輩子,而且,也不愿意太過裝相委屈著自己。
所以,原本是什麼樣,就想給崔玨看到什麼樣。
承認,是仗著正在新婚燕爾、也仗著發現了崔玨對的好和憐,一點點向前試探。
姑娘有吩咐,春澗花影不多說,很快替姑娘裝扮完畢。
青霜也匆匆回來了,進來就笑道:“二爺說請姑娘過去便是。”
又笑回:“我到的時候,二爺正練刀呢。我出去的時候,又聽見二爺吩咐小廝打水洗澡。”
但二爺練刀是什麼模樣沒細看,就不能說給姑娘了。
練刀啊。
紀明遙瞬間想起了許多小說話本里對年英氣俠客、青年冷俊指揮使的形容。
——想看!
Advertisement
想看崔玨練刀的樣子!
雖然現在趕不上了,但說不定下午或明早就有機會。
嘿嘿嘿嘿。
時間不算太,紀明遙就走在傘下,將書房與正院之間的廳堂也細看了一遍。
院里的丫頭婆子只遠遠向行禮,都沒過來請安。
青霜主回道:“姑娘睡著的時候,請桂嬤嬤出來教了一遍,倒不知們原來是什麼規矩。”
紀明遙點頭,但并不急著在這時候見新人。
現在最要的是崔玨的家業要不要管,其余都要排在后面。
且若接手崔玨的家業,見這些人說話是一種態度,若不接手,就會是另一種態度了。
出了廳堂院落,再走一條南北夾道,便是崔玨的書房。書房從后穿堂也能進去。
紀明遙看到了圍墻遮不住的一叢青竹。
提起子,才邁上臺階,便聽邊人都請安說:“二爺!”
接著,的手腕就被握住。
握住的手纖長有力、骨節分明,掌心是昨夜和今早悉了的溫度。
紀明遙笑著抬頭。
崔玨鬢角還有幾分,上是新換的袍,面上也因才練過武又洗了澡,比平常多了幾分紅潤,連眉眼都顯出和。
他說:“夫人慢些。”
“嗯,”他握得很松,紀明遙把手腕向外了,直接握住他的手,笑喚一聲,“二爺。”
兩人并肩走了進去。
這書房比紀明遙的正院略小,正房只有三間,但院落的空間便顯得更大。分明正是百花姹紫嫣紅的初夏,這院子里卻無一點鮮亮的,只有竹影森森、樹蔭蔽日、鳥鳴細細,清幽至極。
Advertisement
紀明遙不由多賞了片刻。
待收回目,崔玨才請向屋走。
屋里站著兩個小廝,分明聽見人進來,卻連頭都不敢抬。
紀明遙也且不管他們,先將三間屋子大致掃過一遍。
普通的書房,三間屋子全有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
堂屋正中是一張不大的八仙桌,墻上一副對聯和一張匾,匾上兩個字“靜堂”,其余并無擺設裝飾。
西側應是臥房。堂屋西面的墻壁上掛著刀、劍、弓、槍。臥房門開著,紀明遙沒有仔細向張。
東側無墻隔斷,只有一張輕巧的竹石屏風立在當地,里面是書案、扶手椅等,臨窗有榻。
紀明遙自然有了很多問題。
最先問的是:“除了這幾間屋子,還有哪放著書?”
崔玨答:“東廂、西廂皆有,庫中也有,大哥書房亦有許多孤本。”
若夫人想看,他可以去借。
紀明遙現在不想看書。尤其掃了一眼在外面的書封,更是興致全無。
只又問:“二爺平日練武都在什麼時辰?是晨起嗎?”
“非朝日便是晨起,”崔玨答,“或傍晚有空閑,也會練上幾刻。”
“那今晚有空閑嗎?”紀明遙立刻笑問。
“……大約有。”崔玨回答。
他好似猜到夫人想說什麼了。
“多謝二爺!”
紀明遙又靠近他一寸,小聲詢問:“那我下午過來看?還是二爺下午不走了,就在后面?總歸不管在哪,二爺都給我看看吧。”
Advertisement
“嗯。”
崔玨攥了攥手,心道他并無不可給夫人看之,便又重復回答一次:“好。”
“二爺真好。”紀明遙聲音更小。
說這些話,其實也不是完全坦。
但真的想看嘛。
已經達目的,紀明遙趕轉移話題,又問匾額:“這是二爺的字?”
這匾與“凝曦堂”三個字看上去是同一人所寫,只是“靜堂”兩個字還稍有清秀稚氣,“凝曦堂”三字的筆跡卻更剛勁、質樸、有力,意態也添了許多瀟灑自由。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逆天五寶:主母她是個受寵體質
一朝穿越,她直接就當起了便宜媽,寵愛一個遊刃有余,一下子五個寶寶真的吃不消。 她刷著小算盤打算全都退還給孩他爹,卻突然間發現,這一個個的小東西全都是虐渣高手。 她只需勾勾手指,那些曾經欺負她害過她的就全都被她五個寶寶外加娃他爹給碾成了渣渣! 爽點還不止一個,明明一家七口五個都比她小,結果卻是她這個當娘親的成了全家人的心尖寵。
12.5萬字8 41511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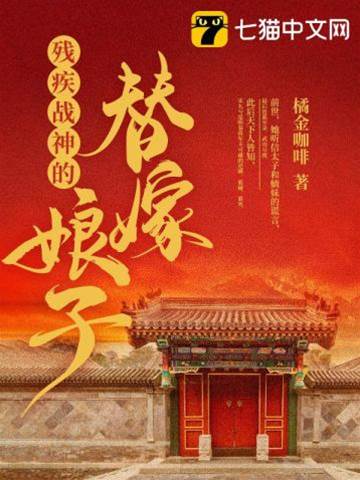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645 章

盛唐無妖
穿過盛世大唐茶都還沒喝一口被迫上了花轎遇上了口味比較重的山村女鬼... 老師傅:姑娘,世上竟有你這般如此骨骼精奇、命格貴重、百邪不侵... 顧曳:說人話 老師傅:你命硬,可驅邪,上吧!
176.8萬字8.18 7847 -
完結608 章
盛寵世子妃
一覺醒來,現代大齡剩女變成了農女,內有渣爹狠毒嫡母,外有惡鄰惡霸環伺,怎麼破?種田發家,智商碾壓!貪心親戚是吧?我讓你搶,到嘴的都給我吐出來!白蓮花是吧?我讓你裝,將計就計虐你一臉!什麼?後臺?隨手拎個世子當苦力算不算?某夜,世子大人可憐巴巴地湊過來:"娘子,他們說,你沒付我工錢…""嗯?"…
94.8萬字8 88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