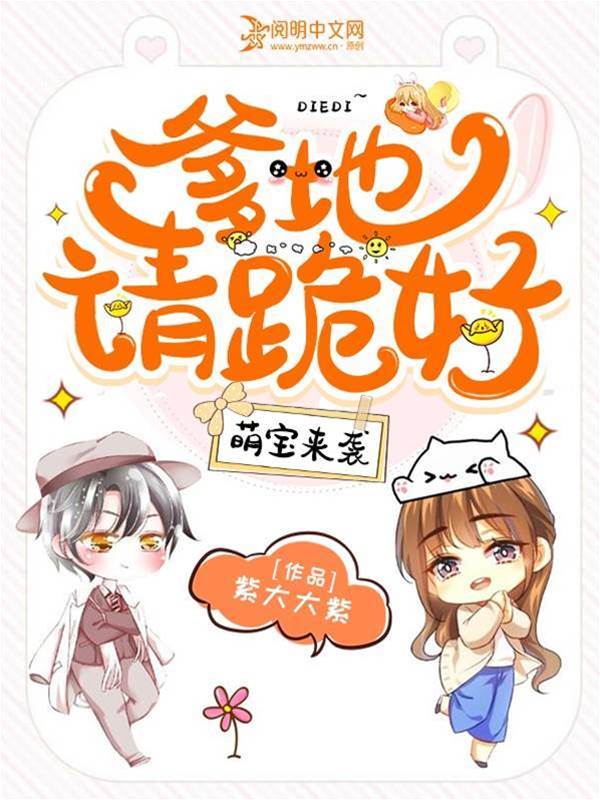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婚不厭詐》 第26章 玩具槍
江寒深輕輕笑了起來。
“玩槍,很難找嗎?”
說完,江寒深退了回去,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盛晚:“?”
子都了,就這?
玩槍?
逗呢?
顧祈年沒注意到後座的古怪,這會轉過頭來,手上還拿著剛才的那把槍:“嫂子,你看看,這玩槍做得還真的。”
盛晚心有疑,接了過來。
而等到拿到手之後……
盛晚確認了。
這還真的是玩槍。
盛晚:“……”
玩槍做得很真,但還是能夠分辨出一二的,不過,天黑,又隔著距離,的確不好辨認。
所以,江寒深就搞了一堆玩槍,找了這麽幾個人,就來救了?
這要是文哥發現了其中端倪,嘖,他們今天要想全而退,怕是就有些難了。
“江,真有趣。”盛晚慨。
江寒深挑眉:“畢竟是法治公民,怎麽會有槍這種危險東西?”
“倒是盛小姐。”江寒深臉上帶著笑,但是眼神裏的打量,毫不藏:“盛小姐對於我有槍的事,似乎,一點都不驚訝。”
盛晚心下一。
的確。
有錢人不,但是每個有錢人都能搞到槍這些東西嗎?
那不可能,要是這樣,這個社會早就了。
而現在的江寒深,在蘇市,對於盛晚來說,應該隻知道他是握有簡氏權的一個私生子罷了,連簡家都抗不過去,又怎麽可能會隨隨便便拿出那麽多槍來?
這顯然是不符合邏輯的。
但沒有懷疑……
Advertisement
因為太過平靜地接了這一切,所以,江寒深對起疑了。
江家,早年涉黑。
所以,對於盛晚而言,江寒深拿出槍來,有些詫異,但又很輕易地就讓人接,本來就在意料之中的覺,而現在,麵對江寒深的追問……
江寒深的視線,還落在的上。
盛晚隻覺得剛剛落下去的心,此刻又有往嗓子口冒的衝。
沒有立刻開口,車的氣氛,似乎也在瞬間張了起來。
“盛小姐,不能說?”江寒深又開口。
盛晚忽然出了一個笑。
江寒深在試探。
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自陣腳。
也不能表現得太過合理普通,江寒深是隻狐貍,他未必會信。
這麽想著,盛晚挑了挑眉,開口:“沒辦法,誰讓我實在太信任江了?”
“畢竟,江也不像是會玩玩槍的小屁孩。”盛晚回。
沒有去承認自己到底是驚訝還是不驚訝,因為無論怎麽回答,都會出端倪。
那麽,就擺出一副對此本就無所謂的態度來!
讓江寒深自己去猜。
猜,就有猜錯的可能,就是可以利用的機會。
江寒深笑了。
“那倒是,玩槍,的確不是我的風格,畢竟,我素來隻會,真刀,真槍。”江寒深打趣。
盛晚的眉眼跳了跳。
最後四個字,實在說的過於意味深長,和江寒深鋒過太多次,盛晚早就已經準江寒深的習慣,所以,這話……聽明白了。
盛晚也覺得很神奇。
Advertisement
上一秒還在試探,下一秒黃腔就開起來了?
合適嗎?
太合適了!
盛晚拿起手裏的玩槍,晃了晃:“真刀,真槍?”
江寒深從盛晚的手裏拿過,隨後,直接抵在了盛晚的太上。
他還是帶著笑,盛晚卻嗅到了一危險的味道。
“盛小姐,又如何確定,這真的隻是一把玩槍呢?”
“又或者,盛小姐又如何知道,我手上,沒有真槍呢?”
盛晚心下再次一。
江寒深這個狗東西,這話裏表現的意思,太多了。
他還是在試探。
盛晚笑著,手握住了江寒深的手,隨後掉轉他的手腕,江寒深也沒阻攔,由著盛晚轉他的手腕,將玩槍的槍口,對準了江寒深。
“江,小心走火。”盛晚說。
江寒深笑了起來,這一笑,和先前的不同,倒是多了點愉悅的味道,車那子僵持的張氣氛,也瞬間消散了不。
他出另外一隻手,握住了盛晚的手腕,指腹輕輕,暗示十足。
“玩火,尿床,不好嗎?”江寒深說。
盛晚先是愣了一下。
玩火尿床,這玩意就是大人騙小孩子的,而現在,這話從江寒深口中說出來……
玩火,玩的是男之間的浴火,而尿床——
江寒深說這話的時候,視線還落在了盛晚的大上。
裏麵的子現在早就條了,站著的時候,還好一點,坐下來,就有了暴的風險,雖然上披著江寒深的西裝,但是,西裝並不長,也隻能堪堪遮住一些。
Advertisement
江寒深現在看過來,說不出的意味深長。
盛晚:“……”
盛晚嗤了一聲,回:“可現在,是在車上。”
江寒深挑眉:”我不挑,也不是不行。”
盛晚:“……”
視線往前麵掃了一眼,顧祈年和司機是大氣都不敢出,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存在。
“江可真有奉獻神。”盛晚懟了一句,而後一偏,不搭理江寒深了。
江寒深見此,笑了笑,倒也沒有再去逗盛晚。
車子直接開到了盛庭博府。
盛晚下了車。
江寒深依舊沒有靜。
盛晚蹙眉:“你不會?”
江寒深降下車窗,看著車外的盛晚,笑:“盛小姐這是在邀請我嗎?”
“破碎,的確沒有嚐試過。”
盛晚:“?”
想到自己西裝下,堪堪掛在上的布條,盛晚的火氣又有點忍不住了。
“滾!”盛晚送了江寒深一個字,隨後轉就走。
江寒深在後頭樂得不行。
等到目送盛晚離開之後,顧祈年這才弱弱地開口:“江哥啊,你們夫妻倆,這麽……”
“嗯?”
“我想到了一種。”
“And it was called Yellow。”顧祈年直接唱了起來。
江寒深開口:“夫妻趣,不知道塞耳朵?”
顧祈年:“……”
霸道過分了吧?
哦,他江哥啊,沒事了。
顧祈年乖巧作答:“這次沒有經驗,下次記住了。”
江寒深哼了一聲,隨後開口:“去查查盛晚和江家那邊的關係。”
顧祈年愣了一下:“江家的人?”
江寒深閉眼假寐,麵平靜:“未必,但估計是江家那邊走了消息,盛晚,恐怕知道一些我的事。”
“那……要不要?”顧祈年試探。
江寒深睜眼,看了過來,好脾氣地問:“要不要什麽?”
顧祈年立刻做了一個閉的作。
江寒深又閉上了眼,說:“再去查查簡褚辰。”
“今天這事,恐怕不止一個呂言席。”
猜你喜歡
-
完結759 章

慕川向晚
千年難得一遇的寫作廢柴向晚,因為書撲成了狗,被逼相親。 “媽,不是身高一米九腹肌十六塊住八十八層別墅從八百米大床上醒來的國家級高富帥,一律不要。” “……你是準備嫁蜈蚣?” 后來向晚終于如愿以償。 他被國家級高富帥找上門來了,撲街的書也突然爆火—— 有人按她書中情節,一比一復制了一樁命案。 而她與國家級高富帥第一次碰撞,就把人家給夾傷了…… …… 愛情、親情、倫理、懸疑、你要的這里都有,色香味俱全。 【本文狂撒狗血,太過較真的勿來。】
178.1萬字8.09 16781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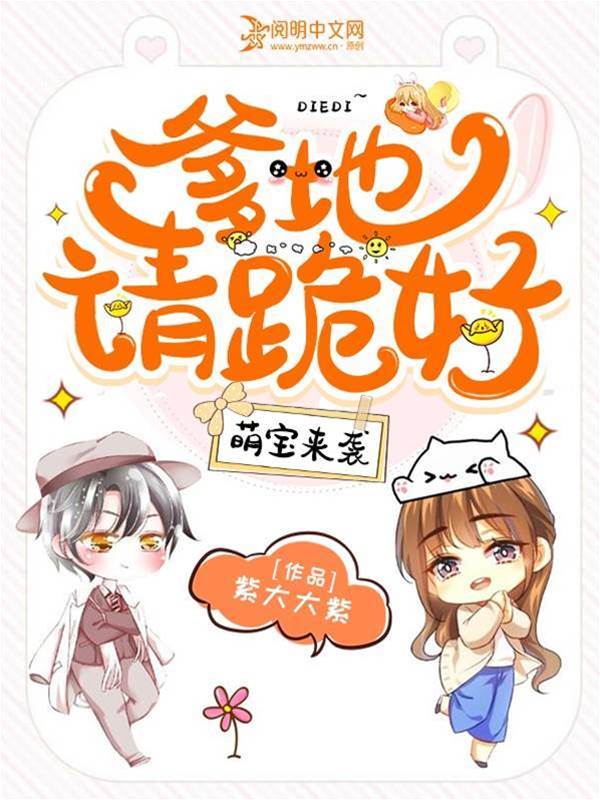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連載339 章

小啞妻死後,千億總裁在墓前哭成狗
一紙離婚協議,喬明月挺著八個月的肚子被趕出薄家。卻不幸遇到車禍,她瀕臨死亡之際,才想到自己的真實身份,不是啞巴,更不醜,而是名動雲城的喬家大小姐!她憤恨、不甘,最終選擇帶著孩子獨自生活,順便虐渣打臉。誰知五年後,孩子的親生父親卻回到雲城,甚至還想讓她嫁給別人!喬明月冷哼一聲,磨刀霍霍預備宰向豬羊!多年後,薄時琛懊悔不已,本該是他的妻,卻兜兜轉轉那麼多年,才重回他的懷抱。
61萬字8 6030 -
完結142 章

他等我分手很久了
莊斐和男友,以及男友的好兄弟陳瑜清共同創立了家公司。陳瑜清以技術入股,對經營的事一概不問。 莊斐和男友經營理念出了分歧,經常意見相左。每每這時,他們就要徵求陳瑜清的意見,試圖以少數服從多數來讓對方妥協。 可陳瑜清總是沒意見,來回就那麼幾句——“隨便。”“你們定。”“我怎麼樣都行。” 他甚至還能幫他們關上會議室的門,懶洋洋地站在門口喊:“你們先吵,吵完了叫我。” - 莊斐離職,幾個要好的同事爲她舉辦了一場狂熱的歡送會。一慶仲裁庭裁決拖欠多年的勞動報酬到手,獲賠高額賠償金;二慶擺脫渣男,恢復自由之身。 森林酒吧裏,渣男的好兄弟陳瑜清不請自來。 莊斐喝醉了,姿態嬌媚地勾着陳瑜清的脖子:“反正你怎麼樣都行,不如你叛了他來幫我?” 不料,厭世主陳瑜清反手扣住她的下巴,毫不客氣地親了下去,無視一羣看呆了的朋友。 他側在她耳邊低語:“既然你那麼恨他,不如我叛他叛個徹底?”
21.4萬字8.18 7874 -
連載455 章

終極火力
這個世界不只是普通人熟知的模樣,還有個常人不會接觸的地下世界。政府特工在暗中處理麻煩,財閥雇養的殺手在私下解決問題。有殺手,傭兵,軍火商,還有特工,有把這個世界
99.5萬字8.18 30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