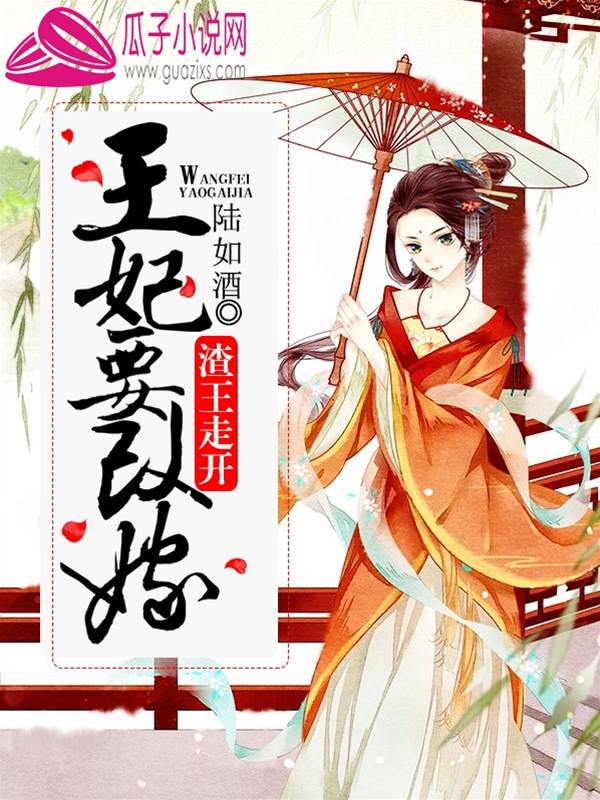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春滿酥衣》 分卷閱讀167
著酈,與妻子坐於家中。聽著自樓外傳來的風聲,嚇得心驚膽戰、坐立難安。
特別是,聽聞那群可惡可恨的西蟒人,以沈夫人為要挾,迫沈將軍大開城門時。
長襄夫人氣得眼眶發紅。
床榻之上,烏發披肩,因是了寒,雙有些失了。適才沈夫人暈厥時,他上前替對方把了脈象,又開了幾道方子,幫著夫人調理休養。
正思量著,忽然見榻上子放下方喝了兩口的母湯。
匆匆穿了鞋,竟連招呼都不打一聲,徑直朝房門外奔去。
長襄夫人微驚:“哎,夫人,您這是要去哪兒?”
他這一聲還未說完,話語忽然一頓。
下一瞬,隻見沈將軍一雪白衫,腰係寶劍,闊步行至院中。
長襄夫人忍不住在心底裏發笑。
夫人與將軍果真恩,旁人還沒見著影兒呢,這就已經撲上去了。
沈頃也看見了跑出房門的酈。
像是方轉醒,披散著頭發,麵亦有些發白。見狀,男人兀地皺眉。
“怎麽穿這麽。”
他彎下,語氣有些急,卻並無埋怨。
“你方了寒,還敢穿這般。連見氅子都不披,就這樣跑出來了。,你是要急死我。”
他一邊說著,一邊不假思索地解下上衫,披在上。
即便懷有孕,姿依舊纖瘦,與前男人相比,的子更是瘦弱得不樣子。對方乍一彎,便將整個人結結實實地攏住。酈還未來得及喚,沈頃已出雙臂,將自地上打橫抱起。
Advertisement
抱著往房走,男人依舊步履輕鬆。
長襄夫人也是極識眼的,見二人如膠似漆,他趕忙放下手中之,將酈的眼睛一捂,帶著小姑娘匆匆離去。
一時之間,偌大的屋隻剩下與沈頃二人。
沈頃的力道極大,極穩。
酈被他像個擺件似的放至榻上,烏發披下來,麵微紅。
繼而,才將纖長的胳膊過去,抱著對方結實的腰。
撲麵而來悉的蘭香,酈吸了吸鼻子,道:
“我想你。”
“聽見你的步子,便心急地跑出來了。”
的聲音有些委屈。
聽得沈頃心頭一陣發,他低下頭,目也不放。
本想叮囑幾聲,如今卻不舍得再說重話。
沈頃出手,無奈了的臉頰,言語寵溺:
“下不為例。”
又是下不為例。
隻要在沈頃這裏,無論做了什麽事,無論犯了什麽事。
他永遠都是那句帶著寵溺的——下不為例。
酈將臉埋進他懷裏。
男人膛結實,卻不冰冷。帶著沾滿蘭香的暖意,將形寸寸包裹。側臉,能聽見對方緩緩加速的心跳,即便親有許多時日了,即便腹中已有了前之人的孩子。
二人親接時,沈頃仍會臉紅。
他的呼吸微熱,耳亦暗暗發燙。
垂下纖長濃的眼睫,男人聲息亦低下來。他目繾綣,輕輕劃過微的麵頰,想起前些日子的事,仍心中生痛。
他沉默時,道:
“是我不好。,是我讓你委屈了。”
Advertisement
酈正靠在他懷裏。
耳畔一道熱氣,抬起頭,恰恰對上男人一雙寫滿了自責的眼。
他的眸很漂亮,溫和,不帶半分淩厲。
與沈蘭蘅不同,也與他行軍打仗時截然不同。
“是我。我無能,護不住你。”
男人垂下眼,著的手,聲音愈低。
見他這般,酈亦心疼。
反手握住沈頃微涼的手指,爾後又將形近了些。窗牖微掩著,雨後微的風自隙間鑽,愈將那蘭香拂麵,吹得人周遭些許料峭。
春寒。
將臉埋男子懷抱,聲音亦:“不怪郎君。妾知曉,先前種種,都不是郎君所為,怨不得郎君的。”
貿然下軍令的是沈蘭蘅。
丟了玄臨關、打了敗仗的是沈蘭蘅。
帶著沈家軍困守通城的,亦是沈蘭蘅。
一切的源起,都是因那人。
“如若郎君在,定不會弄這般。真要怪罪下來,也要怪那人——”
歎著通之困的兇險,渾然沒有注意到,便在開口出聲時,側之人的形竟一寸寸發僵。
酈後知後覺。
“郎君怎麽了?”
他麵上神忽然變得有些奇怪。
麵一滯,雙微白,濃的睫羽下,翕著不辨悲喜的澤。
春日晌午,和煦的日影穿過窗牖,落在男人肩頭。
酈上披著對方那件氅,清風拂來,周如有仙鶴舞,習習翻飛。
“郎君?”
接連喚了好幾聲。
終於,喚回沈頃神思。
Advertisement
酈問:“郎君,怎麽了?”
他看上去似有心事。
男人抿了抿薄,睫影微,眼底如有浮掠影,粼粼而過。
不過轉瞬,這道緒又被他悄然製下去。
沈頃聲音清潤,頭一次對妻子撒了謊:“無事。隻是想著待晚上時要去尋智圓大師祭神,一時出了神。”
“祭神?”
“嗯。”
他點頭,這回卻未再騙,“此次玄臨關一役,我軍將士傷亡數多。今夜……便是眾將士的頭七夜,我想前去神靈之前,為已故將士超度祈福。”
說到這裏,男人微斂神,狹長的眸裏,出慈悲的澤。
思及此,酈亦正。解下上那件氅,披至夫君上。
“郎君,您去罷。”
恰巧智圓大師正在通城中,不知因何緣由,至今尚未離去。
在長襄夫人家用了晚飯,酈便送沈頃上馬。
唯一令酈欣的是,今日黃昏過後,沈頃仍是沈頃,並未變那一人。
便就在他方上馬,揚鞭之時。忽然一道風聲,吹拂得男人袍獵獵,沈頃獨坐烈鷹之上,驀然回頭。
“——”
酈站在院裏,腳下即是那一層不高不矮的階梯。
聞聲,仰首,隻一眼便瞧見對方那一雙清澈溫的眸。
原是清冷的一雙眸,此刻眼中卻有搖曳,於著春風裏,於著春夜中,溫似水,深濃稠。
沈頃就這般回首,深深凝了一眼。
他溫的聲音隨著旖旎的夜風,拂至酈耳中:
“等我,我會回來。”
……
沈頃事先已派魏恪調查好了智圓大師的行蹤。
今夜,智圓大師正在積雪山中修行。
所謂積雪山,顧名思義,因
猜你喜歡
-
完結325 章

攝政王冷妃之鳳御天下
不可能,她要嫁的劉曄是個霸道兇狠的男子,為何會變成一個賣萌的傻子?而她心底的那個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趙國的攝政王?對她相見不相視,是真的不記得她,還是假裝?天殺的,竟然還敢在她眼皮底下娶丞相的妹妹?好,你娶你的美嬌娘,我找我的美男子,從此互不相干。
62.7萬字8 16261 -
完結668 章
毒妃傾城:王爺掌中寵
夏吟墨手欠,摸了下師父的古燈結果穿越了,穿到同名同姓的受氣包相府嫡女身上。 她勵志要為原主復仇,虐渣女,除渣男,一手解毒救人,一手下毒懲治惡人,一路扶搖直上,沒想到竟與衡王戰鬥情誼越結越深,成為了人人艷羨的神仙眷侶。 不可思議,當真是不可思議啊!
120萬字8 17247 -
完結150 章

殷總,寵妻無度
姜綺姝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當她慘遭背叛,生死一線時救她的人會是商界殺伐果斷,獨勇如狼的殷騰。他強勢進入她的人生,告訴她“從此以后,姜綺姝是我的人,只能對我一人嬉笑怒罵、撒嬌溫柔。”在外時,他幫她撕仇人虐渣男,寵她上天;獨處時,他戲謔、招引,只喜歡看姜綺姝在乎他時撒潑甩賴的小模樣。“殷騰,你喜怒無常,到底想怎麼樣?”“小姝,我只想把靈魂都揉進你的骨子里,一輩子,賴上你!”
37.1萬字5 11927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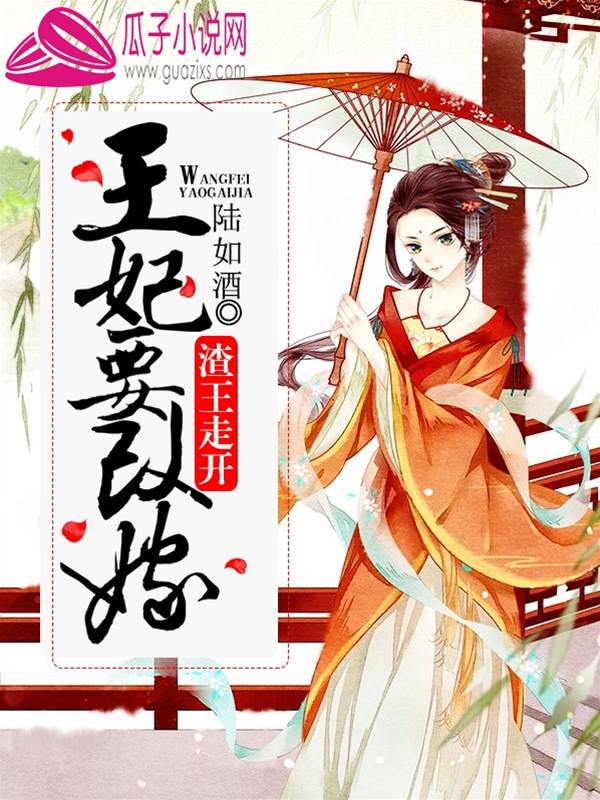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137 章

鶴帳有春
穆千璃爲躲避家中安排的盲婚啞嫁,誓死不從逃離在外。 但家中仍在四處追查她的下落。 東躲西藏不是長久之計。 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生個孩子,去父留子。 即使再被抓回,那婚事也定是要作廢的,她不必再嫁任何人。 穆千璃在一處偏遠小鎮租下一間宅子。 宅子隔壁有位年輕的鄰居,名叫容澈。 容澈模樣生得極好,卻體弱多病,怕是要命不久矣。 他家境清貧,養病一年之久卻從未有家人來此關照過。 如此人選,是爲極佳。 穆千璃打起了這位病弱鄰居的主意。 白日裏,她態度熱絡,噓寒問暖。 見他處境落魄,便扶持貼補,爲他強身健體,就各種投喂照料。 到了夜裏,她便點燃安神香,翻窗潛入容澈屋中,天亮再悄然離去。 直到有一日。 穆千璃粗心未將昨夜燃盡的安神香收拾乾淨,只得連忙潛入隔壁收拾作案證據。 卻在還未進屋時,聽見容澈府上唯一的隨從蹲在牆角疑惑嘀咕着:“這不是城東那個老騙子賣的假貨嗎,難怪主子最近身子漸弱,燃這玩意,哪能睡得好。” 當夜,穆千璃縮在房內糾結。 這些日子容澈究竟是睡着了,還是沒睡着? 正這時,容澈一身輕薄衣衫翻入她房中,目光灼灼地看着她:“今日這是怎麼了,香都燃盡了,怎還不過來。”
20.8萬字8.33 149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