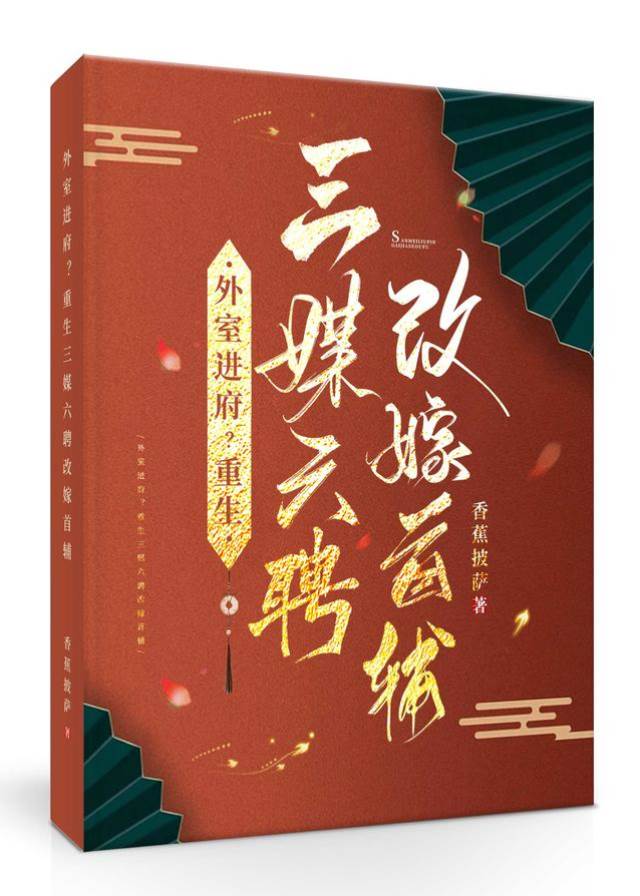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燈花笑》 第一百四十四章 針相大白
不舉?
什麼不舉?
誰不舉了?!
金顯榮腦子懵了一瞬,下意識道:“你胡說什麼……”
醫像是怕他聽不明白,著他道:“金大人不知道麼?你這病不是腎囊癰,是不舉之癥。”
“胡說——”
對方這話實在太驚世駭俗了,驚得他黑黃的臉皮泛出些蒼白,驚得他兩道斷眉快要飛到天上去,驚得連聲音都變了調。
“休要胡說八道!”
門口小夥計聽到靜,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問:“老爺,怎麼了?”
被金顯榮一聲咆哮:“滾出去!”又給嚇退,把門關得死。
陸曈手扶著醫箱,淡淡道:“金大人,難道這些日子你沒有覺得氣虛弱、力不足、行房不起?”
“……那是因為腎囊癰!”
“虧損可不是腎囊癰的表現,”又掃了一眼桌上的蓮紋青花碗,拿起來放在鼻尖下輕嗅一下,隨即搖頭:“大人本就虛,服用溫腎壯藥,只會更耗,不舉之癥越嚴重。”
“你怎麼知道這是溫腎壯藥?”話一出口,金顯榮陡然反應過來,“不對,你憑什麼胡說本是不舉之癥?翰林醫院派了好幾個醫來給我治病,都說是腎囊癰,你這小子,學藝不也敢大放厥詞,信不信本回頭就能讓你離開醫院?”
他說著說著,漸漸自信起來。
怎麼會是不舉呢?先前那麼多醫可都說的是腎囊癰,而且這醫只給他把了把脈,甚至都沒瞧過他……方才說的那些表癥,多半也是瞎貓上死耗子猜中的!
陸曈蹙眉:“之前的醫們,都說是腎囊癰?”
“不錯!”他這時哪還有心思調戲人,一心想要證明對方所言謬誤,他仍是那個雄風大展的金侍郎。
Advertisement
醫沉片刻,出一個微微恍然的表:“原來如此。”卻沒有繼續往下說了。
對方越是如此,金顯榮心中就越是抓心撓肝,忍不住問:“原來如此什麼?”
“我想說,金大人的腎囊癰遲遲不好,原來如此。”
“說明白些!”
醫頓了頓,重新看著他,語氣平淡:“大人口口聲聲說下學藝不,一心相信先前幾位醫們腎囊癰的說法,敢問大人,那這些醫為大人行診多日,大人可有起?”
金顯榮啞然。
別說起,事實上,他覺得況甚至越來越糟了。
“因為大人癥結本就不是腎囊癰,用治腎囊癰的法子,當然治不好。”
金顯榮咬牙,仍想掙扎一下:“那他們為何騙我?”
陸曈憐憫地著,那雙幽冷眼眸在長睫垂映下,若秋水人,然而說出的話卻比冬日的寒雪更涼。
“因為他們不敢。”
“大人居高位,正值壯年,若說出去,折損了大人自尊心不說,日後相見也尷尬。”平靜地說著話,彷彿沒意識到話裡的嘲諷一般,“再者,不舉之癥難治,醫們治不好,索說腎囊癰,讓大人覺得有希,也能繼續賺錢診銀。”
這話直白得讓人覺得冷酷。
金顯榮並不願意相信。
可是……
他先前就找人問過,尋常人得腎囊癰,不過個把月也就好了。何況這兩月以來,藥吃著、方子開著、醫瞧著,卻半起都無。
雖然他口口聲聲罵醫院一群庸醫,但好歹是翰林醫,多有些本事,怎麼會被一個小小腎囊癰難住。
但若是不舉……
他抬頭看向面前人,神有些不定:“你說那些醫誆騙本宮,但你也是醫,怎麼敢說實話?”
Advertisement
“我麼?”陸曈想了想,“可能因為,我是平人吧。”
“我是平人,在宮中並無背景,來之前也無人告訴我這件事。我若知道,或許為了明哲保就不會說出口了。再者,醫們瞞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許是早就決定挑只替罪羊,所以選中了我,來告訴大人真相。”
金顯榮愣了愣。
眼前子說得平淡,倒是沒有半分怨氣,他自己在場,如何不懂這些彎彎繞繞。醫院推舉一個平人醫出來當筏子,說白了就是不想惹禍上。可他們為了保全自己居然對他瞞病,也不怕耽誤他將來一生……這群無恥之徒!
不舉之癥……不舉之癥啊!
他霍然想到自己那位過世的老爹,也是年過不漸漸地不能行房,多遭後院背地恥笑,終日鬱郁,沒幾年積鬱積早早去了。
可他要等兩月後才三十五呢!
金顯榮無力癱倒椅子上,再無方才陸曈進門時的意氣風發,如被霜打蔫兒的茄子,臉蒼白著開口:“如此說來,本這不……這病真是不舉之癥?”
不舉之癥從來難治,下山路向來比上山路難走,這些年他邊認識之人,包括他親爹,一旦虛,就如江河日退千里,再無花紅之日。
再說……他自己的,自己心裡也有數。
“大人病與旁不舉之癥不同,表現出來與腎囊癰有幾分相似,若不及時診治,隨著時日流逝,大人會逐漸紅腫加劇,痛難當,直至潰爛,到最後,為了保全命,需得……”回過,目如冰雪沁骨,緩緩流過他腰間,一字一句地開口:“割除壞死之——”
隨著最後一句說完,金顯榮只覺下一涼,彷彿看到了有人拿著薄薄刀片一點點剔除自己下死,頓時從椅子上彈了起來:“這怎麼能行?”
Advertisement
他捂著下半,彷彿現在已被人閹了一般,在屋裡無頭蒼蠅般竄:“找人,本要找最好的醫給本治!不管付多銀子!”
陸曈低頭收拾著醫箱,悠悠道:“醫院指來的醫寧願說謊也不願意告訴大人真相,說明這病對他們來說很棘手,否則也不會換了這麼多人來行診了。”
金顯榮嚷的聲音一滯,心一片冰涼:“這麼說,本這病是不能治了?”
他才三十五,難道就要走他父親的老路?
他還沒活夠呢!
“能治。”
忽然間,他聽到一個仙樂般的聲音。
金顯榮霍然抬頭,就見那位麗的醫站在前,對著他微微一笑:“對他們來說棘手,對我來說還好……不舉之癥雖然麻煩,但也不是無解。”
“真的?”
“當然,畢竟我可是今年太醫局春試紅榜第一。”
猶如地獄重回人間,一剎那,金顯榮看這位年輕的醫,猶如那九天之上雲端瓊樓裡的仙,整個人都發出閃閃金。
若不是他要臉,他都快跪在這子跟前了。
他癱坐在椅子上,著對方聲開口:“陸醫,您要是真能治好我,金銀財寶,隨你挑選。”
子點了點頭,神溫和又從容,彷彿來救苦救難的菩薩,高高在上俯視著無助信徒,在暗裡顯出異樣的彩。
“好啊。”
幽幽道:“不過,大人得照我說的做。”
……
從金府出來時,金顯榮特地讓人重新為陸曈備了一輛馬車,又恭恭敬敬將陸曈送出門,規矩的模樣直讓門房眼珠子差點掉出來。
陸曈揹著醫箱上了馬車,馬車便往街道上駛去。
今日要趕往兩行診,除了金顯榮,還有殿前司的衛。
Advertisement
不過好在翰林醫院離金府與京營殿帥府都不遠,時候也來得及。
馬車搖搖晃晃,駛過盛京街巷,外面傳來市井嘈雜人聲,陸曈的目漸漸悠遠。
金顯榮的確是不舉之癥,不過,倒也沒有說得那般嚴重,不至於真就到了割除死的地步,之所以這樣說,也不過是為了恐嚇他而已。
當初春試出結果,臨出發前,答應替苗良方報復崔岷,也請苗良方幫了一個忙。
請苗良方將自己認識的、悉的宮中人境況、甚至曾生過的病全部記錄下來。
苗良方在宮裡做醫多年,一度曾為院使,宮中人多多都認識,十年過去,一些故人已經不在,但留下來的,悉他們的境況總會使人走許多彎路。
金顯榮……
苗良方與說過,此人好不知節制,風流,年紀輕輕醉心春方房,又常服用溫腎大補之,陸曈還記得苗良方說到此人時的不屑:“我敢說,若他繼續荒唐,不出十五年必然不舉個廢人,同他老子一樣!”
苗良方說得果然沒錯,甚至還沒到十五年,金顯榮就已不行了。
他格外看重自己的男子自尊,又因為金父的原因,對此事十分惶恐,陸曈只要稍一恐嚇,真假參半,便能輕而易舉將他拿。
只要能拿此人,就機會接近戶部……
接近戚玉臺。
外頭的嘈雜聲不知什麼時候輕了,四周變得安靜起來,馬車慢慢地停住,外面傳來車伕的聲音:“小姐,殿帥府到了。”
殿帥府到了。
陸曈挑開車簾,下了馬車。
往裡走去,眼前漸漸出現一大片空地。
不知是演武場還是什麼,角落的兵架上掛滿兵。再往後是小院,院子裡種滿梧桐,正對門前栽著一方紫藤花架,夜雨打溼的落花鋪了一地,甚是芬芳撲鼻。
才走到門口,迎面撞上一個年輕的穿衛服的男子,不知是不是殿前司衛,瞧見也是一愣:“你……”
陸曈道:“我是醫院的陸曈,奉值來行診的。”
衛撓了撓頭,似才看清了陸曈的臉,什麼都沒說,回大步往裡走,邊大聲喚道:“兄弟們都出來,翰林醫院的醫來行診啦!”
聽見靜,從裡三三兩兩走出一群人來,待瞧見陸曈皆是呆了呆,隨即“呼啦”一下全圍上來,熱得簡直人招架不住。
“咦,這是新來的醫嗎?從前怎麼沒見過?”
“我姓李,您貴姓啊?”這是個開朗自報家門的。
“姓陸。”
又有人上前,將方才問話的人到一邊,笑瞇瞇道:“原來是陸醫……您這麼年輕,怎麼就去翰林醫院了?瞧著還沒我妹妹年紀大……您定親了嗎?”
“滾滾滾,陸醫看看我!”說話的人早早挽起袖子,不知是故意還是無心出壯實有力的小臂,高舉著湊到陸曈眼前,“我這幾日都不得勁兒,您給我把把脈,我是不是病了?”
慣來冷寂的殿帥府一下子熱鬧起來,殿前司的衛們各個正值氣方剛的年紀,偏偏整日見的都是小子,陡然瞧見這麼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個個孔雀般爭著上前開屏。害的就遠遠站在一邊看,膽大的更多,這群人將陸曈圍在中間噓寒問暖,又生得瘦弱單薄,一眼過去,簡直尋不到人在何。
只聽得到嘰嘰喳喳的吵鬧聲。
裴雲暎一進門就看到的是這幅場景,皺了皺眉,問靠在角落站著喝茶的蕭逐風:“在幹什麼?”
蕭逐風朝人群努了努:“你的陸醫來行診了。”
裴雲暎一怔。
“託的福,我第一次知道,在殿帥府養鴨子是這種覺。”蕭逐風嘲笑完,放下茶盞,轉出了門。
裴雲暎:“……”
他走到大廳中間,衛們獻殷勤獻得熱火朝天,誰也沒發現他回來了,坐在中間的陸曈正低頭把脈,面前明晃晃著數十隻赤的胳膊,個個故意用力顯出頗有力量的線條,至於那一張張笑得傻氣的臉,像極了每次梔子問段小宴討骨頭時,湊上去對方手指的神。
真是脹眼睛。
實在看不下去,裴雲暎走上前,刀鞘點了點桌:“安靜點。”
再吵下去,旁人聽見還真以為殿帥府改行養鴨子了。
“大人?”
衛們這才瞧見他,忙立起來退到一邊,還有人像是怕他不明白般主解釋:“大人,醫院新來的陸醫來為我們行診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44 章
海棠閒妻
穿越了,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翻雲覆雨的本事,只想平平靜靜過她的懶日子,當個名符其實的閒妻.然而命運卻不給她這樣的機會,爲了兒子,爲了老公,閒妻也可以變成賢妻!家長裡短,親友是非,統統放馬過來,待我接招搞定,一切盡在掌握.
33.5萬字8 24418 -
完結528 章

快穿之太子再虐你一遍
天界的太子殿下生性風流,沾花惹草,天帝一怒之下,將他貶下凡塵,輪回九世,受斷情絕愛之苦。左司命表示:皇太子的命簿…難寫!可憐那小司靈被當作擋箭牌推了出去,夏顏歎息:“虐太子我不敢……”她隻能對自己下狠手,擋箭,跳崖,挖心,換眼……夏顏的原則就是虐他一千,自毀八百!回到天宮之後……夏顏可憐巴巴的說:“太子殿下看我這麽慘的份上,您饒了我吧!”太子:“嗬嗬,你拋棄了孤幾次?”眾人:太子不渣,他愛一個人能愛到骨子裏。
92.1萬字8 11419 -
完結227 章

戀愛腦暴君的白月光
“你爲什麼不對我笑了?” 想捧起她的嬌靨,細吻千萬遍。 天子忌憚謝家兵權,以郡主婚事遮掩栽贓謝家忤逆謀反,誅殺謝家滿門。 謝觀從屍身血海里爬出來,又揮兵而上,踏平皇宮飲恨。 從此再無鮮衣怒馬謝七郎,只有暴厲恣睢的新帝。 如今前朝郡主坐在輪椅上,被獻給新帝解恨。 謝觀睥着沈聆妤的腿,冷笑:“報應。” 人人都以爲她落在新帝手中必是被虐殺的下場,屬下諂媚提議:“剝了人皮給陛下做墊腳毯如何?” 謝觀掀了掀眼皮瞥過來,懶散帶笑:“你要剝皇后的人皮?” 沈聆妤對謝觀而言,是曾經的白月光,也是如今泣血的硃砂痣。 無人知曉,他曾站在陰影裏,瘋癡地愛着她。
35.1萬字8 491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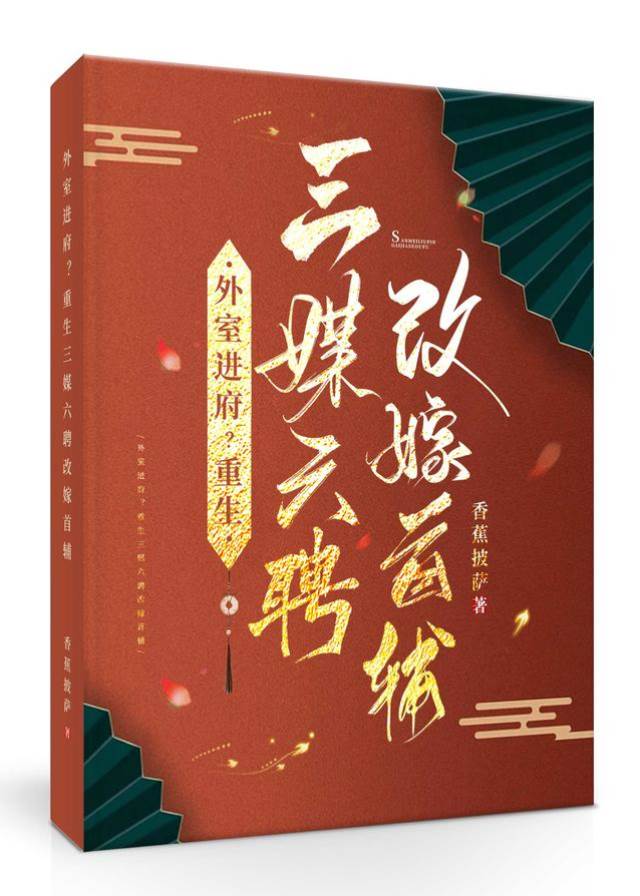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