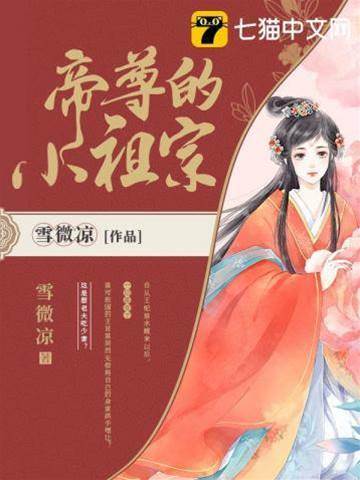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憐嬌奴,禁欲權臣夜夜寵》 第205章 畫上的女孩與穗和一般無二
裴景修頓時變了臉:“小叔懷疑是我安排的嗎,那個藥我不也吃了嗎?”
“你也可以事先服下解藥。”裴硯知說,“或許你在路口遇見我們的時候,已經提前到莊子上安排好了一切。”
裴景修臉越發難看,緒也激起來:“小叔,都這個時候了,我們還要相互猜忌嗎,我擔心穗和不比你,難道我會為了算計你把穗和置於險境,還故意讓人非禮,傷害嗎?”
“誰知道呢?”裴硯知嗤笑一聲,“雖然你是我侄子,但我卻從未看清你,你總能一次又一次顛覆我的認知。”
“……”裴景修無語,悻悻道,“既然小叔不信我的話,我說再多也沒有用,但那個藥我自從服下並無任何異常,想必並非什麼毒藥,而是那護衛用來嚇唬我們的。”
“但願吧!”裴硯知說,“你放心,如果那個藥可以致命,我走的時候會帶上你的,咱們叔侄二人黃泉路上結伴而行。”
裴景修吃驚地看著他,後背一陣發涼。
馬車在府門外停下,阿義開啟車簾說:“大人,到家了。”
Advertisement
裴硯知沒理會目瞪口呆的裴景修,率先下了車。
回到東院,坐在書房裡,有種恍如隔世的覺。
他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枯坐了半晌,一點頭緒都沒有。
想起在莊子上與穗和短暫的溫存,想起他沒有得到答案的表白。
他拉開屜,從裡面拿出那捲畫軸,放在桌子上慢慢鋪開。
畫面上,穿湖藍的孩子靜靜坐著,烏髮遮面,玉足纖纖,一朵鮮豔的蓮花在腳踝綻放。
他說回京後會把這位小姐的故事詳細說與穗和聽,現在,他又覺得,似乎沒有說的必要了。
馬車上裴景修說的那些話,不是沒道理,穗和如果跟了他,不會比跟著裴景修更好。
至跟著裴景修能活命,跟著他,隨時隨地都可能喪命。
他是真的不能有肋。
進場十年,他一直避免讓自己有肋,這不,才剛有了一點苗頭,就被人給牽制住了。
所以,他可能還是更適合一個人。
他盯著畫上的孩子,盯得久了,像是出現了幻覺,孩子的長髮突然被風吹,出半張白如凝脂的容。
Advertisement
那模樣,竟然與穗和一般無二。
裴硯知吃了一驚,忙閉上眼睛甩了甩頭,再睜開眼,畫上的孩子還是原來的樣子,沒有任何變化。
他想他真是魔怔了,看誰都是穗和的樣子。
也不知穗和如今在宮裡是什麼況?
……
皇后的棲宮裡,穗和被安置在了後殿最僻靜的一個房間,皇后派了兩個宮照顧的藥食起居。
皇后說,之所以把安置在這裡,是因為前面一天到晚人來人往,怕擾了養病。
穗和沒有任何發言權,只能默默接。
頭兩天,病得嚴重,躺在床上哪裡都不能去。
劉院判得了皇后的吩咐,一天兩次來給診脈,及時調整藥方。
兩天後,上的疼痛終於減輕了些,可以自己下床在房裡來回走。
兩個宮照顧十分周道,就是嚴得很,無論問什麼都說不知道。
穗和得不到外面的任何訊息,覺自己就像與世隔絕一樣。
又過了兩天,子好了很多,可以走到門外廊下去曬太。
但的活範圍僅限於房前那一小片地方,一旦走得稍遠一些,就會被宮扶回去。
Advertisement
宮負責照顧,同樣也負責監視。
穗和讓宮轉告皇后,說自己現在已經好了,想回家去。
宮拒絕幫轉達,讓安心養著,等病好了,劉院判自然會稟報皇后,皇后自然會派人送。
穗和心裡明白,只要皇帝不想讓走,劉院判永遠都不會說病好了。
不能這樣坐以待斃。
想念大人,也怕大人為了救出去,再做出什麼激怒皇帝的事。
不能總是讓大人為冒險。
猜你喜歡
-
完結1747 章

鬼面梟王:爆寵天才小萌妃
一道圣旨,家族算計,甜萌的她遇上高冷的他,成了他的小王妃,人人都道,西軒國英王丑顏駭人,冷血殘暴,笑她誤入虎口,性命堪危,她卻笑世人一葉障目,愚昧無知,丑顏實則傾城,冷血實則柔情,她只想將他藏起來,不讓人偷窺。 “大冰塊,摘下面具給本王妃瞧瞧!”她撐著下巴口水直流。 “想看?”某人勾唇邪魅道,“那就先付點定金……” 這是甜萌女與腹黑男一路打敵殺怪順帶談情說愛的絕寵搞笑熱血的故事。
316.4萬字8.09 152892 -
完結1039 章
絕寵世子妃
前世被親人欺騙,愛人背叛,她葬身火海,挫骨揚灰。浴火重生,她是無情的虐渣機器。庶妹設計陷害?我先讓你自食惡果!渣男想欺騙感情?我先毀你前程!姨娘想扶正?那我先扶別人上位!父親偏心不公?我自己就是公平!她懲惡徒,撕白蓮,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重活一世,她兇名在外,卻被腹黑狠辣的小侯爺纏上:娘子放心依靠,我為你遮風擋雨。她滿眼問號:? ? ?男人:娘子瞧誰礙眼?為夫替你滅了便是!
196.7萬字7.75 191914 -
完結107 章

蕓蕓卿州
魂穿貧家傻媳婦,家徒四壁,極品後娘貪婪無恥,合謀外人謀她性命。幸而丈夫還算順眼,將就將就還能湊合。懷揣異寶空間,陸清蕓經商致富,養萌娃。鬥極品,治奸商,掙出一片富園寶地。
17萬字8 27651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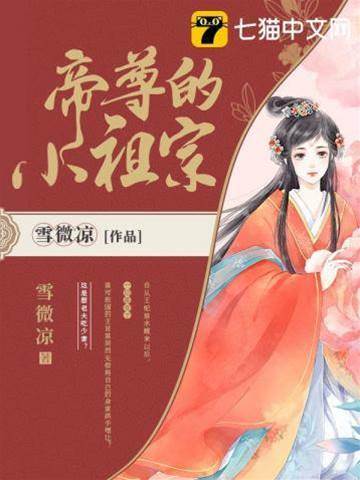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