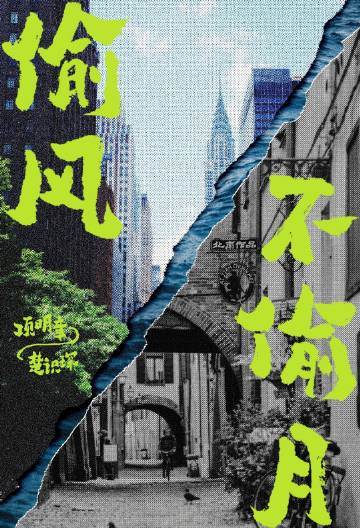《君寵難為》 5-4
木清與生塵不過說了幾句話。生塵臉先是突然變了,兩手用力擺,好像在說“不行”。可是木清卻突然湊近他耳邊,又低聲說了起來——單是他湊近,生塵臉就騰地紅了。開始他還在抗拒,但最后,卻還是點頭了。
等到木清揮揮手,讓生塵離開時,木朗的臉難看得不行。
“一個十幾歲的藥,你也對他做出這種態?阿清,你越來越胡鬧了。”
“怎麼,我對他好,哥哥不高興?”
“那只是個小孩!什麼也不懂,你卻去勾……”勾引兩個字,還是沒說出口。木朗焦躁地看著他,“阿清,你小時候我不在你邊,確實虧待了你。你平時任些,我也不太約束你。可你做事卻不能越來越偏差,總要有些底線……”
“什麼底線?”
那木清卻一下子站起來,“哥哥,你可是要篡位謀反的人——你還以為你是那個大儒生?你是不是還要我跪圣賢相,抄起把戒尺懲戒我?你也知道你虧欠我?嗯?”
“阿清……”
“我告訴你,我偏就討厭姓杜的!什麼杜公子,誰讓他姓杜?到我,算他倒霉!我又沒有要取他命,我只是告訴他,若他肯找一個人替他吃了藥,再喝下那人的,他就不必病癥再現的痛苦——你猜他疼得死去活來時,會不會心?”
“可據我所知,你這一項卻還沒有研究完全。若是那人當真飲了,卻沒有用呢?豈不識破你在害他!”
“我害他什麼?當然是有用的——只不過,他得將那人飲干凈了!他自己喝了,他當然就懂,這藥的劑量不夠,絕對撐不到最后的。所以哥哥,到那時候,他就要自己想辦法哄騙人家給他,甚至將人家綁起來,放喝掉,來讓自己活命!”
Advertisement
木清越說,笑容越,看得出是十分高興。
“誰他姓杜?一般人死就死了。可既然姓杜,我偏偏不讓他死,要他知道自己還有救,只是卻要殺了別人,用那個人的命去換。而且,還要讓他往生路上走了幾步才知道,是要殺人才行的——不過哥哥,你說能下決心喝人的人,肯眼睜睜看著自己去死嗎?我猜,只要走出第一步,他就絕對收不了手!哥哥你看,這樣一出好戲,會不會十分彩?說不定那個替他放學的人是他的父母,兄弟,人……哈哈哈,到那時候,還不一定要釀什麼樣的人倫慘劇呢!”
阿清笑得愈加開心,臉上竟起了一層紅暈。木朗看著自己的弟弟,心里第一次生出了寒意。
……
那一夜雨收風住后,山谷中一片狼藉。誰也沒料到這一場忽如其來的暴雨,竟然這樣來勢洶洶,將谷中樹木都折斷了許多。
“去,給公子送飯。”
淮何不在,秦凌就了侍衛隊的臨時統領。他大咧咧揮揮手,人給李廣寧送飯去。
既然黃大夫發了話,準許李廣寧的人進二百尺,整個侍衛隊就都搬了過來。正好淮何不在,秦凌直接越俎代庖,大手一揮,連伺候的下人也都住進來了。
按理說,這算是僭越行事。但此刻,沒人會挑他的不是——淮何去送信,還未曾歸來。而李廣寧的心,只在杜玉章上。
從昨夜犯病算起,杜玉章已經昏迷了整整十八個時辰了。看他的樣子,似乎還將無休無止地昏迷下去。
李廣寧坐在杜玉章床前,輕輕著那人的頭發。手指從他臉上過,能覺到他輕弱的呼吸,和溫熱的溫。
可除此之外,連一活著的表征都沒有。就連黃大夫的針灸之,也無法再讓他有一點反應——哪怕是眼睫,手指輕擺,都不再有了。
Advertisement
就在這時,一名侍捧著餐盒,敲開了黃大夫的房門。
“公子,用飯了。”
李廣寧并沒有理會。他眼睛一錯不錯地盯著杜玉章的臉。那侍也不敢再勸,跪在地上。
片刻后,黃大夫開口,
“陛下,不如您……”
“玉章究竟何時會醒來?”
李廣寧打斷了黃大夫的話。他聲音低沉,愈發嘶啞,
“昨夜,你不是說,他這一夜無礙的麼?既然無礙,為何現在還不醒過來?嗯?”
“按照昨日的脈象,杜大人確實不該有事。但陛下,我不得不說,杜大人已經頻頻出乎我意料了……你們昨日……”
黃大人猶豫片刻,輕聲問,
“陛下,您昨日真的沒有對他做什麼?”
“黃大夫!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因為杜大人的病,是長期憂傷痛苦淤結在心。因此心境如何,對他病其實有極大的影響。而昨日我初見他時,他還笑容郎朗,甚至能與陛下您,還有那位蘇先生談笑自如。晚間再見,他卻仿佛失去了心中的生念。再之后,就是突然病發——不過短短一日,他的病急轉直下!我行醫這麼多年,也沒見過這種況!所以黃公子,你們昨日究竟發生過什麼?陛下您仔細想想,會不會哪里刺激到了他,他心如死灰,再沒有求生的了?”
“他那樣的子,我怎麼舍得對他如何?昨日我只是送他回去……路上他對我使小子,我也沒……最多,是不自親吻了他!難道一個吻,就能讓他再不想活下去?”
“陛下,就沒有其他線索?”
“他只說我他想起……想起……”
“想起什麼?”
李廣寧滿眼,用力擂向桌面。
“他還不知我份,他只說我他想起……他的仇敵……李廣寧!”
Advertisement
這是李廣寧第一次在黃大夫面前說起他與杜玉章的關系,卻用的是“仇敵”一詞。黃大夫倒一口氣。這一個詞,加上杜玉章上的傷病,似乎給他勾勒出一副腥暗畫卷的一角……
難道這兩人從不曾心心相印,一直都是皇帝陛下的威豪奪?
突然,他想到一個可能,登時驚出一冷汗。黃大夫趕抓起杜玉章手腕——可太過微弱,一時辨不出病虛實。
“怎麼?你想到了什麼?玉章病有變化不?”
“陛下,你可知,杜大人他眼睛并非真的失明,而是服藥導致?”
“你是說過……究竟是誰**害他失明?”
“不是害他,而是救他!這是西蠻薩滿教的路數,恐怕有人曾經用草藥替他延緩病,但是卻產生負作用。雖然能夠制他的病痛,但也導致了他眼睛暫時失明。薩滿教有巫蠱之力,與我們的藥不同……其中復雜難辨我也說不清楚,總之,這副作用與藥效相輔相!”
“你是說……”
“對,若藥效不足以制病,副作用自然煙消云散!現在,杜大人的病洶洶,恐怕他眼睛已經……”
李廣寧聽到此,已經向后退了幾步,直接跌坐在椅子上。難道昨夜玉章已經看到他真容?
——不,不會的!若是他認出自己,怎麼會一點反應也沒有?
——除非……他早就已經知道自己份!
——可就算他早就知道自己份,又怎麼會裝作不知道?這不是玉章的啊……他眼里本不得沙子,從來是一定要爭個是非曲直!要不然,當年怎麼會屢屢激怒自己,吃了那麼多苦頭?
——等等,他也曾心灰意冷,不愿辯駁過!那是……他打定主意赴死之時……是東湖落水前夜……
Advertisement
“玉章!”
李廣寧突然撲到杜玉章床前。他一把握住杜玉章手腕,失聲吼道,
“你是不是昨夜就打定主意,不愿醒來了!”
“陛下!”
黃大夫上來拉他,被他一把揮開,直接推得摔在地上。
“杜玉章!你到底想干什麼!你給我醒過來!就算認出是我又怎麼樣!你趕我走啊!
你恨我不是嗎?你起來啊,醒過來!我在這里,我從前如何對不起你,你報復我啊!你去找那個姓蘇的,去跟他雙宿**!你讓我眼睜睜看著,我不敢對你如何的!你報復我啊,你活著才能報復我——要不然你就再次遠走高飛!再折磨我三年,三十年,讓我晝思夜想,讓我寢食難安,若你還不能心安,你就一把刀捅死我……我給你以命相抵!你給我醒過來!”
“陛下!您不要這樣!”
黃大夫大驚失,卻怎麼也拉不開李廣寧。
——陛下怎麼了!他是不是瘋了!
黃大夫三年多前被關押時,原本聽過徐家軍私下議論,說當今陛下是個生多疑,偏激的人——可這次見面,他沒覺出什麼端倪。
卻為何,現在突然失控了?堂堂皇帝,再怎麼寵一個臣子,哪怕是專寵,又怎麼能說出以命相抵這種話來!若當真如此,天下豈不是要大!
“陛下!別這樣!您松手……杜公子的子經不住您這樣搖晃!陛下!您是想害死杜公子嗎!”
這一句出來,李廣寧終于放手了。他倒退幾步,頹然撐住桌沿。他低下頭,兩只胳膊好像有些支撐不住的重量,一直在抖。連帶著,整個子都有些抖了。
不知為何,黃大夫從他那抖的背影中,似乎看到了一只絕的困……
“黃大夫。”
“陛下?”
“若他真的不肯醒過來……”
李廣寧咬著牙,從齒里出話來,
“你說的那種藥……還能有效果麼?”
“啊?”
黃大夫后退一步,
“陛下三思!老朽說過的,那藥是虎狼之藥,效果雖然好,可用藥之時痛苦萬分!原本杜大人的子就已經虛弱不堪,未見得能撐過三次藥效……何況他已經心生死意,若中途他自己放棄了,說不定就真的……”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辦法?你說出來啊!”
李廣寧雙眼赤紅,用力扼住黃大夫手臂,
“你倒是救他啊!不然該如何……你我眼睜睜看著他死在我面前,再不能醒來嗎?”
猜你喜歡
-
完結221 章

電競團寵Omega
全息电竞联赛是Alpha们的秀场,凋零战队Polaris为了凑齐职业重返赛场,居然招了个第二性别是Omega的巫师。小巫师粉雕玉琢,站在一群人高马大的Alpha选手里都看不见脑袋,时不时还要拽着队长林明翡的衣角。全联盟都觉得昔日魔王林明翡掉下神坛,要笑死他们不偿命。 后来,他们在竞技场里被夏瞳用禁制术捆成一串,小巫师用法杖怼着他们的脑袋一个个敲过去,奶凶奶凶的放狠话:“给我们队长道歉!不道歉的话就把你们全部送回老家!道歉的话......我就唱歌给你们听!” 众俘虏顿感上头:“靠,他好可爱!” - 作为全息电竞行业里唯一的一只Omega,夏瞳不仅是P队的吉祥物,还是所有战队想挖墙脚的对象,迷弟迷妹遍地跑。 拿下联盟赛冠军的第二天,一个西装革履的Alpha敲开了P队俱乐部的大门。 “夏瞳是我走失的定制伴侣,请贵俱乐部即刻归还,让他跟我回去生孩子。” 林明翡赤着精悍的上半身,叼着烟堵着门,强大的信息素如山呼海啸:“你有胆再说一遍?” #让全联盟的团宠给你回去生孩子,你是不是没被人打过! #再说他现在是老子的Omega! 看着沉稳实则切开黑的大帅比X看着傻但打架超狠的小漂亮。 →1V1,苏爽甜,弃文勿告,感谢尊重。 →社会制度游戏规则全是鬼扯,千万别考据。 →求不养肥,养着养着可能就死了...
48.6萬字8 14032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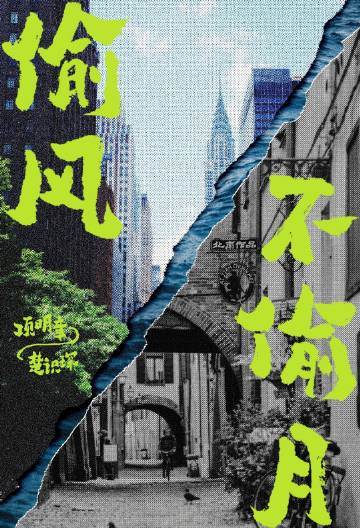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連載136 章

我是卷王穿越者的廢物對照組
時書一頭悶黑從現代身穿到落後古代,爲了活命,他在一個村莊每天干農活掃雞屎餵豬喂牛,兢兢業業,花三個月終於完美融入古代生活。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牛逼了!卻在河岸旁打豬草時不慎衝撞樑王儀仗隊,直接被拉去砍頭。 時書:“?” 時書:“操!” 時書:“這該死的封建社會啊啊啊!” 就在他滿腔悲鳴張嘴亂罵時,樑王世子身旁一位衣著華貴俊逸出塵的男子出列,沉靜打量了他會兒,緩聲道:“學習新思想?” 時書:“……爭做新青年?” 謝無熾面無表情:“6。” 這個朝代,居然、不止、一個、穿越者。 - 同穿古代卻不同命,謝無熾救時書一命。時書感激的找他閒聊:“我已經掌握了這個村子的命脈,你要不要來跟我混?吃飽到死。” 謝無熾看了看眼前衣著襤褸的俊俏少年,淡淡道:“謝了。我在樑王座旁當謀士,生活也挺好。” “……” 感受到智力差距,時書忍了忍:“那你以後要幹嘛?” “古代社會,來都來了,”謝無熾聲調平靜,“當然要搞個皇帝噹噹。” 一心一意打豬草的時書:“…………” - 謝無熾果然心思縝密,心狠手辣。 時書驚慌失措跟在他身旁當小弟,眼睜睜看著他從手無寸鐵的新手村黑戶,積攢勢力,拓展版圖,逐漸成爲能逐鹿天下的雄主。 連時書也沾光躺贏,順風順水。 但突然有一天,時書發現這是個羣穿系統,只有最後達到“天下共主”頭銜,並殺光其他穿越者,才能回到原來的世界。 “……” 一個字:絕。 時書看看身無長物只會抱大腿的自己,再看看身旁手染滔天殺孽、智謀無雙的天子預備役謝無熾。 ——他還不知道這個規則。 時書深吸了一口氣。 當天深夜。 時書拿著一把短刀,衣著清涼,白皙肩頭微露,誠惶誠恐爬了謝無熾的牀。
60.9萬字8 4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