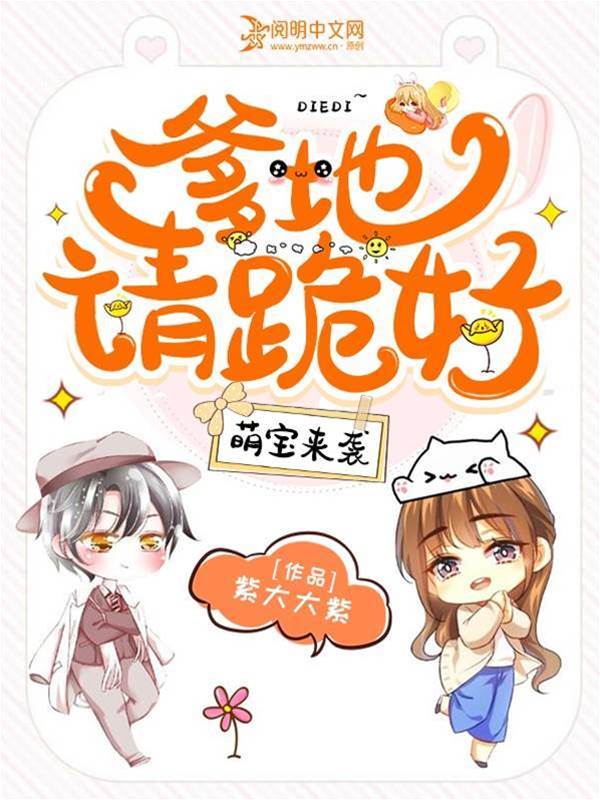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你是我的萬千璀璨》 第326章 崔少變態,是個變態!
br />
崔銀起的話對於鍾繾綣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一想到自己這五年的生活一直在賀誅的注視下,便起了一的皮疙瘩。
搖著頭,人喃喃著,“都這麽久了,他為什麽還是不肯放過我?”
“也許他放不過的是他自己。”
崔銀起將手收回來,意味深長地看著鍾繾綣的臉,隨後說了一句,“我吃飽了,你倆聊吧。”
楚鳶看了一眼崔銀起的盤子,他好像沒吃多,深夜回家,莫不是……匆匆趕回來的?
沒去多想,等到崔銀起一走,鍾繾綣便看向楚鳶,“賀誅這些年在幹什麽?”
“還是那副樣子。”
楚鳶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知道的,賀家一直讓他快點結婚生子,不過賀誅不肯,至於賀守,你也明白的,他更沒有那方麵的心思了,所以現在賀誅是頂著家族的巨大力……”
楚鳶的話音一頓,接著道,“不過那也和你沒有關係,繾綣,你不必自責。”
本就是賀誅犯錯,這樣看來好像是鍾繾綣倒欠了他似的,哪有這樣的理?
所以楚鳶對著鍾繾綣安道,“沒事的,賀誅是個年人,該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鍾繾綣的眼神暗了暗,好像是下定了什麽決心。
這頓晚餐吃完,楚鳶和鍾繾綣一起收拾了餐桌,等到一切都弄幹淨以後,楚鳶找了一間二樓的客臥,很自覺地搬了進去,關門之前招招手,“要是有什麽事記得隨時喊我哦。”
鍾繾綣點頭,也關上了自己主臥的門。
寶寶在另一個寶寶房睡覺,如今臥室裏隻剩下一個人,鍾繾綣歎了口氣,打開了手機。
Advertisement
就在這個時候,門口響起了開門聲,鍾繾綣猛地一個坐起,發現居然是崔銀起不打一聲招呼便進了的臥室!
門一關,崔銀起和鍾繾綣便同時待在了同一個空間裏。
鍾繾綣皺眉,“你來幹什麽?”
崔銀起走到邊上掀開被子,跟上自己的床似的,“你說呢?”
鍾繾綣推了他一把,“楚鳶在外麵呢。”
“那怎麽了,讓看見就看見唄。”
崔銀起說,“你跟我睡一覺就那麽難嗎?”
鍾繾綣眼裏全是抵,“你要把我送回賀誅邊,所以我現在不是很想看見你的臉。”
崔銀起這回哄也不是罵也不是,“我看看你的反應啊。”
鍾繾綣說,“人心窩子好玩嗎?”
說出這話的時候,人的眼裏好像有淚在一閃一閃的,足以證明是真的有被崔銀起吃飯時說的那些話給傷到。
崔銀起原本還滿臉不在乎呢,目及到鍾繾綣的眼角,猛地一頓。
他許久沒說話,隔了好一會,仿佛是咬著牙從牙裏出一句話,“好玩啊。”
鍾繾綣自嘲地笑了一聲,隨後手抹了一把自己的眼睛,“我就知道你這個人是這樣的。”
崔銀起按著的肩膀,將翻過來,但是鍾繾綣不依,固執要翻過去,“你幹嘛啊?我這人什麽樣的?你倒是說清楚啊。”
他有些著急,他也不知道為什麽。
鍾繾綣紅著眼睛說,“還要我誇誇你嗎?崔銀起,在你邊和在賀誅邊,也許對我來說,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崔銀起覺自己的口被人砸了個似的,回過神來的男人無法控製自己的緒,怒氣一下子溢滿了整個腔,他強行把鍾繾綣子扳過來,力道大得讓雙肩生疼,而後崔銀起冷笑著看鍾繾綣,“當初賀誅不就是讓你來討好我嗎?你也知道這種事?我以為這五年你活得太好,都忘記自己原本是什麽貨了呢!”
Advertisement
鍾繾綣疼得悶哼一聲,卻沒有求饒,的手指死死攥在一起,看著眼前的崔銀起,人覺自己像是在遭一場折磨,明明他還沒——可是崔銀起,你帶給我的神上的攻擊,已經令我疲力竭。
鍾繾綣噙著眼淚喊了一聲,“你這麽看不起我那你還問我幹什麽!幹脆直接把我還回去不就好了!也正好還你一個清淨!”
此話一出,崔銀起的呼吸一滯。
鈍鈍的痛覺緩慢從腳底爬上來,他對著鍾繾綣梨花帶雨的臉愣了好久,這幾秒鍾的時間裏,心髒一一的,好像在膨脹,又好像在坍。
還?
不,他不想還。
崔銀起抿,去了一下鍾繾綣的臉,驚覺抖在抖,好像一隻驚弓之鳥,知曉自己下一秒會被箭矢不留餘力地穿心髒。
而拉弓的人,不是賀誅,是他崔銀起。
真該死。
崔銀起捧的手指回來,男人啞著嗓子說了一句,“你別哭行不行?”
鍾繾綣扯著虛偽的笑容問他,“那我這樣笑你滿意嗎?”
崔銀起覺那笑容太刺眼了,心裏也跟著像有針在紮似的,他嘶得了口氣,對著鍾繾綣喃喃著,“鍾繾綣,我不好。”
鍾繾綣的表僵在臉上。
居然能從崔銀起裏聽見這個話,人愣住了。
他居然低啞地對鍾繾綣說,“你別哭,我不好。”
鍾繾綣下意識輕幅度地搖頭,“你又想弄什麽花招?你又覺得這樣逗我很好玩是吧?”
崔銀起深呼吸一口氣,“我tm也不知道為什麽。”
鍾繾綣的眼淚快幹了,崔銀起才敢再的臉,“你要問我為什麽,老子tm也不知道!反正你別哭了,你再哭,我真把你送回去。”
Advertisement
說完這個,他還直接掏出了手機,“你再敢在我麵前掉一滴眼淚,我就直接給賀誅撥通電話。”
豈料鍾繾綣麻木又疲憊地看著他,“你別威脅我了,你撥通吧。”
崔銀起登時心裏一,一窒息浮上頭,他竟然有些不可置信地問,“你……你難道……是真的想回去他邊嗎?五年了,你還沒忘記嗎?”
鍾繾綣說,“忘記?怎麽忘記啊,把我人生變一灘爛泥的人,恰好是他和你。”
他和你。
崔銀起指著自己,“我也是嗎?”
“不然呢。”
鍾繾綣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意,“你們為什麽不我又不肯放過我呢?”
崔銀起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回答是他也不知道。
沒有回答,隻有沉默。
隔了一會,崔銀起說,“你是賀誅,還是……恨賀誅。”
“你說呢。”
鍾繾綣眼睛通紅,那眼裏的緒呼之出,強烈洶湧到了崔銀起都……不敢和對視的地步。
說,“殺人不犯法就好了,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們通通……殺。”
意也好,恨意也好,原來在閾值最巔峰的那一秒,和殺意毫無分別。
崔銀起說,“這五年你呆在我邊,一直抱著……這樣的想法嗎?”
“對啊。”鍾繾綣看著崔銀起那張白皙致的臉,這一次,換作主去他,“每一次你躺在我邊的時候,我都想過,如果把手放在你脖子上用力收會是什麽樣呢?崔銀起,如果眼前的人不是你,是賀誅的話……”
是賀誅的話……
Advertisement
鍾繾綣將手就這麽直接放在了崔銀起的脖子上,可是沒有力氣收,本不會那麽做,那等於再拖人下水。
世界上傷的人已經太多了。
沒辦法再去製造額外的悲劇。
哪怕也是悲劇之一。
痛苦地搖著頭,無助地哭喊著,“是賀誅或者是你的話,就算被我殺了,世人也會原諒我的吧!”
崔銀起的心像是被人挖出來了似的,疼得他倒一口涼氣。
怎麽會這樣。
他帶著鍾繾綣逃離了賀誅的控製,這五年,他也不止一次和同床共枕,雖然他沒,但是一起睡覺,已經足夠曖昧。
原來每一次,鍾繾綣都是這樣睜著眼懷揣著殺意一直到半夜。
他和一個想要親手殺了自己的人,相了五年。
崔銀起輕聲低語,“鍾繾綣,你可一點不比賀誅遜呀。”
你簡直是他完的……卑劣的複刻。
漂亮,忍,狠,卻又充滿了肋。
崔銀起竟然直接將手放在了鍾繾綣的手腕上,另一隻手覆著的手背,教如何掌控力道,他說,“沒關係的。”
沒關係的。
鍾繾綣隻覺得這句話心驚跳,說要掐死他,而他說,沒關係的。
崔銀起一不地直視著鍾繾綣的眼睛,仿佛是在宣讀一場死亡宣告,他說,“你試試收一點呢?至那種覺我用的,鍾繾綣,你的刺,讓我很舒服。”
鍾繾綣電似的把手收回來,卻被崔銀起攥得很,說,“你瘋了!”
崔銀起說,“要不然呢?你以為我說那些話刺激你是為什麽?賀誅五年了還在找你,老子tm被惡心壞了!聽不懂人話嗎!”
聽不懂人話嗎!
鍾繾綣抿,“賀誅找我,跟你有什麽關係?你憑什麽因為這種事就遷怒我!”
跟他有什麽關係?
崔銀起抓著鍾繾綣的手,強製用力扼住了自己的嚨,而後他的大手著鍾繾綣的小手收,連帶著鍾繾綣的指頭也加重力道鉗住了他自己的頭。
強製的,狂的,又一塌糊塗的,他們的手以這樣的作十指錯,互相糾纏施。
“你不是想嗎?”崔銀起問,“你不是一直想這樣嗎?”
鍾繾綣用力地開手,渾發抖,手指頭都在,“夠了!”
崔銀起是個瘋子!
猜你喜歡
-
完結759 章

慕川向晚
千年難得一遇的寫作廢柴向晚,因為書撲成了狗,被逼相親。 “媽,不是身高一米九腹肌十六塊住八十八層別墅從八百米大床上醒來的國家級高富帥,一律不要。” “……你是準備嫁蜈蚣?” 后來向晚終于如愿以償。 他被國家級高富帥找上門來了,撲街的書也突然爆火—— 有人按她書中情節,一比一復制了一樁命案。 而她與國家級高富帥第一次碰撞,就把人家給夾傷了…… …… 愛情、親情、倫理、懸疑、你要的這里都有,色香味俱全。 【本文狂撒狗血,太過較真的勿來。】
178.1萬字8.09 16781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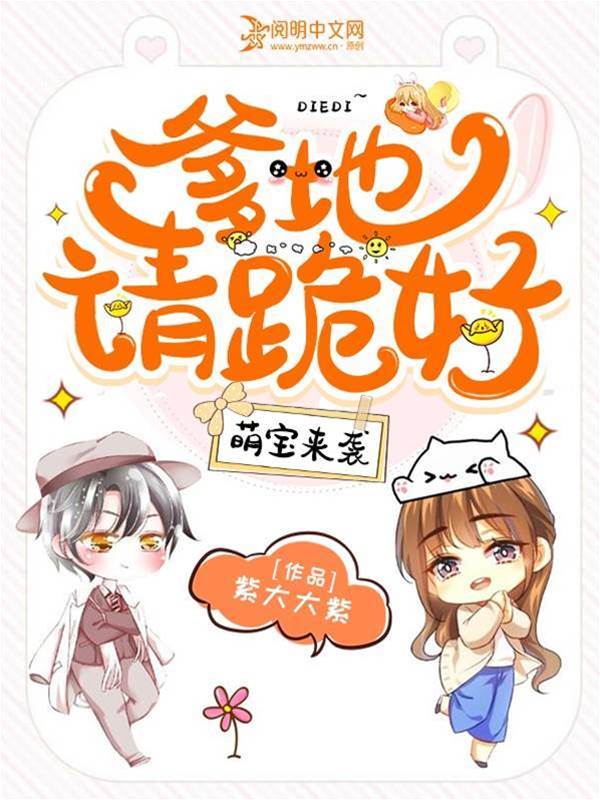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連載339 章

小啞妻死後,千億總裁在墓前哭成狗
一紙離婚協議,喬明月挺著八個月的肚子被趕出薄家。卻不幸遇到車禍,她瀕臨死亡之際,才想到自己的真實身份,不是啞巴,更不醜,而是名動雲城的喬家大小姐!她憤恨、不甘,最終選擇帶著孩子獨自生活,順便虐渣打臉。誰知五年後,孩子的親生父親卻回到雲城,甚至還想讓她嫁給別人!喬明月冷哼一聲,磨刀霍霍預備宰向豬羊!多年後,薄時琛懊悔不已,本該是他的妻,卻兜兜轉轉那麼多年,才重回他的懷抱。
61萬字8 6030 -
完結142 章

他等我分手很久了
莊斐和男友,以及男友的好兄弟陳瑜清共同創立了家公司。陳瑜清以技術入股,對經營的事一概不問。 莊斐和男友經營理念出了分歧,經常意見相左。每每這時,他們就要徵求陳瑜清的意見,試圖以少數服從多數來讓對方妥協。 可陳瑜清總是沒意見,來回就那麼幾句——“隨便。”“你們定。”“我怎麼樣都行。” 他甚至還能幫他們關上會議室的門,懶洋洋地站在門口喊:“你們先吵,吵完了叫我。” - 莊斐離職,幾個要好的同事爲她舉辦了一場狂熱的歡送會。一慶仲裁庭裁決拖欠多年的勞動報酬到手,獲賠高額賠償金;二慶擺脫渣男,恢復自由之身。 森林酒吧裏,渣男的好兄弟陳瑜清不請自來。 莊斐喝醉了,姿態嬌媚地勾着陳瑜清的脖子:“反正你怎麼樣都行,不如你叛了他來幫我?” 不料,厭世主陳瑜清反手扣住她的下巴,毫不客氣地親了下去,無視一羣看呆了的朋友。 他側在她耳邊低語:“既然你那麼恨他,不如我叛他叛個徹底?”
21.4萬字8.18 7874 -
連載455 章

終極火力
這個世界不只是普通人熟知的模樣,還有個常人不會接觸的地下世界。政府特工在暗中處理麻煩,財閥雇養的殺手在私下解決問題。有殺手,傭兵,軍火商,還有特工,有把這個世界
99.5萬字8.18 30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