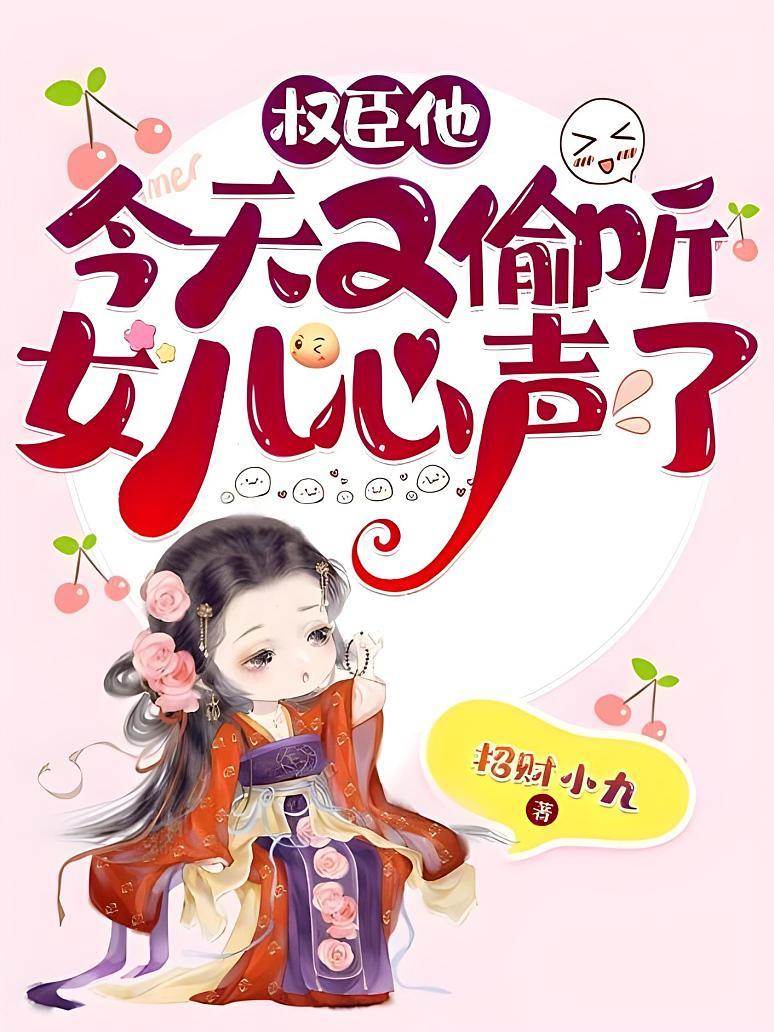《小庶女》 第72章 第72章
江北秋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徊。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映來。——《江上》王安石。
通州口岸依舊忙碌,舉凡上京述職,商販、讀書人,上京通道多源於此,有上京而來,也有出京的人,只此時,前面幾座婚船在岸邊不停的在搬嫁妝,因此後面的車馬行人全都被堵著了。
本來等也就等著,但不知道是誰開始抱怨著,一個接一個的都抱怨起來。
頓時,那婚船上一位管家模樣的出來道歉,還十分會做人的在旁邊茶寮給被堵塞的行人都送了一盞紫蘇飲。
一輛寬闊蓋馬車上,一對青年夫妻也接過這茶飲,都相視一笑。
這對夫妻正是雲驪和裴度。
端午過後幾日,裴度的詔命下來,他和裴夫人說了想攜家眷赴任,裴夫人問過雲驪后,知曉雲驪願意去,於是就同意了。
把家裡的嫁妝打理托給雪柳夫妻和素文魏田一家,收拾好行李箱籠,夫妻二人就出發了。
雲驪吃了一口熱飲,不道:「這還是我長大以來,頭一回出遠門,沒想到還要熱飲子喝。只是不能喝多了,要不然這裡可沒有五穀迴之所。」
大抵和裴度悉很多了,雲驪覺得自己說話沒有一開始那麼保持完那麼拘謹了。
五穀迴之所?裴度朗聲笑道:「知道了。」
旅途寂寞,有個伴兒就是好。
好一會兒,車馬能夠彈了,大抵是馬車外掛著銜牌,不停有人想過來搭話。雲驪非常新奇,以前往來勛貴之家,不知道原來員出行,甚至舉人出行都能打牌,像裴度就掛著丁寅舉人、乙未會元、狀元及第、欽點通判。
他們雇的一條商船,是裴夫人幫忙打點的,還怕們小夫妻不通庶務,特地把心腹尤大夫妻派了來,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
Advertisement
雲驪也就帶了服侍的四個丫頭,並素文夫妻六個人伺候。
「到了,我們上船去吧。」裴度扶著雲驪下馬。
船一共有兩層,尖尖的頭,聽說這種船跑的很快,正常兩個月要到的,這樣的船要一個月不到就能到升州。
茜紅和青手腳麻利的把起居之收拾好后,雲驪則在旁拿出一套茶,親自點了一杯茶,茶香裊裊,裴度亦是賞心悅目。
「嘗嘗我點的茶如何?」遞給裴度。
裴度呷了一口,「甚好,茶醇香,還有茶點也好吃。」
雲驪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又往室走進去,則對丫鬟們道:「你們也先去收拾你們的行李,再讓廚下早些造飯,大家一早就往通州來,也累倦了,也都歇息好,不必伺候。」
人走了,裴度才進來。
無人,雲驪才張開胳膊:「抱抱。」
這婚半個月,裴度才知曉一個人能什麼樣了,真的是平日在外要說多正經就多正經,在房裡只有們倆在的時候,他都招架不住。
見他摟住自己,雲驪順勢坐在他上,起初他還很不適應,現在越發得心應手了。
「怎麼了?」裴度問道。
雲驪嘆了口氣:「我姨娘是在杭州投水自盡的,升州離杭州很近,我想到時候去杭州寺廟再替我姨娘點一盞長明燈,立一個冠冢,四時八節派人去灑掃,這樣總會讓我姨娘泉下也有供奉,不至於肚子。」
爹雖然曾經寵幸過劉姨娘,但總不會回來為一個姨娘做什麼,能做水陸道場還是寫信懇求的,因此姨娘的事只能靠自己了。
裴度點頭:「岳母的事等我們在升州安頓好了,我就帶你親自去杭州立一個冠冢。」
他想妻子真的非常有孝心,不僅對養在膝下的章家大房孝順至極,在自家對自己的母親,也是態度恭敬,就是對生母也是孝心可嘉。
Advertisement
「你最好了。」雲驪窩在他懷裡,靜靜的聽他的心跳。
船上的生活很單調,雲驪卻很愜意,因為終於不必日忙庶務,可以安靜的看書了,裴度則和帶著的師爺們在一樓談天說地,籌謀上任之事。
茜紅進來道:「大,您還記得咱們在通州口岸看到的那艘喜船嗎?」
雲驪笑道:「當然記得,那船吃水極深,又高大,恐怕新娘子的嫁妝很多呢。」
「誰說不是呢,正好奴婢方才在外邊見到那艘喜船行駛到咱們家的船旁邊了,嗬,您是沒瞧見,好傢夥,那船上的護衛足足有五六十個之多呢。」
這茜紅是王忠家的孫,以前就時常被雲驪派去打探信息,以至於這丫頭每到一,必定先打探四周況。
雲驪聽了茜紅的話,甚是好奇:「只是嫁人而已,為何要那麼些護衛?難道是為了怕婚船被劫。」
這也不是沒可能,就雲驪們船上也請了十數個護衛保護呢。
茜紅想來想去也只有這個理由了。
到了晚上,夜已深沉,房中雲驪和裴度二人云雨初歇,們新婚夫妻,不一般,雖然雲驪自覺要節制一些,裴度也不會日日翻紅浪,但到底很容易一下就被撥上了。
此時,不遠傳來簫聲,這聲音如訴如泣,雲驪聽了忍不住都潸然淚下。
「這必定是吹給哪個他喜歡的姑娘的?」
裴度笑道:「你怎地知曉就是男子呢?」
「閨閣子吹簫不大雅觀,一般先生都會讓你學琴,那樣彈起來更好看。而且,我就是聽的出來,這是男子吹的,多半和子無緣,才會有此思。」
就在此時又有琴聲傳來,那琴聲似乎在和著簫聲。
迷迷糊糊中,琴聲戛然而止。
「那琴聲像是咱們旁邊喜船上傳來的。」雲驪從被窩裡揪出腦袋。
Advertisement
裴度用手直接按住的臉,無的說了倆字:「睡覺。」
「哼。」雲驪生氣他不和自己說話。
……
一大早起來,邊早已無人,現在不必請安,雲驪當然不必那麼早起來,整個人也非常鬆弛,梳洗完,又在二樓欄桿邊憑欄眺。
河道寬闊浩渺,一無垠。
不知道是不是從京中出來了,的心也好了很多,為何世人喜歡說什麼男子心寬廣,子心眼就小。說白了,還不是男人出門的機會多一些,子終日只能困囿於后宅,現在能夠單獨這般沒有長輩跟著,已經比很多人強了。
對面的喜船的窗欞被打開了,因雲驪和們二樓對著,那邊窗戶一打開,雲驪發現的窗戶居然被釘了一條條木條,一隻手都不出來。
窗戶旁約站著一位著紅的新娘子,臉上神鬱鬱寡歡。
聯想起昨天晚上的琴聲,似乎猜到了一些什麼。
船靠岸補給,玉通過來傳話:「大,大爺讓小的過來傳話說船靠岸了,問您有沒有什麼要買的?可以帶下人出去買些。」
咦?可以出門嗎?
雲驪趕戴上帷帽帶著幾個丫頭,匆匆下樓去,裴度正等在此。
「這裡雖然只是個小鎮,但是來往船隻都在此停泊換質,因此南來北往什麼東西都有。」裴度介紹道。
他當年上京趕考,是經過此地的。
只要能出門,就十分高興,哪裡還管那麼多。
「走吧走吧。」雲驪推著他。
裴度失笑,但看著愉悅的跟小雀兒似的,也不忍苛責什麼了。
自從出京了,小妻子就變得活潑許多了,和之前在宅子里判若兩人,那時的笑不齒,一言一行合乎規範,私下倒是和自己撒,但是大面上,又是那般。
Advertisement
還好這一出來,就鬆快許多了。
下了船后,四周的賣聲彷彿像置於清明上河圖一樣,畫卷里的人都活了過來,什麼宅紛爭全都沒了。
有賣炊餅脆梨的,有賣花兒朵兒的,還有賣羊簽子、胡餅以及有貨郎,他的貨擔上是應有盡有,更別提往遠走,有各種茶寮、書店、綢店、胭脂水。
更有子大大方方的在街邊賣餛飩,餛飩鋪子前面正有兩個男孩兒在唱蓮花落,旁邊圍著的還有雜耍的。
雲驪悄悄拉了一下裴度的袖子,指了指前面:「那是耍大刀的,對不對?」
裴度點頭:「自然,那就是耍刀的,江湖人靠這個吃飯。」
但是,他正道:「咱們就不過去了,這些地方龍蛇混雜,你萬一被拍花子的拍走了,如何是好?」
拍花子的?雲驪瞬時乖巧道:「好,絕對不跟著去。」
是很懂事的,一聽說不,就聽話了。
裴度見如此,又十分心疼道:「你看這上頭有茶樓,咱們上去找一間臨窗的,你可以在那兒看。」
「好。」雲驪拍手稱好。
不懷疑裴度騙,因為也並非懵懂無知,們姻親就買過一個孩子做妾,聽說那個孩子就是從好人家拐走的,連自己家是哪兒都不知道了。還有秦樓楚館的兒,有一部分是走投無路,還有不是四拐賣賣進去的。
甚至上京燈會,有位家千金就因為和家人走散了,被人拐了去,後來找到時,聽說已經失了清白。
因此,章家燈會從來不許們出去,唯一出去玩兒的還是那次去莊子上騎馬,要不就是小時候過寒食節能出去。
們進的是這間茶樓的雅間,雲驪靠著窗戶坐下,往下看雜耍,都捨不得扭頭吃一口茶。
「沒想到你這般喜歡這市井生活?」裴度很驚訝。
他覺得以雲驪的才,優雅,喜歡的一定是巧的園林,絕非是這樣過分熱鬧的街道。
雲驪倒是很有自知之明:「那是因為這些熱鬧是我不曾接過的,若我其中,也未必就真的喜歡。不過……」想起那個窗戶都被釘住的新娘子,有些同道:「不管如何,自由才最重要。」
「他們為錢財奔波,看似自由,其實也並不自由。」裴度一語中的。
看似行走江湖,瀟灑自如,可為了生計奔波,無一日能想到自己到底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又算什麼自由。
雲驪覺得和裴度說話很痛快,他常常一針見,對事看的很,不加遮掩。
笑道:「說的也是,只能祝我夫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了。」
裴度舉杯,對這話倒是很用。
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學而優則仕,這是所有士子的心愿。
二人還說話,只聽外邊有人過來站在外頭道:「里可是子珩年兄?」
裴度對雲驪道:「我去去就來。」
雲驪點頭。
四周丫頭們都守在邊,也沒什麼好怕的,只是雜耍的人已經開始要打賞了,雲驪讓下人出去也打賞一番,就把隨帶的出在此看。
而裴度則出去發現是他上科的同年馬如龍,如今準備去襄州谷城做縣令,當初自己中了二甲第三十六名,他中的是三甲,已經外放做了三年縣令,現下去谷城又是做縣令。
他了酒菜歌舞,這茶樓老闆也是人,知曉樓上是兩名員,還送了一對胡姬過來跳舞助興。
裴度見馬如龍癡迷的看著那胡姬擺腰肢,不由笑道:「如今你也變壞了,我記得當初咱們一道上京,你說子都是老虎,會吃男人的,如今倒好堪稱場中人啊。」
馬如龍聽了這話,呷了一口酒,嘖了一下:「子珩啊,你再次科舉又大魁天下,這一授就是通判一職,不知道我們的苦啊。山高苦寒之地,若不為自己找些樂子,這日子怎麼過?我家貧,不似你們宦子弟,去秦樓楚館消遣是家常便飯,我們當初不去,也是畏,我們這些寒門子弟也怕丟醜。我還是好的,不過只有兩三房妾侍,也是為了香火,老孫你知道吧,他更是更厲害了。」
裴度聽到秦樓楚館,雖然雲驪不在邊,他立即澄清道:「馬兄,你可別把我和別人弄混了,我當年也只是去過樊樓詩會,至於秦樓楚館可沒去過。」
「至於你,還是要專心仕途才行,酒傷。」裴度拍拍他的肩膀安。
猜你喜歡
-
完結1881 章

鬼帝毒妃:逆天廢材大姐大
她被夫君與徒弟所害,一朝穿越重生,醜女變天仙! 她有逆天金手指,皇族宗門齊討好,各路天才成小弟! 戲渣父鬥姨娘虐庶妹,玩殘人渣未婚夫!他明明是妖豔絕代、玄術強悍的鬼帝,卻視她如命,“丫頭,不許再勾引其他男人!”
339.8萬字8 166366 -
完結607 章

獨占金枝
齏玉鲙、華服羅裳,肆意一生。 安國公府世子季崇言簡在帝心、城府極深,素有長安第一公子的美譽,走了一趟寶陵城,一向自視身高的他目光卻落在了那個斜風細雨撐傘的女子身上。 季崇言看的目不轉睛,感慨不已:“真是冰肌玉骨、步步生蓮。” 隨從大驚:此女身形壯如小山,世子是不是眼睛出毛病了?...
172.7萬字8 6359 -
完結206 章

公府嬌媳
謝知筠出身名門,千金之軀。 一朝聯姻,她嫁給了肅國公府的小公爺衛戟。 衛戟出身草芥,但劍眉星目,俊若繁星,又戰功赫赫,是一時的佳婿之選。 然而,謝知筠嫌棄衛戟經沙場,如刀戟冷酷,從床闈到日常都毫不體貼。 衛戟覺得她那嬌矜樣子特別有趣,故意逗她:「把瑯嬛第一美人娶回家,不能碰,難道還要供著?」 「……滾出去」 在又一次被衛戟索取無度,渾身酸痛的謝知筠做了一場夢。 夢裏,這個只會氣她的男人死了,再沒人替她,替百姓遮風擋雨。 醒來以後,看著身邊的高大男人,謝知筠難得沒有生氣。 只是想要挽救衛戟的性命,似乎只能依靠一場又一場的歡喜事。 她恨得牙癢,張嘴咬了衛戟一口,決定抗爭一把。 「狗男人……再弄疼我,我就休夫」
38.7萬字8 11279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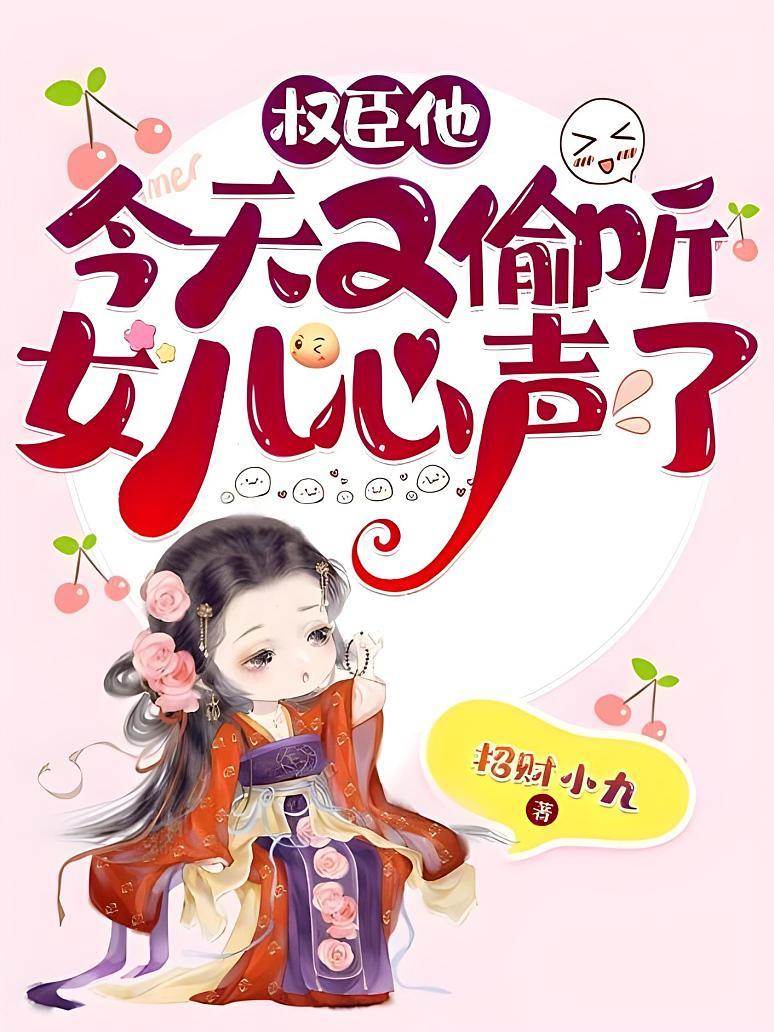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