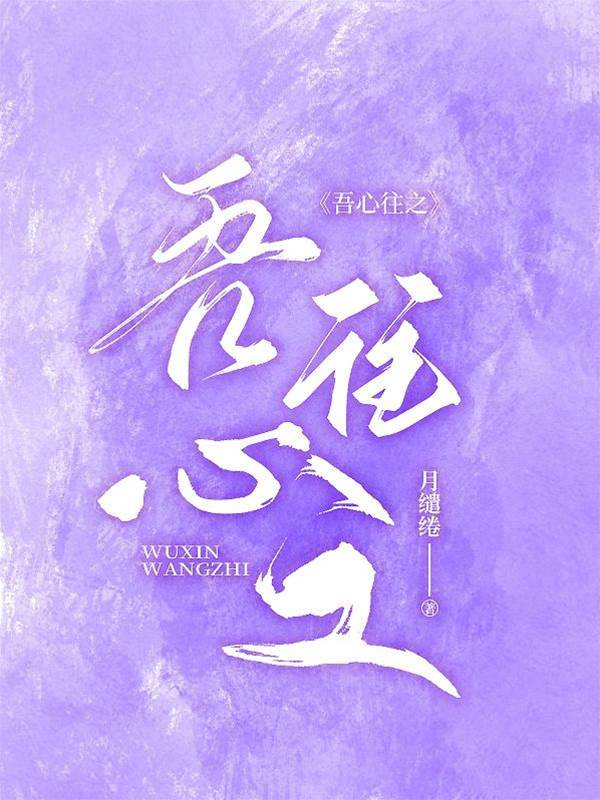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我吻星河》 第58章 第 56 章
午後溫暖耀眼的落進來,綿延在兩人腳下,在木地板上影拓出兩道一高一矮相擁的影,偌大靜謐的書房,靜得似乎只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
祝星燃愣愣地注視著手中的照片,白指尖不自覺收了力道,泛紅的眼眶頓時起了霧。
也就是說,幾年前的那個傍晚,霍庭恩不僅去了的學校,還作為觀眾,觀看了的畢業演出。
可是,這件事卻從未聽他提起。
祝星燃咽了咽發的嚨,心深彷彿下起了一場的雨,心口的位置酸酸脹脹,被什麼東西著,握著手中的書,眼尾溢出晶瑩的水:「.....你怎麼從沒告訴我?」
就連這本《黃粱一夢》,他或許都看了很多遍。
霍庭恩幽暗深邃的目落在照片上,著孩那抹倩麗高挑的影,他的眼神都變得,如今回憶起祝星燃的畢業演出,記憶如水般用來,如電影鏡頭,一幀一幀在腦海中重現,仍無比清晰。
舞臺上的明艷生,芒萬丈,似乎生來就屬於舞臺。
霍庭恩自後抱著,低低埋首在老婆的肩窩,親昵地蹭了蹭,溫熱的息輕吐:「這些都不重要了。」
已經過去這麼久,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霍庭恩對祝星燃的,從未變過,甚至隨著時間的流轉,埋在心底的那顆種子早就悄悄發芽,如今已經長參天大樹。
祝星燃搖頭,轉向他,黑亮明澈的杏眸漉漉的,浸滿了水霧,此時小巧的鼻尖都紅彤彤的,吸了吸鼻子,一字一頓,無比認真地說:「不,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祝星燃從未想過,在自己看不見的角落,原來有個人一直都在後,默默關注著。
Advertisement
對上人堅定的眼神,霍庭恩的心臟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了一把,他薄掀,溫磁沉微啞的聲線溫地不像話:「好,你想知道什麼,我都告訴你。」
祝星燃眨了眨酸的眼睛,努力將眼眶裡的淚水回去,輕聲問:「你為什麼會留著這張照片?」
霍庭恩緩緩勾,沒有毫瞞,只有簡單的四個字:「因為喜歡。」
祝星燃神微怔,竟然對此沒有任何察覺,之前曾問過他,什麼時候對心的,霍庭恩只說比訂婚時要早。
「所以,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嗎?」抿,問得小心翼翼。
祝星燃睜大黑白分明的杏眼,一眨不眨地向他,眸瀲灧流轉,似乎有某種希冀,讓意外的是,面前的男人竟笑著搖頭,漆黑深邃的眼眸溫而專註。
他頓了頓,認真問:「還記得祝明鄴的那場生日晚宴嗎?」
祝星燃還以為是今年,直到霍庭恩提到一個久遠的時間點,眸微頓,似乎已經回憶起什麼,心臟隨之重重跳了一下。
點頭,聲線而清晰:「記得。」
祝星燃被接回京都的第一年,因為和祝蘭萱不和,祝星燃曾在霍庭恩的莊園暫住過一段時間,每天很說話,努力將自己的存在降到最低,雖然與霍庭恩同住一個屋檐下,但兩人的集卻得可憐。
直到祝星燃被祝明鄴接回祝家,兩人說話的次數也屈指可數,霍庭恩眼裡的祝星燃,膽子小,沉默寡言,雖有一雙漂亮乾淨的眼睛,可看向他時總怯生生的,帶著陌生而警惕的敬畏。
霍庭恩對的印象僅限於此,甚至偶爾回憶起,也只能想到這位祝家大小姐被自己養在邊的獵犬嚇出眼淚,花容失的模樣。
Advertisement
後來,祝家的生意如日中天,那段時間也正是祝明鄴最意氣發的時候,他大辦自己的生辰晚宴,借著機會邀請了諸多商界名流,霍庭恩自然也在其中。
那天的祝家大宅賓客眾多,霍庭恩一到場,便是眾星捧月般的存在,冠楚楚的祝明鄴則牽著自己的小兒祝蘭萱給大家一一介紹認識,任誰看了都會覺得父倆深厚,家庭和睦,以至於霍庭恩懷疑自己失憶,祝家只有祝蘭萱一個兒,並沒有祝星燃這號人的存在。
而祝明鄴言語間也隻字不提「祝星燃」三個字,後來前來敬酒的人實在太多,霍庭恩卻毫沒有喝酒的雅興,冷冷淡淡地一一婉拒,目搜尋了一遍宴會大廳,沒有看到那抹悉的影。
霍庭恩只覺得場太悶,隨即放下酒杯離開會客廳,不知不覺閑逛到了花園。
雖然那個夜晚距今已經好多年,可霍庭恩到現在都記得那晚的月亮比任何時候都要皎潔明亮,濃稠靜謐的夜幕之下,激烈尖銳的爭吵自花園旁的偏廳傳來,是兩道年輕子的吵鬧聲,霍庭恩循聲去,目所及之出現兩抹正在對峙的影,其中一道悉的背影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孩背影清瘦高挑,穿著一襲香檳的紗禮服,微卷的長發披散在肩側,鎖骨的線條若若現,白勝雪,偏廳的祝星燃沒有平日里的膽小怯懦,此時冷著臉,漆黑剔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著面前的祝蘭萱,眼神沒有毫溫度,宛若一隻蠢蠢的小,隨時都會出自己尖銳的爪牙。
由於距離遠,霍庭恩並未聽清楚兩個孩因何事而發生爭執,只見祝蘭萱揚著下,一副趾高氣昂的模樣,正對祝星燃說著什麼,眼神輕蔑而充滿諷刺,祝星燃面平靜地回應,置於側的拳卻攥得很。
Advertisement
然而就在祝星燃開口沒多久,祝蘭萱似被激怒,上前一步,氣急敗壞地猛推了祝星燃一把,舉止囂張跋扈。
霍庭恩長眉輕挑,好整以暇地目睹這場鬧劇,俊臉無波無瀾,剛才還在賓客面前端莊有禮的祝家千金祝蘭萱,私底下還有另外一副面孔,像極了大街上撒潑的中年大嬸。
祝星燃則死死地盯著對方,就在霍庭恩以為這姑娘不敢反抗的時候,只見白白凈凈的孩鼓著腮幫子,像只炸了的小,憤怒地朝祝蘭萱撲過去。
兩人同時栽倒在地毯上,厚重的禮服糾纏在一起,祝星燃一把扯住祝蘭萱抹禮服上的蝴蝶結,就算被人撕扯住頭髮也不肯鬆手。
霍庭恩薄微抿,心底終於掀起一層波瀾,竟然開始擔心祝星燃會不會吃虧,然而下一秒,那個被他一直認為膽小怯懦的姑娘,逮著一機會,張直接咬在祝蘭萱揮過去的胳膊上。
祝星燃頂著糟糟的頭髮,死死的在祝蘭萱上,像個小瘋子,早已不顧及形象,全然沒有表面看起來那般弱不風,不堪一擊。
霍庭恩注視著偏廳的鬧劇,神若有所思,直到祝夫人帶著祝明鄴和其他人趕過去。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不由分說一把將祝星燃推開,夫妻倆連忙扶起地上的祝蘭萱,仔細檢查兒上的傷口,當看到祝蘭萱上的傷痕時,祝明鄴陡然間變了臉,眉心鎖,接著就朝祝星燃揚起了掌。
那一瞬,被推倒在地的孩都在哆嗦,卻睜著圓澄泛紅的眸子,一點也不肯服,就這樣倔強地盯著自己的父親。
看到祝明鄴揚起的掌,霍庭恩眸深斂,眼底緒不明,祝明鄴的臉瞬息萬變,掌卻停在半空,遲遲沒有揮過去,可一旁的祝夫人卻不依不饒,就這樣當著偏廳所有人的面,重重扇了祝星燃一掌。
Advertisement
孩被打得偏過腦袋,單薄纖瘦的輕晃了一下,霍庭恩臉漸冷,清雋的眉眼間蹙起一道褶皺。
後來,這場鬧劇終於平息,祝星燃被祝明鄴關在臥室關閉,整場晚宴,都不能離開自己的房間,就連霍庭恩之後再問起,祝明鄴也只是雲淡風輕地說,大兒不適,不方便見客人。
晚宴還在進行中,祝星燃被打的影卻一直在霍庭恩腦海中揮之不去,他鬼使神差地又去了那個花園,花園上方的二樓,正是祝星燃的臥室。
那晚,霍庭恩在花園沉默地佇立許久,就連他自己都未想清楚,為什麼要站在這。
他抬眸向二樓那間亮著燈的臥室,晚風過窗戶,輕輕吹白的窗簾,霍庭恩腦中浮現出無數種可能,都與祝星燃相關,不知是不是正哭鼻子,亦或者,正籌劃著如何「越獄」。
正當霍庭恩思索時,二樓的落地窗忽然被人推開,跟著一抹悉輕盈的影出現在他視野中。
二樓臺,已經換下禮服的祝星燃著一套輕便的白T休閑裝,烏黑的長發紮一束馬尾,小臉瑩白清麗,此時拉著臺向下張。
霍庭恩抬眸,兩人的視線隔空相撞。
祝星燃眼神微頓,似乎一眼就認出他來,黛眉輕蹙,但並未理會,垂眸看了眼二樓到地面的距離,像在計劃著什麼。
霍庭恩薄微抿,沉黑如墨的眸子定定地注視著二樓那抹影,約意識到二樓的孩想要做什麼。
跟著,他看見孩手腳利落的爬上臺,右腳朝下方的空調機過去,然後輕輕一躍,輕盈纖瘦的穩穩地落上去,行輕巧敏捷,全程面不改,沒有毫恐慌。
空調機到地面有一定高度,祝星燃貝齒輕咬著下,暗暗做了個深呼吸,並未理會下方那道直直注視的視線,做完短暫的心理建設后,縱起跳,隨著「咚」的一聲響,半摔在綠油油的草坪上。
好在草坪有緩衝,祝星燃並沒有摔傷。
霍庭恩佇立在原地,著那抹小的白影落地,夏末溫的晚風輕揚起孩純白的角,額前的碎發垂落在臉側,如水的月映著那張緻昳麗的面龐,鍍了層淡淡的清輝,宛若夏夜靈,不似真人。
祝星燃看了霍庭恩一眼,隨即微垂著腦袋,斂著眉眼間的落寞,沉默地與他肩而過,霍庭恩終是沒忍住,側目向,薄輕啟:「準備去哪?」
孩形微頓,好半晌才慢吞吞回頭,纖長綿的眼睫上還掛著幾顆晶瑩剔的淚珠,一雙眼睛紅得像兔子,顯然剛剛哭過,此時卻分外明亮,像藏著細碎的星辰。
撞上男人詢問探究的目,祝星燃面窘迫,低了低頭,一開口,嗓子還有點啞:「哪都可以。」
只要不是這就行。
霍庭恩清清淡淡的目劃過孩就沉寂灰敗的眉眼,心臟像是被一細線纏繞住,他幾乎沒有過多的思考,淡聲開腔:「那就跟我走。」
霍庭恩說出這句話的時候,甚至沒有想好帶面前的小姑娘去哪,他並不是個做事衝的人,卻在這一刻,大腦直接跳過了思考的階段。
祝家大宅,晚宴還在繼續,沒人注意到這裡了兩個人。
那一晚,霍庭恩開車行駛在水般的車流中,窗外是璀璨霓虹,明亮的路燈在夜幕下連一道道耀眼的線,匯聚一條燈河,充斥著城市的繁華與喧囂。
車卻十分安靜,兩人上車后一句話也沒說,霍庭恩握著方向盤,眉眼清雋疏淡,對於這場變故,並沒有多大的緒起伏,他側目看向副駕的祝星燃。
孩微歪著腦袋,怔怔地著車窗外匆匆掠過的街景出神,昏黃斑駁的影細碎的鋪在秀逸的面龐,描摹出緻立的廓,與初見時相比,眉眼間褪去一分稚氣,多了抹明艷。
借著昏黃的燈,霍庭恩這才注意到,祝星燃稍有些腫的臉頰上那道清晰的掌印,此時還在泛紅,從他的角度看過去,剛巧能看到孩眼尾溢出的淚,纖瘦單薄的肩膀輕,哭得無聲無息。
直到車子停在在十字路口,駕駛座上的祝星燃才慢吞吞回頭,淚眼朦朧的向他,可憐的問他,有沒有紙巾。
霍庭恩向來不擅長安人,更別說安一個小姑娘,他張了張,只覺得說什麼都不太合適,只是沉默地將手邊的紙盒遞過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強勢纏愛:總裁,你好棒(林語嫣 冷爵梟)
結婚一年,老公寧可找小三也不願碰她。理由竟是報復她,誰讓她拒絕婚前性行為!盛怒之下,她花五百萬找了男公關,一夜纏綿,卻怎麼也甩不掉了!他日再見,男公關搖身一變成了她的頂頭上司…一邊是拿床照做要挾的總裁上司,一邊是滿心求復合的難纏前夫,還有每次碰到她一身狼狽的高富帥,究竟誰纔是她的此生良人……
264萬字8 56104 -
完結1446 章

借住後,小黏人精被傅二爺寵翻了
傅二爺朋友家的“小孩兒”要來家借住壹段時間,冷漠無情的傅二爺煩躁的吩咐傭人去處理。 壹天後,所謂的“小孩兒”看著客房中的寶寶公主床、安撫奶嘴、小豬佩奇貼畫和玩偶等陷入沈思。 傅二爺盯著面前這壹米六五、要啥有啥的“小孩兒”,也陷入了沈思。 幾年後,傅家幾個小豆丁壹起跟小朋友吹牛:我爸爸可愛我了呢,我爸爸還是個老光棍的時候,就給我准備好了寶寶床、安撫奶嘴、紙尿褲和奶酪棒呢! 小朋友們:妳們確定嗎?我們聽說的版本明明是妳爸拿妳媽當娃娃養哎。 小豆丁:裝x失敗……
261.7萬字8.18 126691 -
完結596 章

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親哭我
她愛上霍時深的時候,霍時深說我們離婚吧。后來,顧南嬌死心了。霍時深卻說:“可不可以不離婚?”顧南嬌發現懷孕那天,他的白月光回來了。霍時深將離婚協議書擺在她面前說:“嬌嬌,我不能拋棄她。”再后來,顧南嬌死于湍急的河水中,連尸骨都撈不到。霍時深在婚禮上拋下白月光,在前妻的宅子里守了她七天七夜。傳聞霍時深瘋了。直到某一天,溫婉美麗的前妻拍了拍他的背,“嗨!霍總,好久不見。”
105.6萬字7.77 95117 -
完結1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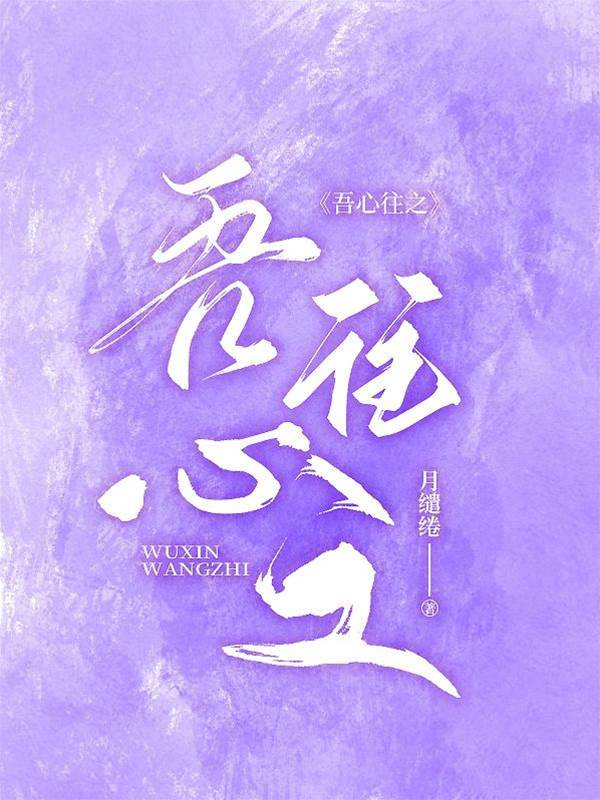
吾心往之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嘴硬心軟,有甜有虐he 】【獨立敏感的高冷美人??死心塌地口是心非的男人】【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京圈權貴、商界霸總】——————阮想再次見到周景維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燕城的初雪。她抱著朋友的孩子與他在電梯間不期而遇。周景維見她懷裏的混血女孩兒和旁邊的外國男人,一言不發。走出電梯關閉的那一刻,她聽見他對旁邊的人說,眼不見為淨。——————春節,倫敦。阮想抱著兒子阮叢安看中華姓氏展。兒子指著她身後懸掛的字問:媽媽,那是什麼字?阮想沉默後回答:周,周而複始的周。
22.3萬字8 33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