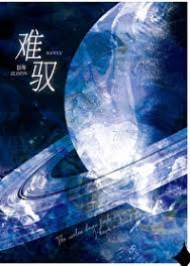《十二年,故人戲》 52.第五十一章 浮生四重恩(2)
;
從匯中飯店往北,到了徐園,不過十分鐘的車程。
他們到時,日落西斜,車馬紛紛而至。當今梨園之盛,甲於天下,南北兩地皆是如此。
「三爺請跟我來。」有人帶傅侗文往裡去,是去黃老闆定的包房。
有拿了票的客人同他們肩而過,三兩相伴地笑著、聊著,向前走,和在京城不同,能看到客,甚至還有孩。
沈奚過去唯一出去聽戲,就是和傅侗文去廣和樓。
今日踏這裡,始才覺出南北戲園的差異。 閱讀更多容,盡在st🎇o.co🍑m
那裡一路下去,是黑漆大門敞開,燈影昏暗,是夾道狹長,到繞過木影壁就能單面的戲臺子。一眼去全是男人,嬉笑怒罵自然放得開,葷話不休,到有葷腔的戲時,臺上臺下老爺們吆喝好的景象,像還在清末的上世紀裡。
這裡一路下去,是亭臺軒閣,沿迴廊去,到引路人帶進去,進了個茶園似的場子,戲臺是三面觀敞口式的,樓上樓下兩層。過去,見到不賓客,蘭麝香濃,綺羅雲集,大小姨娘雜坐於偎紅倚翠的風塵子之間,也都是砸錢捧角的人。;
跟傅侗文上樓時,有兩個握著紙扇的人並肩而下,在低聲說著今日來了幾位名角。因為樓梯狹窄,傅侗文和沈奚是前後上樓的,他兩手斜在西口袋裡,在兩個人下樓時,微駐足,偏過,讓兩個士先下了樓梯。
於是,兩個人接下的話題就是……這又是哪裡來的公子,很是面善。
傅侗文眼藏笑,斜倚著樓梯扶手,對出右手。在旁人艷羨的目里,被傅侗文拉著上了兩級臺階,到了二樓。
Advertisement
轉眼到包房外,兩個守在那的男人,一左一右為他們推開門。傅侗文將自己的西裝外遞給跟隨而來的兩人,讓他們在門外候著,帶沈奚。
裡頭,五個男人正坐著閒談,見了傅侗文都紛紛立,招呼著。為首的那位穿灰長袍的是黃老闆,餘下兩個中年男人和一個老者都還算客氣,角落裡的男人是唯一西裝加的,正眼也不看傅侗文一看。
賓客們是滿清末年的款式妝容,有手裡拿著遠鏡,也有著紅戲單子的,見男人都起了,也即刻離席,對傅侗文欠,行得是舊禮。;
「今日裡,特地囑們換了這裳,」黃老闆和悅地指們,「能三爺的眼嗎?」
上海書寓里的風塵和蘇磬那種北地胭脂不同,偏洋派,打扮賽金花的模樣,也像是臨時上的戲妝,不過是為了討好傅侗文。
「南方佳麗同北地胭脂,是各有千秋,各有妙。」
一語未完,他又笑說:「方才從匯中飯店過來,沒來及送沈小姐回家,就一起過來了。」
沈奚跟著說:「你好,黃老闆。」
「是普仁醫院的沈醫生。」老者眉眼堆笑,輕聲提醒黃老闆。
在上海的富貴圈子裡小有名氣,黃老闆經這一說,也仿佛記起來這號人,對笑笑。
「聽說沈醫生是在國留過洋的,都說這歐是鍍金,日本是鍍銀,」煙榻旁的男人笑著恭維說,「我們也算見識見過鍍金的先生了。」
眾人笑。;
今日包房裡的客人都是配好的搭子,不管男,都有對應布置過的。煙榻上兩位先生是生意人,想要黃老闆搭線和傅侗文打個照面、混個臉。餘下的老者和西裝男人是黃老闆的心腹,軍師和先鋒的地位,算是左右手。
Advertisement
就連人也都費心安排好了,誰伺候誰,猛多了沈奚一個醫生,倒顯得多餘了。只是是傅侗文帶來的伴,不好怠慢。老者囑人添座給沈奚,大夥各自歸了位。
「稍後這齣,三爺必定喜歡。」黃老闆落座。
「哦?」傅侗文問,「是什麼?」
黃老闆指樓下,開鑼了。
傅侗文一抬眼,向戲臺。銅鑼敲了幾聲,胡琴起。
他聽出端倪,角噙笑,用手指輕打著拍子。
「三爺開個嗓?」老者邀約。
傅侗文也像來了興致,經老者這一請,便和臺上那位角一同唱將起來:「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論如反掌保定乾坤~」;
正是那空城計最彩的一段,諸葛亮閒坐城頭,笑對千軍。他唱得是字正腔圓,戲腔純正,毫不輸那臺上擺開架勢的名角。
老者微微一笑,跟著唱下去:「先帝爺下南駕三請~」一段胡琴後,再來一句,「算就了漢家業鼎足三分~」
黃老闆細細品咂著,痛快擊掌:「好!」
樓下,看客們此起彼落的好聲也灌進來,震得沈奚耳嗡嗡。
那夜隔著兩扇門,聽傅侗文唱得是愁腸百結的四郎探母,今夜卻是談笑自若的空城計。沈奚只覺這一折戲才配得上他。
在座的男人們都被挑了興致,全唱了兩三句,卻把最彩的唱段留給了傅侗文。人們最會分場合、看份的,從唱詞就聽出來:這位三爺就是今日的上賓了。
茶過三巡,沈奚後坐著的兩位姑娘輕聲笑談。
們用遠鏡看樓下散座,不是再聊戲,而是在聊著樓下捧角的姨太太們,說哪家姨太太和戲子走得近,還有哪家的姨太太和戲子搞在一。;
Advertisement
煙鋪上的男人兩兩相對,談起了生意。
借著戲園子的好氣氛,隔著鏤空的銅製煙燈,一人邊伺候著一位眼神流盼的年輕姑娘,替他們裝了兩筒煙。
在煙霧繚繞里,沈奚翻著茶幾上的一摞報刊,剛看完《梨園雜誌》,又撿了本《俳優雜誌》。突然,房裡暗下來。是煙榻上的兩位老闆嫌電燈晃眼,囑人撳滅了電燈。
大燈滅了,此時除去煙榻上燃燒著的小煙燈,僅剩了主座兩旁的西洋式落地燈。落地燈外垂著艷紅的燈罩子,紅影暗沉,讓人昏昏睡。
沒了源,看不報刊,百無聊賴地聽著戲,落地鍾走到了十點。
已經等了四個小時,傅侗文仍是氣定神閒。
沈奚在黑暗中,瞧見一個黑青年人推門而,躬到黃老闆耳畔,耳語片刻。
黃老闆揮退他,對傅侗文說:「三爺請安心。」;
傅侗文回說:「黃老闆費心。」
兩人相視而笑。
黃老闆道:「沒想到三爺是個重義的人。」
「義是負累,我擔不起這些,」傅侗文道,「只能說被人上了梁山。」
「哦?何為上梁山?」
傅侗文道:「是被他用六妹要挾著要錢,心裡不痛快。這樣被人拿,不合我的脾氣。」
黃老闆恍然,笑罵道:「一個土司令還敢要挾三爺?那些赤佬在自己地盤上耀武揚威慣了,殊不知,今日的人上人,就是明日的墳中骨,活不長了。」
兩人談話聲時高時低,沈奚只聽到隻言片語,沒多會就因為新戲開鑼,各自安靜了。
沒多會,窗子外邊,稀稀沙沙一陣雨。
下人沏了一壺茶新茶,為他們斟上,茶煙裊裊,鑼鼓又起。
Advertisement
;
白順著門,緩緩擴了扇形。
青年人再。
沈奚以為是有新消息了,豈料他只是把手裡的戲單遞給黃老闆:「樓下問,老闆還要點什麼戲,大家都在候著呢。」
「三爺還有什麼想要聽的?」黃老闆略略掃過戲目,「這有一出時裝的劇,《宋教仁遇刺》,三爺以為如何?」
「賣的是噱頭,這戲沒意思。」傅侗文品呷著新茶,興趣乏乏。
「我以為三爺是個追時髦的人,會對革命的劇目興趣。」煙榻北面的男人笑著搭話。
煙榻南面的男人一氣吸完手裡的煙槍,卻道:「你以為還是清朝末年?想要出人頭地,先去幹革命、造炸彈?老黃曆了。」
傅侗文笑,眾人便跟著笑。
「再來空城計吧。」
「是。」青年人倒退而出。;
西洋式的落地鍾里,指針走到了十一點半。
沈奚剛才在戲單上看到徐園的閉園時間是午夜十二時,還有半小時這裡就要撤席了。倘若十二點還沒消息,難道還要換個銷金窟,接著等嗎?心裡有不安,黃老闆把事辦妥後,讓人送一個信去公寓就好了,為何要請傅侗文親自來等消息?
總覺,還會有旁的枝節。
臺上,戲開了鑼。
沈奚剛端了茶盞,那扇門第三次被推開。還是同一個人。他到黃老闆旁,耳語數句。黃老闆突然擊掌:「好!看賞!」
門外,青幫的人當即吆喝:「黃老闆賞嘍~」
樓下的散客這才知道樓上包房裡的是青幫黃老闆。池子裡的男都像是領了賞錢的人,喝彩聲一浪高過一浪,歡笑著鬧將起來。
沈奚被那音浪推送著,茶也喝得不安寧。
到底想明白了,自己為什麼會坐立不安,是因為這裡是青幫的底盤,和京城的廣和樓不同。傅侗文在廣和樓的威風是真威風,在這裡雖是座上賓,也只是客人。;
愈發不安,裡溜進一片茶葉,輕吐到茶碟里。
突然聽見後一陣人的笑聲,笑得心突突跳。
燈影錯里,聽見黃老闆對傅侗文說:「三爺,是一個好消息。令妹返家途中遇到劫匪,是車毀人亡,骨無存。」
心驚了一瞬,再瞧見傅侗文的笑,立刻品出了旁的意思。應該是他們借著骨無存的理由,讓六小姐金蟬了殼。
「既是如此,我這裡就陪了,」傅侗文擱下茶盞,說,「先去理家事。」
他無意多留,接過下人遞來的西裝上,到門口,無人開門。
這門是青幫的人守著的,外頭掛鎖,沒吩咐不會開。
傅侗文駐足,並不惱怒,反而是笑著掉頭,看黃老闆:「這是?」
黃老闆不答。
老者倒背著手,在黃老闆旁道:「三爺走得急了,要等我們把話說完。」;
傅侗文著他們,等下文。
黃老闆這才道:「今日的事,我替三爺辦妥了,我這裡也有一樁小事,想和你打個商量。」
煙榻上的兩位生意人權當沒聽到,呼哧呼哧著大煙,不理會他們。
傅侗文向對方一笑,道:「眼下我算是籠中的鳥,直說就是。」
「三爺言重了,」老者說,「還是法租界醫院外的那一樁舊案,三月里的事。」
果然舊事重提了。
從初春到夏末,傅侗文和這位黃老闆有過幾次公開的應酬,禮尚往來也頻繁,沈奚還以為傅大爺在醫院外鬧出來的事已經過去了。可現在看,他們不是忘了,而是在等著一個機會清算恩怨。
傅侗文不言不語,端看著他們。
虎落平被犬欺,他並不意外。難怪今日裡包房客這麼多,又有生意場上的人,也有長三堂子有名的姑娘,原來是要幾個見證,找回場子。;
老者像怕他誤會,解釋說:「傅家的事呢,終歸是家事,黃老闆本不想手的,只是當初傅三爺沒打招呼,就去找了另外兩位老闆手。雖然看上去是解決了,可這不合規矩,也損了我們的面。」
老者又道:「不過我們也很清楚,廠的這個生意,三爺要是請另外兩位老闆幫忙,也一定能辦的妥當。可三爺卻找了我們。照我的猜想,三爺是要補償三月的事,是不是?」
在這世,用一間廠換一個人,對任何一個混江湖的人來說都是天方夜譚,是穩賺不賠的生意,誰接了這個活都要燒高香、拜謝財神的。
猜你喜歡
-
完結632 章

絕配良緣,獨寵小醫妃
傳說北野王北冥昱的眼睛盲了,其實,他的眼睛比鷹眼還要亮。 傳說呂白鴦是個啞美人,其實,她的聲音比誰都好聽,連天上的鳳凰鳥聽到她的歌聲都會飛下來在她的頭頂上繞幾圈才肯飛走。 一出調包計,大婚之日,兩頂花橋一齊出府,一齊浩浩蕩蕩地走過京城的大街。 呂國公府上的三千金呂白鴦原本該嫁的人是當今聖上最寵愛的東滄王殿下北冥淵,卻在新婚夜后的隔天醒來時,發現自己的夫君變成盲了眼睛的北野王殿下北冥昱。 陰差陽錯,啞千金配盲夫北野王,絕配!且看他們夫妻怎麼驚艷逆襲,扭轉乾坤,聯袂稱霸江湖,袖手天下,情定三生。
60.3萬字8 199322 -
完結592 章
警草小甜棗
十年前校園初見,他霸道宣布:這個小甜棗兒是我的! 十年後警隊重逢,他眉頭一挑:這不是我那劈腿前女友嗎? 相看兩厭卻並肩作戰,十年懸案步步揭開,邢警隊長為公道挺身,美女法醫為亡者代言。 奪命追兇時他告誡她:你回來也沒用! 老子好馬絕不吃回頭棗。 酩酊大醉時他咬牙切齒:你跟老子服個軟! 老子就大人大量原諒你! 生死關頭他發來短信:小甜棗熟了,想吃。 路霄崢抽煙喝酒脾氣壞骨頭硬一身臭毛病,卻讓唐早愛了十年...... 真相大白時,她拍拍某人狗頭:回家吃棗? PS:MAN爆的警隊帥草VS甜爆的美女法醫
111.9萬字8 7121 -
完結210 章

嫁給渣男他哥,我被寵上天了
【重生,寵文,雙強,1v1】 路家和宋家是鄰居,路言兮和宋家二少宋淮青梅竹馬,她是宋淮的白月光。 宋淮怕追求失敗不敢對她表明心意,長久壓抑的感情無處發泄,找了個和她有點像的女生做替身。 路言兮傷心出國。 五年后回國,宋淮再三向她保證不再和替身有牽扯,路言兮耐不住他整整一年風雨無阻的苦苦追求,最終答應了。 宋淮向她求婚時替身找來。 替身生病了。 路言兮死了,因宋淮以救命之恩相逼讓她給替身捐骨髓引發并發癥。 生命盡頭躺在病床上那三年,是宋家大少宋綏默默陪伴她,似醫生對病患,似兄長對妹妹,似朋友對朋友…… 路言...
40.5萬字8 29826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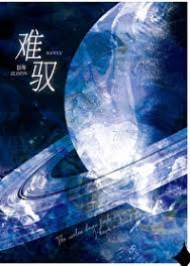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213 章

位高權重的夫君傲嬌霸道,得哄著
【古言 無重生無穿越 先婚後愛 寵妻甜文 虐渣 生娃 女主成長型】薑元意容色無雙,嬌軟動人,可惜是身份低微的庶女。父親不喜,嫡母嫌棄,嫡姐嫡兄欺負,並且不顧她有婚約,逼迫她給奄奄一息的景國公世子爺衝喜。拜堂未結束,謝容玄暈倒在地。當時就有人嘲笑她身份低、沒見識、不配進景國公府。她低頭聽著,不敢反抗。謝容玄醒來後,怒道:“誰說你的?走!罵回去!”他拖著病體教她罵人、給她出氣、為她撐腰、帶她虐渣……她用粗淺的醫術給他治療,隻想讓他餘下的三個月過得舒服一些。沒想到三個月過去了。又三個月過去了。……謝容玄越來越好,看見她對著另一個男人巧笑嫣然,他走上前,一把將她摟入懷裏,無視那個男人道:“夫人,你不是想要孩子嗎?走吧。”第二天薑元意腰疼腿軟睡不醒,第三天,第四天……她終於確定他病好了,還好得很,根本不是傳言中的不近女色!
39.4萬字8 20510 -
完結211 章

卑鄙的我
林質從來不恨那個叫聶正均的男人切斷了自己所有的退路。 從五歲被領進聶家的大門時起,她就知道,那個高高在上的男人她無論如何都......難以抵抗。 這個夏天,甜寵你! V章高甜,怕過七夕及一切情人節的單身貴族們慎點! 藍老濕保持天天更大肥章的速度,不怕被秀
31.7萬字8 16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