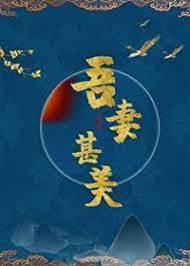《宮女在逃》 第179頁
兩人慢慢走著,相談甚歡。
「我比你大三歲,你我姐姐吧。」
殊麗大方喚道:「呦鳴姐姐。」
陳呦鳴翹起角,「我三月出生,你呢?」
在宮中蹉跎多年,殊麗都快忘記自己的出生時辰了,「十月。」
再有幾日,就是十八歲的生辰了。
將陳呦鳴送回府,殊麗剛要乘車回宮,忽然被巷口竄出來的一道影攔下。
「以漁,你怎麼在這兒啊?」
突然出現的元利康,令殊麗厭煩不已,沒等攆人,車夫和侍衛就亮出了佩刀,「貴人出行,閒雜人等退避。」
貴人,退避?
元利康覺得無比刺耳,一瘸一拐走到殊麗面前,「我和你們這位貴人可是親戚,你們要當著的面殺我不?」
不願讓人看了笑話,殊麗示意車夫等人稍稍退開,隨後看向元利康,「找我有事?」
「偶然遇見。」
元利康手裡還提著吃食,確實不像跟蹤而來,不過,若他是跟蹤而來,侍衛們真有了滅口的理由。
「下次遇見,不必特意過來打招呼,咱們不。」殊麗眉眼淡淡,疏離又不近人。
元利康暗自撇撇,面上笑得燦爛,「你來宋老太師的府邸作甚?剛剛那個年輕男子是何人?」
問話時,他眼中忽閃,就好像發現了什麼了不得的,足以拿住殊麗。
殊麗角泛起嘲弄,語氣更冷,「辛,元大人還是不要追問底的好,以免追悔莫及。」
Advertisement
「我追悔莫及的事兒還嗎?不差這一件。」他一邊笑著,一邊打量起殊麗的穿戴,綾羅綢緞、珠翠燒藍,乍一看,哪裡像個服侍人的婢子,分明是豪門養出的。
嘖,飛上枝頭,就是不一樣了。
元利康笑得諂,又湊近半步,「你也知道舅舅府宅遭了大火,燒得什麼也不剩,我們一家不得不住進署的廨宇,擁的不行。你看,一家人的,是不是該接濟一二?」
說話時,他就差眼睛放了。
像是聽了一樁笑話,殊麗忽然掩帕輕笑,「一家人?從打進宮,我就沒有親人了,別往自己臉上金了,你不配。」
說完,繞開臉難堪的中年男子,踩上腳踏,正要彎腰鑽進車廂時,後傳來一道譏誚——
「你若不認我這個舅舅,就休怪我大義滅親,剛那個小白臉是你的相好吧,若是被陛下知道,你該知後果多嚴重。」
殊麗下車簾,縹緲的聲音從窗傳出,「那你就去前告狀吧。」
我還有些期待呢。
馬車緩緩駛離深巷,元利康氣得擲了手裡的紙袋,朝馬車追了幾步,「小畜生,你給老子等著!」
他不好過,也休想好過!
車外的謾罵持續不斷,殊麗閉了閉眼,下火氣和委屈,冷著臉回到了宮裡,守夜時,也是罕見的沒有一笑意,外人見了,還以為和天子慪氣呢。
陳述白是在三更時才回的寢殿,手裡還攥著一座小城發來的報,說是有人在城中發現了陳斯年等人的蹤跡,卻無力阻攔,讓他們逃了。
Advertisement
「吩咐下去,派人前往此城一探究竟。」
側的軍統領有點不解,「可他們不是已經離開那座城了麼,要不要直接北上捉人?」
陳述白將報甩在他臉上,「即刻。」
一個千戶握有一千一百餘人,陳斯年邊充其量百餘人,若是起手來,刀劍影,即便打不贏對方,也會引起其餘城池將士的注意,怎會沒有收到其他任何城池的報?
事出反常必有妖,說不定,這就是一封偽造報,亦或是,送出報的千戶被人控制住了。
察覺天子了怒,軍統領哆嗦一下,「末將馬上去辦!」
屏退隨侍,陳述白走進寢,見殊麗坐在塌上發呆,斂了周的寒氣,走過去拍拍的背,「誰惹你不高興了?」
殊麗敷衍地福福子,被陳述白打橫抱起放在了書案上。
灼吻落下時,殊麗別過臉,沒讓他親到。
陳述白也不氣,對越來越有耐心,「跟朕說說,誰惹你不快了?今兒朕也不快,咱們正好拿欺負你的人出出氣。」
還能這樣出氣,有夠稚,殊麗勉強扯出一抹笑,「陛下真的想為我出氣?」
陳述白靜默地看著,不置可否。
殊麗主攬上他的肩,前傾,在了他微涼的下頷上,眼眸幽幽晦暗,流出幾分妖氣。
妖氣而冷,很難招架住。
「這些日子,我想多和公主走,陛下允嗎?」
Advertisement
公主......陳述白想起那個古靈怪的皇妹,「怎麼,你們很投緣?」
「是呀,陛下允不允?」殊麗淺啄他的下頷,一下下帶著。
化妖的傾城子,殺傷力是平時的十倍不止,將陳述白那點慍火也一併排解,唯留下呢噥旖旎。
大手撐住韌的腰肢,將人豎抱起來,喑啞命令道:「盤上。」
殊麗蹬去繡鞋,雙腳一勾,勾住他勁瘦腰,將嬈的子靠了過去。
窸窸窣窣一陣後,綾羅珠翠落了地,雪白的襯上還留有幾個凌的腳印,兩人的影從書案輾轉至龍床,再到湢浴,一路跌跌撞撞,龍袍、玉冠落在了湢浴外。
猜你喜歡
-
完結207 章

仵作驚華
一樁宮廷血案,永信侯府滿門獲罪,祖父與父母親被判斬刑,年幼的戚潯死裏逃生活了下來。 十五年後,京城繁華如舊,新帝登基五年,朝野海晏河清,可臘八節吉慶之夜,一宗連環詛咒殺人案如驚雷般令朝野俱震。 天資玉骨的仵作戚潯,因此案一戰成名。
95萬字8 32897 -
完結490 章

花式養成權臣大佬
前世冉秋念家破人亡,不得善終,重生歸來,她要讓那狠心郎君和毒辣繼姐,血債血償! 卻在復仇開始前,遇上曾經護她一世的陰郁權臣,看著還寄人籬下的大哥哥,她決定這輩子的大佬她來守護!如果能順便抱個大腿就更好啦。 沒想到養著養著,養成的權臣大佬,真的跟她成了一家子
134.6萬字5 12032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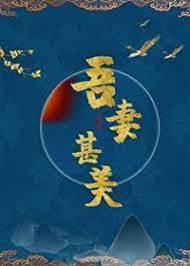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