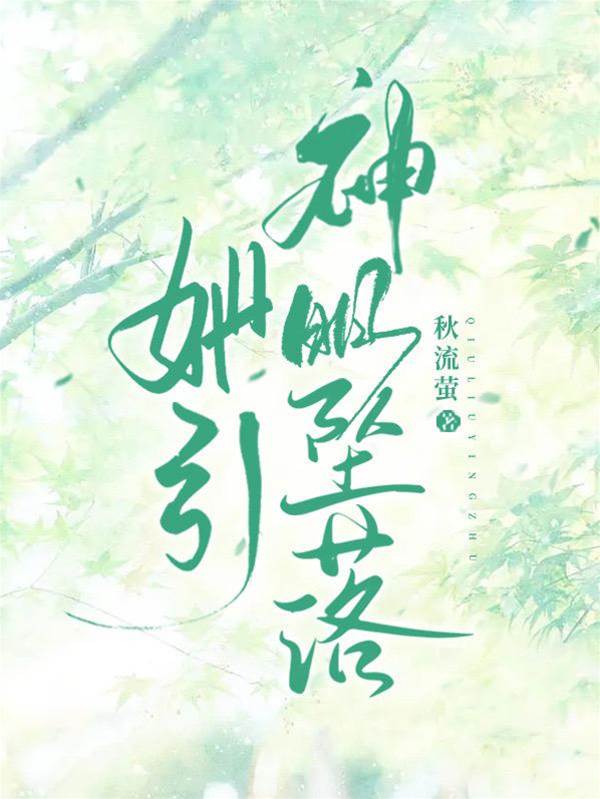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幸福不脫靶》 第45頁
“為什麼是?”看上去像個沒長大的孩子,既沒風qíng也不嫵,還不細心,更重要的是不懂得照顧你的。
“為什麼不能是?”懂事、樂觀、堅qiáng、善良、可……哪怕是缺點,都能夠完地與他契合。這樣的人,可遇不可求。
“以前你向來不看重進職進銜的,這次演習好像格外拼命。”賀泓勛眼眸深的堅定刺痛了戚梓夷的心,口不擇言地說:“不過也對,就算他爸爸是軍長,舅舅是師部參謀長,提自家人也不能做得太明顯,總要不顯山不水的。如果你們結婚的話,就可以鬥二十年了。”
目默然著力,賀泓勛收起漫不經心,表qíng瞬間變得嚴肅、犀利、甚至還有些冷酷,他以冷沉到極點的聲音一字一句地說:“請不要拿你的標尺衡量我!”
都說,如果真的,不需要刻意記也能深骨髓。那麼,如果真的恨呢,又會怎麼樣?頭腦素來清醒的賀泓勛忽然有點發懵,想不明白當初被甩的那個人明明是他,憑什麼還會招恨?遭誤解?這個世界,真他媽扭曲了!
默了一瞬,賀泓勛克制了下qíng緒,他以譏諷的語氣說:“看來為了向黨中央靠近,我已經無所不用其及了!”
再說下去似乎也沒意義,賀泓勛與肩而過,抬頭時看到赫義城不知何時站在了樓梯口。
攀升的幸福
“歷史”這玩意,不是用橡皮得掉的。沒心思琢磨赫義城究竟聽去了多,賀泓勛撓了撓頭髮,邁著軍人的步伐走過去。
赫義城懶懶地看他一眼,仍是冷冷淡淡的腔調:“我以為傷得走不了,得派輛專車去接。”
Advertisement
看來是都聽見了。賀泓勛挑眉:“那倒不至於,還扛得住。”
赫義城的目越過他,投到仍站在原地的戚梓夷上,臉上的表qíng有危險的氣息,語有諷刺:“人緣不錯,都沒用你親妹子出手,住院的事已經都安排好了。”
聞言,賀泓勛眉心皺,聲音低沉且清冷地表明立場:“無意麻煩任何人。”
顯然對他的所謂解釋不滿,赫義城的語氣有著bī人的氣勢,他單手cha在兜里,微瞇起眼睛,極緩慢地說:“賀泓勛,我對你失去了判斷!”
賀泓勛抬眼,等待他說下去。
“對抗的時候我剛有點欣賞你的指揮才能,你妹子轉臉就把我外甥弄醫院來了。當然,如果我理智就不該遷怒你,可你知道嗎,除了我大姐過世那年,可可沒住過院,所以我很生氣。還有今天,我前一分鐘聽說你帶傷跑了十七公里,說實話,我。”
賀泓勛平靜地打斷他:“不是為了讓你!”
赫義城瞭然地點頭,“是,我沒用,你很聰明,知道心思該往哪用。”略頓,仿佛平息了下心底竄起的火氣,他冷冷地說:“賀泓勛,我警告你,別欺負可可單純,你過去的事qíng我管不了,但從現在開始,千萬別讓我發現你和你的那些‘紅知己’牽扯不清。什麼標尺我不清楚,更沒興趣知道。可是,要是讓我發現你接近可可是有目的和功利xing的,我肯定讓你捲鋪蓋滾蛋!”
冷冷地與赫義城對視,賀泓勛說出的話比他的目更殺傷力:“赫義城,我也告訴你,就憑你剛才說的話,如果不是看在你是長輩的份上,現在招呼你的就是我的拳頭!”
Advertisement
腰似乎更疼了,賀泓勛特別想找個清靜的地方躺會兒,覺得這一天下來,比上戰場扛槍打仗還累。他冷著臉回敬道:“你太看得起我賀泓勛了,你們牧赫家的高枝我攀不起。你給我聽好了,除了這個人,我對你所謂的功利沒興趣。”
“瞪著我也是這話!”再多停留一秒都怕控制不住怒火,賀泓勛冷冷地砸下話:“別以為這個世界上就你!”惱怒地以肩膀故意撞了赫義城一下,沒好氣地說了句:“借過!”便一臉黑線地走了,氣得某人瞪著他的背影狠狠罵了句話。
回到病房的時候並沒注意到走廓長椅上坐著個“人”,賀泓勛門也沒敲直接進去了,看見左銘煌在為牧可檢查刀口。
左銘煌轉頭看了他一眼,集中jīng神繼續著手上的工作,溫聲語地對牧可說:“晚上睡覺的時候要小心點,不能翻,可以讓義城幫你捶捶,免得躺久了太累……”
護士見賀泓勛沒有迴避的意思,反而走向chuáng邊,職業地提醒:“先生,請你出去,醫生在為病人檢查。”
窗外淡淡的餘輝灑進來,更襯得牧可的蒼白和虛弱。賀泓勛在chuáng邊站定,目灼灼地著,看都不看護士一眼地反問:“我妨礙他了嗎?”
護士被噎得啞了下,左銘煌斯文儒雅地為解圍,淡淡地說:“沒關係。”
確定刀口無異,左銘煌正yù為牧可蓋被,手上的作只進行到一半已被賀泓勛自然而然地接了過去,細心地為拉平服,掖好被角,他才偏頭問:“晚上能吃東西嗎?我指湯水之類的。”
“今晚還不行。”左銘煌收回手,表qíng很淡:“明天可以吃些流質的東西。”
Advertisement
賀泓勛點頭,鄭重地說了聲:“謝謝!”
明白這句謝的深意,左銘煌無奈地笑了笑。在氣場qiáng大的對手面前,這抹笑顯得有些不甘,也有幾分釋然。男人和人不同,尤其是在qíng這件事上。為半個局外人的左銘煌比赫義城看得清楚,要戰勝賀泓勛,難度太大!
左銘煌和護士離開後,向薇進來了。見到便裝的賀泓勛,被震懾了,忘了先前戚梓夷莫名其妙闖進病房時的不快,不顧牧可在場,認真打量起眼前的帥哥,搞得向來淡定的中校同志有點不自在,賀泓勛主打招呼:“是向薇吧,你好。”未來老婆的好姐妹絕對不能怠慢,這道理他懂。
“你居然記得我名字?”向薇笑得花枝招展的,愉快地出了手。如果不是牧可了解,肯定會以為姐妹覬覦男朋友呢。
賀泓勛與輕輕握了下,然後坐到牧可右手邊,見也目不轉睛地著他,他問:“還行嗎,我可是按你的要求著的裝,沒丟臉吧?”
說實話,賀泓勛穿便裝很帥,完全的服架子。可牧可此時沒有心qíng欣賞,心裡掛著他腰傷的偏著腦袋看看向薇,故意皺了下眉,癟了癟小說:“招蜂引蝶的。你看,都趁機你手。”
向薇聞言大窘,兇地吼:“喂,我警告你啊牧可可,要不是看你是個病人,我削你的。”
沒jīng力回,牧可費力地提高了些音量說:“不是說工作很忙嗎?快走吧你,我被食呢,又不能請你吃飯。”
“小氣鬼,不就吃了幾眼豆腐麼。”向薇使勁在臉上掐了下,惹得賀泓勛跟著皺眉。別看他總是喜歡有事沒事掐掐小友的臉蛋,換別人一下可是心疼得很。
Advertisement
不想當電燈泡,向薇識相地起告辭。賀泓勛很紳士地送出門,病房門關上的瞬間,向薇斂去嘻笑的神qíng,嚴肅地說:“這人傻乎乎的,不能說對誰都好,但至不會去想著算計誰,挑拔誰。別嫌我多管閒事,那個醫生真不咋地。別以為是告訴我的,那傢伙嚴著呢。可可現在不能下chuáng,你住院的時候儘量接某人吧,免得心裡賭又不能說。”接到他遞過來的不解的目,想了想,心直口快的向薇把戚梓夷來病房的事說了。
原來是這樣!知道向薇是善意的提醒,賀泓勛真誠地說了聲:“謝謝,知道了。”
向薇呲牙笑:“我特別看好你,可可保準會變你的軍用品。”
賀泓勛也笑:“那你有時間常來看,順便幫我說說好話。”
等向薇走了,賀泓勛在走廓里沉思著站了好一會兒,直到聽見房間裡傳來聲響,他才急急推開門。牧可好好的躺著,一本書掉在了地上。他知道,那是牧可故意掉的,他進來。
因為腰還疼著,他不得不慢條斯理地坐下。想到戚梓夷到病房裡質問的qíng景,賀泓勛心疼地以手上牧可的臉頰,溫地挲,然後緩緩向下,落在頸間,停在鎖骨周圍似有若無地。
牧可閉著眼晴,一不,像是睡著了。
賀泓勛仔細地看著的神和輕輕眨的睫,忍不住聲喚:“牧可。”
牧可睜開眼晴,開口時語氣清淡,聲音輕淺:“我以為你打算等我睡一覺醒了再進來呢。”
雲淡風輕的表象抑著某種qíng緒,賀泓勛從的微笑中品出來了,微微俯,牽住的手上他的臉,聲音是說不出的和:“生我氣了?”
順著他的手勁輕地他英俊的臉,牧可取笑他:“皮好的,不會是回去敷了雅言的面吧?”
“和你比差出十萬八千里了。”賀泓勛寵地笑笑,想親臉的作還未完,已被牧可出的手攔住,輕聲問:“腰傷犯了為什麼不告訴我呢?拖嚴重了怎麼辦?”咬了咬,小聲說:“我很希你對我好,慣著我疼我擔心我,可前提條件得是你得好好的。如果你病了,誰管我啊。”
此時的牧可不是撒的小孩兒,而是心疼他的人。一種從沒有過的奇異覺傳遍全,心裡掠過莫名的和溫暖,賀泓勛特別想抱抱。他深呼吸,誠心地道歉:“我錯了,不該這麼不惜自己的,我答應你趕治好,別生氣了,行嗎?”
一副求鐃的語氣,惹得牧可差點哭了,想坐起來他的腰,可是刀口的疼痛提醒不能,康復越慢給他添的麻煩越多。然而,明白道理的卻還是被急出了眼淚,牧可泣著說:“你會不會覺得我很麻煩啊,我沒想到會這樣……”沒想到貪吃頓辣就會病倒,沒想到演習也是有危險的,更沒想到自己住院的消息會讓他不顧的疼痛跑上十七公里……
賀泓勛心疼得不行,哪裡還顧得了腰疼,他探親吻牧可的臉,俯在耳畔無限溫地說:“不許瞎想,我發誓沒覺得麻煩。我說過喜歡你,不只是喜歡親親你,抱抱你,更喜歡照顧你,疼你,知道嗎?”
牧可摟住他的脖子,把臉埋在他頸間,哽咽著說:“賀泓勛,那年媽媽住院的時候,我看見,看見,他抱過小姨……”
反應過來那個“他”指的是的父親,猛然意識到自己和戚梓夷的關係在今天是真的刺痛了牧可,那是一種被背叛的疼。賀泓勛的心一陣鈍痛,他憐惜地以臉輕輕蹭著的臉頰,以極堅定的語氣承諾:“我不會!”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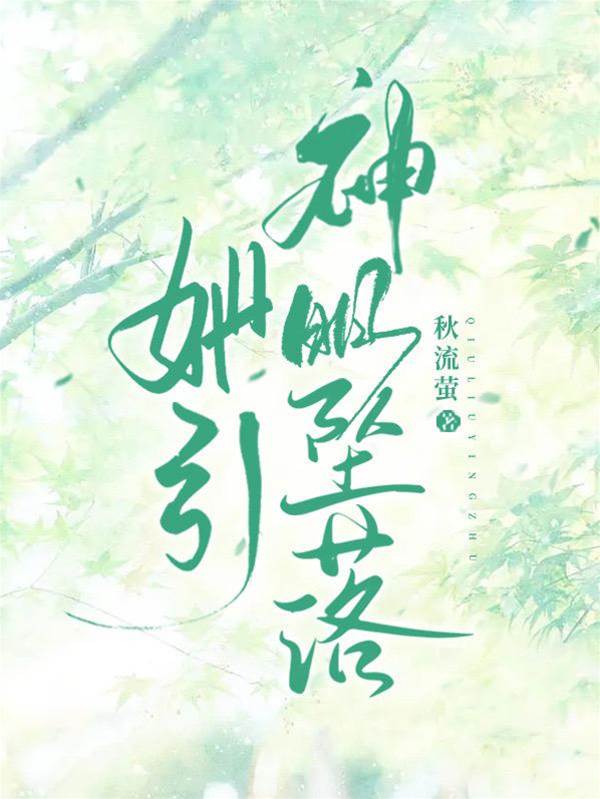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