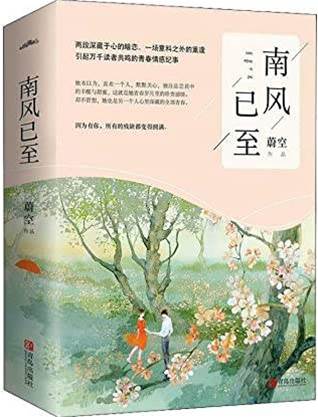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你的胡子我的圍巾》 第188頁
一邊說一邊跑,氣吁吁地。
“你先站住。”方永年說話變得很慢很慢,“我還沒到。”
“從哪家醫院跑出來的?”他問得更慢。
問得奇奇怪怪的,下意識站住的陸一心卻馬上聽懂了。
“在你們公司門口撞的……”撓著頭,“所以就去了就近的那家醫院。”
“現在下班高峰車子打不到,我都跑到一半了。”勻了口氣,“你到了等我一下,我應該還有二十分鐘!”
“你他媽給我站著別!”方永年終于了,“位置共給我!”
“我這邊單行線,現在在堵車。”陸一心被吼得了脖子。
“位置給我。”方永年著脾氣又說了一次,一字一字的。
難怪他覺得今天不對勁。
難怪剛才打電話的時候,支支吾吾的。
“別掛電話。”他在共位置的時候,又叮囑了一句。
“哦。”開著功放共位置的陸一心忍不住嘀咕了一句,“我真的沒事啊。”
能跑能跳的。
就是服臟了……
本來還想趕重回宿舍換件服最好讓李小安幫忙化個妝。
早知道就不去那家粵菜館了,上次丟了手機發燒,這次被托車撞了被燙了……
大概就是八字不合……
下次再也不去那家店了……
要見公婆啊,這可怎麼辦……
***
方永年到的非常快。
他們本來都是從公司去學校,方永年開車,掉頭開了五分鐘就看到了陸一心。
Advertisement
百無聊賴的蹲在馬路邊,上那件鵝黃的羽絨服臟兮兮的,牛仔不知道是本來就破還是摔破的,大冬天的出了一大截膝蓋。
“上車!”方永年車子停在邊,搖下了車窗。
蹲著的陸一心抬頭,眼睛腫腫的,臉上也有些污漬,臟兮兮的像路邊的小要飯的。
第二次了。
方永年太突突的。
“我……上很臟。”上還有粥黏糊糊的殘渣,所以剛才在醫院門口都不敢打車。
方永年一聲不吭,下顎咬得死。
很會看人臉的陸一心秒慫,乖乖的打開車門,乖乖的上車。
開車門的時候左手到剛才燙傷的地方,想又不敢,皺著眉頭委委屈屈的在副駕駛座。
“一會你爸媽要過來……”像是在解釋自己剛才的猶豫,“看到車子臟了多不好。”
方永年好久沒回老家了,他父母一過來就看到車子臟兮兮的,算什麼事。
“安全帶。”方永年看都沒看。
陸一心委委屈屈的又給自己系上了安全帶。
明明摔跤被燙的那個人是,現在卻莫名其妙的心虛。
“其實……”一心虛就開始話多,“你就讓我回宿舍洗個澡換件服就沒事了。”
很輕的燙傷,比起疼痛,更難的是本來想見他一面結果卻被現實打擊到急診室的挫敗。
“這樣多丟人……”訕訕的。
Advertisement
本來快三個禮拜沒見,他們應該小別勝新婚的,就和上次一樣,只是對視就覺得幸福。
但是現在方永年看都不看一眼,從側面看,他五冷峻的跟雕塑一樣。
陸一心惴惴不安的還想再說點什麼,卻被方永年打電話的作嚇得著脖子一聲不吭。
方永年在給他哥哥打電話。
電話一接通,方永年就連稱呼都沒,直接報出了他爸媽到華亭的航班號。
“你或者嫂子個時間去接一下,今天晚上安頓好,我明天再找他們。”他說的特別慢,慢的陸一心脖子越越短。
電話開的免提,陸一心能很清楚的聽到方永年哥哥在電話那頭的意外。
“我知道他們是來找我的。”方永年皺著眉,“一心出了車禍,我帶去醫院檢查。”
出了車禍的陸一心張著:“……”
“行。”方永年哥哥很了解方永年的語速,語速慢這樣,基本就是說啥都沒得商量了。
方永年又一聲不吭的掛了電話。
陸一心很不安的在位子上挪了挪:“我……都檢查過了,連CT都拍了。”
“那個托車闖紅燈,很怕出事,一進去就帶我做了全檢查。”終于也皺起了眉頭,“我不要去了,我討厭去醫院。”
方永年打了個方向,把車子繞到附近建筑的停車場。
“報告單。”他車子剛剛停穩就出了手。
Advertisement
陸一心:“……”
方永年看著,冷著臉,皺著眉。
陸一心慢吞吞的解開了安全帶,側到方永年這一邊,打開了車鎖。
因為靠近方永年,頓了頓,咬著牙,還是按下了那個按鍵。
然后打開車門,一聲不吭的,頭也不回的背著的包包就下了車。
臟兮兮黏糊糊的稀飯還黏在頭發上,下車的時候,甩了方永年一臉。
媽的!
邊走邊氣!
那麼想他!
沒有擁抱!連個眼神都不給!
不去見他父母了,連問都不問一句!
他以為他還是叔叔麼!
作者有話要說: 看吧,昨天我如果卡在這里你們肯定會給我寄刀片,馬上二更!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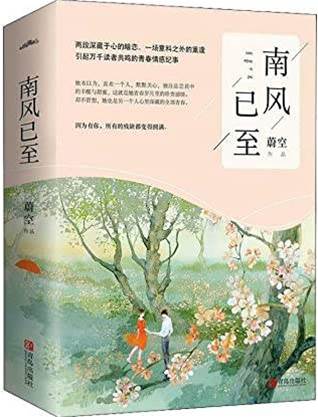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1080 章
婚亂流年
結婚紀念日,妻子晚歸,李澤發現了妻子身上的異常,種種證據表明,妻子可能已經……
191.5萬字8 10953 -
完結336 章
錯嫁后她成了第一財閥夫人
被渣爹后媽威脅,沈安安替姐姐嫁給了殘廢大佬——傅晉深。全城都等著看她鬧笑話,她卻一手爛牌打出王炸!不僅治好傅晉深,還替傅家拿下百億合作,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財閥夫人
64.8萬字8 53558 -
連載405 章

流產當天,我離婚了
“恭喜你,懷孕了!”她懷孕的當天,丈夫卻陪著另一個女人產檢。 暗戀十年,婚后兩年,宋辭以為滿腔深情,終會換來祁宴禮愛她。 然而當她躺在血泊里,聽著電話中傳來的丈夫和白月光的溫情交耳,才發現一切都只是自我感動。 這一次,她失望徹底,決心離婚。 可在她轉身后,男人卻將她抵在門板上,“祁太太,我沒簽字,你休想離開我!” 宋辭輕笑,“婚后分居兩年視同放棄夫妻關系,祁先生,我單身,請自重,遲來的深情比草賤。” 男人跪在她面前,紅了眼,“是我賤,宋辭,再嫁我一次。”
49.2萬字8.18 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