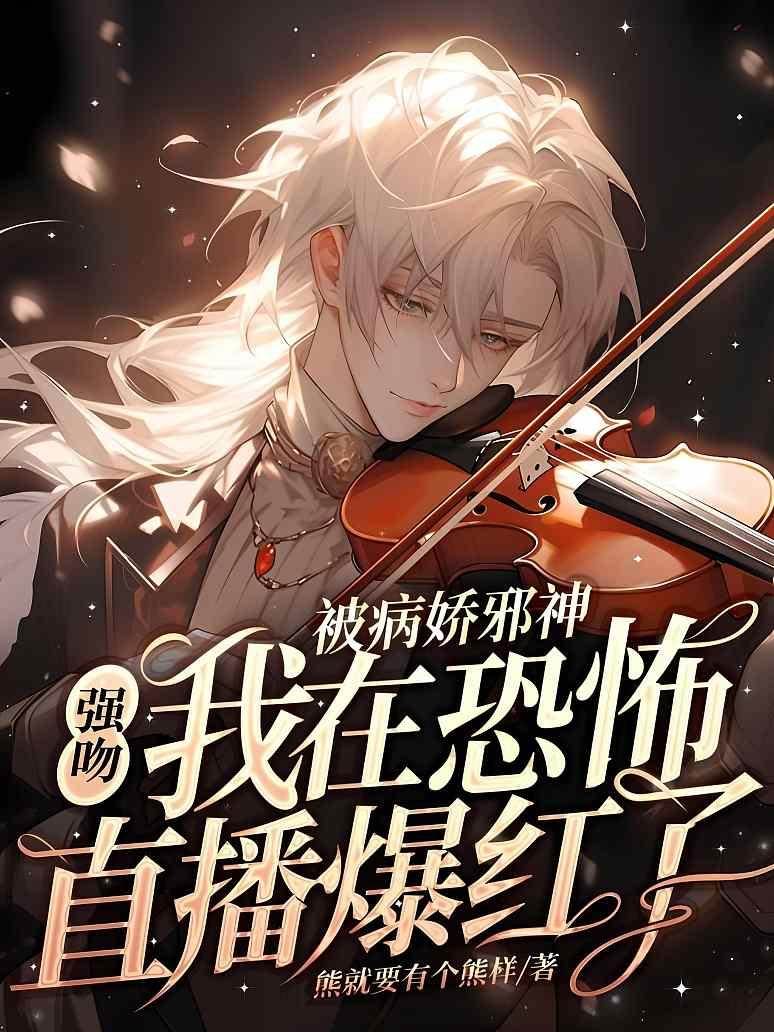《嬌吻!小美人一哭,徐總寵溺輕哄》 第1卷 第139章 小小的一片云呀
蕭惠笑著點頭,“好,湯會喝完,板栗也會吃完,也會永遠記住花香。”
逢秋抿了抿,明明決定不哭,但這一刻,還是忍不住淚眼眶,“爸爸,你去到那個世界后,要好好照顧自己,要經常給我托夢,讓我在夢里見見你。”
“好,秋秋不哭,爸爸會好好照顧自己。”蕭惠看到的眼淚就心痛,“秋秋,以后你要好好生活,要開心,要快樂,我會保佑你歲歲平安。”
逢秋胡點點頭,眼淚簌簌而落,哭著對蕭惠說,“你在我心里永遠是一位好父親,爸爸,以后我會告訴響響,有一位很的外公。”
“好。”蕭惠彎笑了笑,“秋秋,我的孩子,再見了,我永遠你。”
如果有下輩子,我一定要找到你。
離開看守所,逢秋靠在徐清懷里泣不聲,所有的抑的緒再這一次全部傾瀉而出,哭得全抖,聲音破碎至極,“徐清,我沒有爸爸了。”
原來,失去摯的人是那麼痛苦,一顆心仿佛被挖掉一半,留下的是痛苦、是孤獨、是空虛、是一個永生不會愈合的傷口。
逢秋好像回到了悉尼第一次遇見蕭惠的時候,他站在那幅巨大的《心臟》前,雙手都是。
……
行刑前,警局派人給蕭惠做心理疏導。
“蕭惠先生,五個小時后,我們將在郊區打靶場對您實行槍決,之后,我們會把您的骨灰給您的家人。”
“嗯。”蕭惠語氣淡然,他看起來本不像是一個赴死的人,他對死亡的態度平靜冷漠,死的恐懼在他上無落腳。
“您還有什麼言嗎?”
“沒有。”
……
京市大雪綿綿,蕭惠穿逢秋為他準備的淺咖西裝站在郊區打靶場里。
大雪落滿他的雙肩,他戴著手銬,扣眼里別了一朵小小的郁金香。
Advertisement
漫天大雪紛紛落下,槍聲響起的那一刻,他抬頭看向天空,緩緩閉上眼睛。
子彈穿過皮進心臟,臨死前的一秒鐘,意識格外清晰。
他好像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里看到一個穿著淡公主的小孩,抱著一只小兔子玩偶,一邊走一邊哭,邊用白白的小手眼淚邊喊媽媽。
小孩好像看到了他,于是止住哭泣,白白的小手了紅紅的眼睛,抱著的小兔子跑到蕭惠面前。
孩子仰起頭看他,兩人對視沉默,最后,孩子主出小手握住他的大手,他的手太大,握不住,于是就抓住他的一手指。
“我終于找到你了,大兔子。”
可的小音飄在蕭惠耳邊,他想到什麼后,挑眉輕笑,彎腰抱起他的小孩,他抱著,走向那未知的另一個世界。
小郁金香被握在孩子小手里,漂亮的眼睛彎月牙,趴在蕭惠肩膀上,聲氣地唱兒歌給他聽,“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過來……”
……
蕭惠的骨灰差點沒回到逢秋的手中,蕭家派了人來截蕭惠的骨灰。
蕭惠離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逢秋都走不出來。
不回香港,也不回南城,住在京市蕭惠生前住過的房子里。
好像被困在了蕭惠死的那一刻,一春又一夏,一秋又一冬,沒有好好聽蕭惠的話,沒有好好生活,邊的人都在往前走,只有,仍舊留在失去蕭惠的那個冬天。
整整一年沒有回南方,徐清沒有強迫,他給時間、給關心、給,他靜靜等待著。
這一年里,徐清經常兩個城市來回跑,鶴東的私人飛機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京市國際機場和香港國際機場,有時候是徐清一個人,有時候他會帶著響響。
Advertisement
響響已經一歲多了,在秋天學會走路,可的小棉花糖經常晃晃悠悠地撲進徐清懷里,學會說話后,就摟著徐清的脖子聲氣地喊爸爸。
京市下午六點,徐清抱著響響走出機場大廳,司機早就在等著了,一看到響響,就忍不住夸,“哎呦幾天不見小小姐看起來又可了。”
徐清笑了笑,單手抱著小棉花糖,了小腦袋瓜上的茸茸的小醒獅帽,小棉花糖還戴了一條厚厚的白小圍巾,一張嘟嘟的小臉在帽子和圍巾之間,白白的,瞳孔干凈烏黑,眨眼睛的時候能把人萌死,現在比小時候還要可。
小棉花糖聲氣地說了幾個粵語,正是出牙期,小有些風,再加上司機是京市人,本聽不懂響響在說什麼。
徐清勾輕笑,“說你也可。”
聽到這話,司機一個大男人,詭異地臉紅了。
一個小時后,司機把父倆送到棲園。
徐清剛打開外面的小木門,響響就迫不及待地從徐清懷里下來,踩著自己小小的雪地靴,晃晃悠悠地邁著小短跑進別墅里。
“媽媽,響響來啦。”
小棉花糖不僅會說粵語,也會說普通話,可聰明了,每次來見媽媽都說風的普通話,和爸爸在一起的時候,就說風的粵語。
逢秋正坐在沙發上看書,一聽到這道聲氣的聲音,立刻站起走向門口,響響跟個小老虎似的撲進懷里,逢秋彎了彎,立刻把孩子抱起來。
“媽媽,媽媽,窩好想你哦。”響響白的小手摟住逢秋的脖子,撅起的小往逢秋臉上親了好幾下,然后就害地摟住逢秋不松手。
逢秋也親了親小棉花糖,“媽媽也想響響,就響響自己嗎?爸爸來了嗎?”
Advertisement
“我在這。”徐清從外面走進來,男人穿黑長款大,肩膀上落了點雪,俊朗的眉眼剛毅溫,骨節分明的大手里拎著響響來的時候背的一只淡牛油果小斜挎包。
他把響響的小包掛在玄關的小架子上,換了鞋后走到逢秋邊,抬手了的頭發,隨即蹙了下眉,“好像瘦了,是不是沒好好吃飯?”
“沒瘦,還胖了呢。”逢秋抿了抿,角淺淺微笑,“怎麼這麼晚來了?”
“小姑娘想見你。”徐清聲音低沉,深邃的眼眸看著,“我也想你了。”
逢秋抬手遮住響響的眼睛,踮腳吻了吻他的下,徐清笑聲低沉,微涼的薄在上要描摹片刻。
“吃晚飯了嗎?”徐清溫聲問。
逢秋搖頭,“還沒有。”
“冰箱里還有菜嗎?”
“沒有多了,要重新買。”
“那我們帶著響響一起去逛街?”
“好。”逢秋點點頭。
車庫里有幾輛車,徐清開了一輛黑勞斯萊斯。
逢秋和響響一起坐在后座,這輛車之前沒有兒座椅,上星期才裝上。
一家三口先去了附近一家高檔商場逛逛,買了許多東西,又陪小棉花糖看了一場海洋館人魚表演,才離開商場去附近的大型超市。
超市里,響響被丟進購車里,徐清推著車,逢秋走在他邊。
買了一些蔬菜和類后,又買了一些水果,接著去零食區給小棉花糖買零食,經過酒水區的時候,小棉花糖要了一瓶兩萬多的路易十三。
小孩子不能喝酒,就是看上了路易十三的酒瓶子,圓圓的很好看,坐在購車里抱著不撒手。
結完賬,徐清推著購車走向地下車庫,逢秋剛把響響從購車里抱出來,忽然聽到一個悉的聲音的名字。
“秋秋,是你嗎?”
猜你喜歡
-
完結891 章
顧少,你老婆又帶娃跑了
在雲城,無人敢惹第一權貴顧遇年,關於他的傳聞數不勝數。陌念攥著手裡剛拿的結婚證,看著面前英俊儒雅的男人。她憂心道:“他們說你花心?”顧遇年抱著老婆,嗓音溫柔,“我只對你花心思。”“他們說你心狠手辣?”“要是有誰欺負你,我就對誰心狠手辣。”“他們說你……”男人伸手,把小嬌妻壁咚在牆上,“寵你愛你疼你一切都聽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還是你的。寶貝還有什麼問題嗎?”婚後。陌念才知道自己上了賊船。她偷偷的收拾東西,準備跑路。卻被全城追捕,最後被顧遇年堵在機場女洗手間。男人步步緊逼,“女人,懷著我的孩子,你還想上哪去?”陌念無話可說,半響憋出一句,“你說一年後我們離婚的!”男人腹黑一笑,“離婚協議書第4.11規定,最終解釋權歸甲方所有。
130.5萬字8 30545 -
完結978 章

孽火
繁華魔都,紙醉金迷。我在迷惘時遇到了他,他是金貴,是主宰,把我人生攪得風起云涌。我不信邪,不信命,卻在遍體鱗傷時信了他,自此之后,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253.1萬字8 16987 -
完結679 章

財閥大佬,您的夫人A炸了
【萌寶+馬甲+女強男強+打臉爽文】 正式見麵前: “找到那個女人,將她碎屍萬段!” “絕不允許她生下我的孩子,找到人,大小一個也不留!” 正式見麵後: “我媳婦隻是一個被無良父母拋棄的小可憐,你們都不要欺負她。” “我媳婦除了長的好看,其他什麼都不懂,誰都不許笑話她!” “我媳婦單純善良,連一隻小蟲子都不捨得踩死。” 眾人:大佬,求您說句人話吧!
124萬字8.25 732289 -
完結7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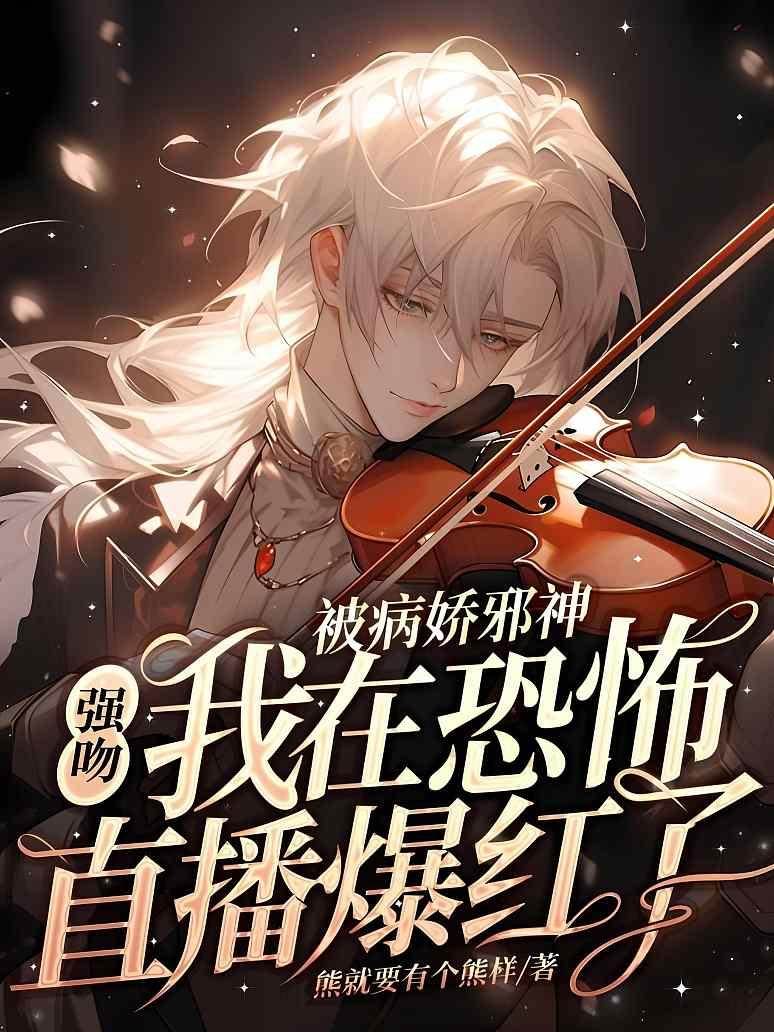
被病嬌邪神強吻!我在恐怖直播爆火了
桑榆穿越的第一天就被拉入一個詭異的直播間。為了活命,她被迫參加驚悚游戲。“叮,您的系統已上線”就在桑榆以為自己綁定了金手指時……系統:“叮,歡迎綁定戀愛腦攻略系統。”當別的玩家在驚悚游戲里刷進度,桑榆被迫刷病嬌鬼怪的好感度。當別的玩家遇到恐怖的鬼怪嚇得四處逃竄時……系統:“看到那個嚇人的怪物沒,沖上去,親他。”桑榆:“……”
123.3萬字8.1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